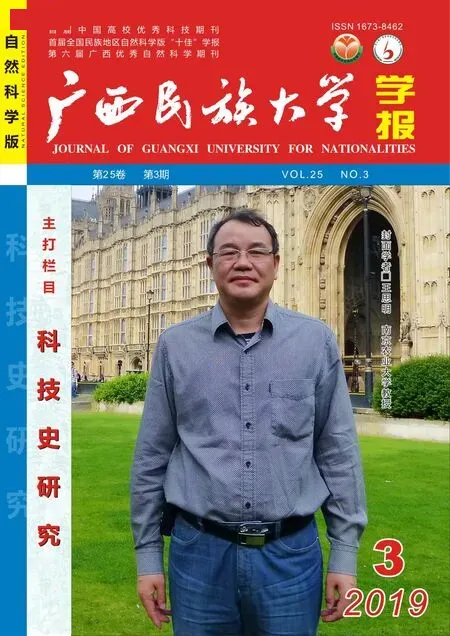“算術”和“數術”*
——中國傳統數學發展的兩條進路
周瀚光
(華東師范大學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中國數學史研究開展到現在,應該有條件對中國傳統數學的發展路徑做一個宏觀的分析和把握了.在筆者看來,中國傳統數學在其不斷發展的進程中,存在著兩條具有不同特點的路徑:一條是“算術”的路徑,一條是“數術”的路徑.所謂“算術”,顧名思義,就是計算技術和算法系統,它以解決國計民生中的具體數學問題為目的,涉及田畝、測望、工程、營建、賦役以及商品交換、度量換算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所謂“數術”,則主要討論較為抽象的數理,其中不僅包括了基本的數學理論問題,甚至還涉及更加廣泛的領域,如用“數”去范圍天地、化成萬物,去把握并預測萬物發展和人生命運.①在筆者看來,中國古代的“數術”一詞具有廣義、中義和狹義三種不同的含義.廣義的“數術”,數學家秦九韶的說法,數理和算術相關的內容,同時也包括了星占、形法(后世演變為風水)等與數學無關的方術(術數).一如班固《漢書·藝文志》中“數術略”之“數術”.中義的“數術”,特指僅與純粹數學相關的內容而不包括其他與數學無關的方術,其含義大致與秦九韶《數術大略》(即《數書九章》)書名中的“數術”一詞相當.狹義的“數術”,則專指純粹數學(即中義的“數術”概念)中與“算術”(即計算技術)相對而不同的內容,大致與《數術記遺》書名中的“數術”一詞相近.本文所說的中國傳統數學發展兩條路徑之一的“數術”,就是在狹義的意義上使用的,專指中國古代數學中與“算術”(計算技術)相對而不同的數理思想及其他內容.按照南宋數學家秦九韶的說法,數學具有“大”和“小”兩方面的功能:“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數書九章序》).這里“經世務、類萬物”的“小”者,就是“算術”的功能;而“通神明、順性命”的“大”者,則是“數術”的功能.從兩者的表現形式和書面語言來看,“算術”一般采用實際生活中應用問題的形式,并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問——答——術——草”這樣一種較為規范的書寫程式;而“數術”則多采用注釋、陳述、推理、論證等不拘一格的書寫形式,并且往往喜歡引用《周易》或其他傳統經典中的概念和詞句.從兩者的數學家群體來看,“算術”家以朝廷的行政官員為多,而“數術”家則更多地來自民間,其中一部分具有天文歷法的背景,另一部分則具有道教或隱士的背景.這兩條路徑從中國數學一開始發源后,就沿著各自的方向并按照不同的特點齊頭并進地向前發展,期間經過了分分合合,各展所長,互相交融,互相補充,最終匯成了中國數學史精彩紛呈的絢麗景象.大致說來,當“算術”和“數術”這兩條發展路徑合流而融匯在一起的時候,往往是中國傳統數學大踏步前進的時候,中國古代數學發展也由此而達到一個新的高峰.
(一)
中國傳統數學發端于伏羲畫八卦的《周易》,這是歷代數學家的共識,而《周易》正是算術和數術的共同起源.《漢書·律歷志》說:“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劉徽《九章算術注序》一開頭就說:“昔在包犧(即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這里的“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出自《周易·系辭下》,所說的“通神明”和“類萬物”正是后來秦九韶區別數學大小兩種功能的出典.這說明中國數學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蘊含了“通神明”(數術)和“類萬物”(算術)兩方面的內容,存在著算術和數術兩種潛在的發展進路.所謂“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中的“九九之術”,是用來“類萬物”的乘法口訣和四則運算,是算術;而“六爻之變”則是用來“通神明”的測算之術,是數術;中間用一個“合”字把它們連接起來,說明算術和數術一開始是融合在一起的,而且算術是為數術服務的.
時間稍晚一點的黃帝也是中國數學的鼻祖之一.《數術記遺》中說:“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這是說黃帝發明并確立了數的記法和用法.又傳說黃帝的老師大撓發明用天干和地支來記年、記月和記日,黃帝時的隸首作數,倕發明了畫圓和畫方的規矩,等等.所以劉徽的《九章算術注序》在肯定了伏羲氏對數學的始作之功后,接著便說:“暨于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后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這說明在劉徽的思想里,黃帝的數學功績是繼承了《周易》的數學傳統,并在此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神而化之、引而伸之”的發展.
大約在西周初年周公的時候,算術開始從數術中分化出來并獨立地向前發展了.周公制禮,規定貴族子弟必須學習和掌握六種基本才能——“六藝”,其中之一便是“九數”,而這就是最早的國立“算術”學科.秦九韶《數書九章序》說:“周教六藝,數實成之.”劉徽《九章算術注序》說:“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這說明周公時確立的“九數”,即是后來《九章算術》的濫觴,也是中國數學史上“算術”這一發展進路的重要標志.
到了春秋戰國的時候,儒家和法家等有志于國計民生的學派繼承了數學發展中的“算術”這一傳統.儒家創始人孔子年輕時就很懂算術,后來更把包含算術在內的“六藝”作為他教育學生的重要內容之一,并且培養出了曾參、冉求等一些精通數學的人才.枚乘《七發》說:“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說明在西漢人的眼中,孟子也是很擅長于計算的.法家的《管子》把“計數”列為其治國的七大法則(“七法”)之一,以為“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管子·七法》).現存的《管子》一書中,保存了先秦時期的許多“九九”口訣、分數運算等原始數學資料.李悝在《法經·盡地力之教》一文中,通過加減乘除九步四則運算,逐一列出了當時農村一家五口的正常收支情況,并且把這一運算過程詳細地記錄在文章里面.除了諸子學派之外,還有一些專門的數學家繼承并發展了“算術”這一傳統,例如秦簡《數》的作者和漢簡《算數書》的作者等.
與此同時,數學發展的另一條路徑——“數術”,也在獨立地向前進展.春秋末年的《老子》曾說:“善數者不用籌策”,這說明當時確實有一些數學形式是無關籌策,無關計算的.①劉徽《九章算術注》卷五說:“數而求窮之者,謂以情推,不用籌算.”這可以從一個側面證明《老子》的話并非虛言.就我們現在所知的與計算技巧迥然相異的數學形式,首推戰國時后期墨家的《墨經》中所蘊含的理論數學萌芽.《墨經》運用其所掌握的邏輯思維方法,對一系列數學概念如圓、方、平、直、厚、端、兼、體、盈、損、窮、倍等,用判斷和命題的形式給出了科學的定義,從而開創了中國數學史上理論幾何學研究的先河.同時又用推理和論證的形式,探討了“位值制”計數法、整體與部分的關系等一些基本的數學原理.同時期的名家則提出了“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等一系列涉及“無窮”的數學悖論.
除了上述理論數學的內容外,中國古代的“數術”中還包括了與天文歷法相關的數學內容.由于天文歷算在中國古代具有“范圍天地、曲成萬物”以及“通神明、順性命”的功能,因此將其歸于“數術”是理所當然的.班固在編撰《漢書·藝文志》時,即將“歷譜”置于“數術”略之下.他解釋“歷譜”說:“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此圣人知命之術也.”[1]這種“通神明、順性命”的“大”功能與純粹計算技術的“小”功能顯然不同,所以在《周禮》“九數”的算術傳統中是不被包括的,在后來繼承這一傳統而編撰成書的《九章算術》中也付諸闕如.
“算術”和“數術”這兩條不同的數學進路發展到漢代,各自出現了自己的代表著作.“算術”的代表著作是《九章算術》,而“數術”的代表著作則是《周髀算經》,兩者具有較明顯的不同特點.《九章算術》是一部由官方編定的實用數學著作,最早的編撰者為漢初的北平侯計相張蒼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周髀算經》則是一部民間口耳相傳的數理天文學著作,至今仍不知其作者是誰以及其確切的成書年代.①現在的數學史家一般認為,《周髀算經》是長期積累編撰而成的一部著作,最晚在公元前1世紀前后成書.《九章算術》的內容涉及田畝、測望、工程、營建、賦役以及商品交換、度量換算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體現了當時計算技術和算法體系的最高水平.《周髀算經》則闡述了數學方法在測量天地、制訂歷法中的作用,提出了學習和研究數學的正確方法,論述了勾股圓方的基本知識、測望“日高”的計算方法以及《四分歷》的基本數據和有關算法等一系列數學理論問題及與天文歷法相關的數學內容.《九章算術》以應用問題的形式引出計算方法(術),每一問題基本上都采用了“問——答——術”這樣一種比較規范的表述程式;《周髀算經》則仍然采用傳統的敘述和論說相結合的寫作方法.《周髀算經》還借周公之口發出“大哉言數”的感嘆,體現了其不限于具體計算技術而要去追索數之“大”者的學術旨趣.
(二)
“算術”和“數術”這兩條具有不同特色的數學進路各自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之后,由于某種歷史條件和學術契機,又常常會出現一種融匯和合流的景況,而這又往往給傳統數學的發展帶來了一股新的動力.縱觀漢代以后數學史的發展,這種“算術”和“數術”融匯合流的景況主要出現了三次,而每次融匯合流的出現,都對傳統數學的發展起到了推動的作用,從而使中國數學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算術”和“數術”的第一次融匯合流出現在魏晉時期,是由劉徽通過注釋《九章算術》而得以完成的.劉徽于正史無傳,是一位民間的布衣數學家.從其《注序》中屢屢征引《周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而化之,引而伸之”、“兩儀四象精微之氣”等話語以及關于“日高”和“日徑”等測望計算方法的論述來看,他對于“數術”方面的內容是非常精通的.當他把“數術”的精髓引入“算術”,用他掌握的豐富的“數術”知識來注釋《九章算術》這樣一部“算術”代表著作時,立刻使《九章算術》的數學水平大大提升了一步.劉徽的這種融匯“算術”和“數術”的注釋工作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1)劉徽繼承了先秦墨家注重邏輯和理論數學的傳統,按“審辨名分”的原則對《九章算術》中的許多數學概念給出了明確的和準確的定義,又用“析理以辭”的方法對《九章算術》中的許多公式和法則進行了詳細論證和邏輯證明,從而奠定了中國古典數學理論的基礎.
(2)劉徽繼承了《老子》“大直若屈”和《周髀算經》“圓出于方”的圓方統一思想,及先秦名家和《墨經》關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的無窮分割思想,首創“割圓術”以求取圓面積,并在此基礎上求得圓周率π=3.14和π=3.1416這兩個較為精密的近似數值,從而使中國古代關于圓周率的計算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3)劉徽繼承了《周髀算經》中因歷算需要而測量“日高”的方法,創立了“重差術”這一相似勾股形的比例算法,并把它推廣到測量諸如海島、遠山、深谷等一些極高、極遠、目之能及而人不可達的目標,從而彌補了《九章算術》在這一方面的缺陷和不足,開創了一個新的數學研究領域.
顯然,劉徽的這些工作都是原來數學發展中“數術”這一進路的強項,是以《九章算術》為代表的“算術”這一進路的弱項,而劉徽通過他對“算術”和“數術”的融匯合流,有效地彌補了原來“算術”進路的不足之處,提升了當時數學研究的整體水平,從而使劉徽的《九章算術注》成為中國古代數學發展的一個高點.
魏晉以后,中國古代數學在劉徽《九章算術注》的基礎上,繼續沿著“算術”和“數術”這兩條具有不同特點的進路向前發展.到唐代初年,這兩條進路出現了第二次的融匯和合流.而這一次的融匯合流,則是以李淳風奉命編定十部算經并以此作為國子監明算科的教科書為代表.
唐初李淳風編定的十部算經是:《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五經算術》《綴術》和《緝古算經》.這十部算經可以說是匯集了自漢至唐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數學著作,也可以說是涵蓋了“算術”和“數術”這兩條研究進路的最重要的成果.其中《九章算術》《張丘建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和《緝古算經》這五部著作因其以計算技術為主要內容,大致可歸為“算術”類研究成果;而《周髀算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經算術》和《綴術》這五部著作則因其內容既含有計算技術而又不限于計算技術,大致可歸為“數術”類研究著作.關于《周髀算經》一書的“數術”性質,前文已有論述,此處不再重復.《海島算經》原為劉徽注釋《九章算術》時附在卷末的“重差”章,至唐時單獨成書.其內容源出于《周髀算經》中因歷算需要而測望“日高”的“數術”,經劉徽演化創立為“重差術”(相似勾股形比例算法),并把它推廣到測量諸如海島、遠山、深谷等一些目之能及而人不可達的目標.《孫子算經序》說:“夫算者,天地之經緯,群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陰陽之父母;星辰之建號,三光之表里;五行之準平,四時之終始;萬物之祖宗,六藝之綱紀.”這種對于數學的極端推崇,明顯帶有《周易》論數的印跡.《孫子算經序》中又論及數學的目的是“稽群倫之聚散,考二氣之降升;推寒暑之迭運,步遠近之殊同;觀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縱橫之長短;采神袛之所在,極成敗之符驗;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這顯然就是秦九韶所說的“通神明、順性命”的“大”的功能.該書托名孫子,雖不必視為先秦孫子所著,但其中保存有先秦以來兵家或其他學派的思想資料,則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其中的“物不知數”一題,開啟了后世“一次同余式”理論的研究和“中國剩余定理”的取得,是對世界數學史的重大貢獻.這在《孫子算經》的年代,應該是屬于“善數者不用籌策”(《老子》)的重要成果.《五經算術》是一部對儒家經典中涉及數字計算的有關內容進行詳盡解釋的著作,其論題的表述方式與以《九章算術》為代表的數學著作中“問——答——術”的基本程式完全不同,明顯是一部“數術”類的著作.至于《綴術》,雖因其早已佚失而不知其具體內容,但從其作者祖沖之曾編制《大明歷》和唐初國子監明算科規定學習《綴術》一書要長達四年這兩個史實來看,推測該書當是一部與天文歷算有關的較為深奧的“數術”著作.又據李淳風《隋書·律歷志》和《九章算術注釋》所述,祖沖之父子曾取得圓周率3.1415926<π<3.1415927及球體積計算方法等重要數學成就,這些應該都是《綴術》一書中的重要內容.與十部算經一起作為唐代國子監明算科教科書的,還有《數術記遺》和《三等數》等數學著作.《數術記遺》以“數術”為名,本身就昭示了其“數術”的性質.該書至南宋時,因《綴術》一書的佚失,而被補列于《算經十書》之中.
唐初,“十部算經”的編定以及當時國子監明算科對各種數學典籍的收集和研究,是中國古代數學自先秦以來的一次大檢閱、大合成和大總結,也是“算術”和“數術”這兩條發展進路的一次大融匯和大合流.它克服了在此之前數學發展或偏于一隅,或隱于民間,或失之單薄的弱點和不足,使中國古代數學的整體發展迎來了一個豐盛期和繁榮期,并由此而奠定了唐朝作為一個數學大國的歷史形象.東西方各國前來學習先進的數學知識和其他知識的遣唐使絡繹不絕,而中國當時先進的數學知識則隨著這些數學典籍的翻譯和傳播,流布到了東北亞、東南亞,甚至西方等各個國家.
中國傳統數學發展到宋元之際,迎來了“算術”和“數術”這兩條進路的第三次融匯合流.這一次的融匯合流是由秦九韶、李冶、朱世杰、楊輝這四位號稱“宋元四大家”的一流數學家群體共同完成的,并由此而推動中國古代數學的發展達到了它的頂峰.
秦九韶在《數書九章序》中,自述其“早歲侍親中都,因得訪習于太史,又嘗從隱君子受數學.”這說明他學習數學的背景,一個是來自于太史的歷算,另一個是來自于隱士的“數學”,兩者都屬于“數術”的范疇.他的《數書九章》一書,又名為《數術》《數術大略》或《數學大略》,也昭示了其數學研究的“數術”淵源.他提出的“大衍求一術”理論,自稱源自于《周易》的“蓍卦發微”,并且能解決“古歷會積”的歷算問題,顯然是建立在“數術”這一研究進路上的重大數學成果,并因其給出了一次同余式的一般解法而創立了“中國剩余定理”.李冶的數學工作和研究成果,是其中年以后棄官北渡、隱居山林時才開始并取得的.他寫作數學名著《測圓海鏡》的動力和基礎,完全是因為得到了一部具有道教背景的算書——“洞淵九容”,因愛不釋手、日夕玩繹才最終完成的.而所謂“洞淵九容”,其實就是討論勾股容圓、方圓相纏的“數術”問題.該書最早記載并保留了“天元術”這一中國數學史上的重大成果,被后來的數學史家稱為“自古算家之秘術”(清阮元《測圓海鏡序》).朱世杰完全是一位民間的數學家和數學教育家.他在《四元玉鑒》中所創立并闡述的“四元術”——多元高次聯立方程解法,也是中國古代數學發展的一個高點.他在書中的一個旁注中說:“凡習四元者,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也.”這里的“盡性窮神之學”,無疑應歸于“通神明、窮性命”的“數術”進路.至于楊輝,他不僅對流傳下來的《九章算術》中的計算技術非常精通,曾著《詳解九章算法》十二卷,保留并記述了“賈憲三角”等一系列重大數學成果;而且還編撰了《續古摘奇算法》一書,開辟了“縱橫圖”(即今所謂“幻方”)研究這一組合數學的新領域.縱橫圖起源于《周易》中的“洛書”和《數術記遺》中的“九宮”,它在楊輝的時代,完全是一種“不用籌策”、與復雜的計算技術關系不大的“數術”.
要而言之,宋元時期中國古代數學發展高潮的來臨,一方面是由于當時的數學家們繼承并發展了以《九章算術》為代表的卓越的“算術”傳統,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他們同時又吸取了傳統“數術”研究進路中的優秀創新成果,兩者融匯相通,共同發力,終于使傳統數學達到了它前所未有的高峰.到了明代以后,一則由于“八股取士”制度的盛行而導致“算術”進路乏人問津,二則由于“數術”進路偏向神秘一隅而少有真正的數學創新,致使傳統數學趨于停滯,一蹶不振.明末數學家徐光啟一針見血地指出:“算數之學特廢于近世數百年間爾.廢之緣有二:其一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實事,其一為妖妄之術,謬言數有神理.”(《同文算指序》)誠哉斯言.
(三)
以上我們簡要地回顧了中國傳統數學中“算術”和“數術”這兩條進路既各自獨立發展又互相融匯合流的歷史過程,從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關于中國數學史研究的新認識:
(1)首先應該為中國歷史上的“數術”一詞正名.廣義的“數術”一詞,既包括了“算術”(計算技術)和數理,還包括了一些與數學無關的其他方術(“術數”).而中義的“數術”一詞,排除了與數學無關的其他方術,完全就是純粹的數學內容,其實就是中國古代“數學”的代名詞.正如中國古代的“儒術”其實就是“儒學”一樣,中國古代的“數術”其實也就是“數學”.秦九韶的《數術大略》又稱《數學大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狹義的“數術”,則主要是指與“算術”(計算技術)相對而不同的數學理論、與天文歷法相關的歷算知識以及與計算技術關系不大的其他數學分支(例如縱橫術等).
(2)以《九章算術》為代表的計算方法及其算法體系,雖然顯示了中國古代高超的計算技術和獨特的數學風格,但是卻不能完全代表中國古代數學發展的最高成就和水平.《九章算術》從其成書的時代起,就缺漏了數學理論以及天文歷算這一領域的數學成果,在其后來的發展過程中又不能完全涵蓋各個時代的其他數學成就.如果沒有劉徽在《九章算術》原有框架中增添數學理論以及其他“數術”元素,沒有宋元數學家取得突破《九章算術》框架的其他重大數學貢獻,中國古代數學成就的光輝將大為遜色.
(3)中國古代數學的發展起源于廣義的“數術”.以后“算術”從“數術”中獨立出來,并與狹義的“數術”齊頭并進地各自獨立發展.在整個傳統數學的發展史上,“算術”和“數術”這兩條進路曾有過三次大的融匯和合流,第一次是魏晉時期劉徽對《九章算術》的注釋,第二次是唐代初期李淳風編定“十部算經”并作為國子監明算科的教科書,第三次則是“宋元四大家”在融匯整合這兩條進路的基礎上創造了一系列嶄新的重大數學成果.“算術”和“數術”的每一次融匯合流,都極大地推動了傳統數學的進步;而兩者在宋元時期的第三次大融合,則將中國傳統數學的發展推向了它的最高峰.
鑒于以上這些認識和總結,筆者認為,我們對于中國數學史和中國數學思想史的發展,也許可以采用一種新的思路和新的框架去理解和概括,以便使其更加符合中國古代數學發展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