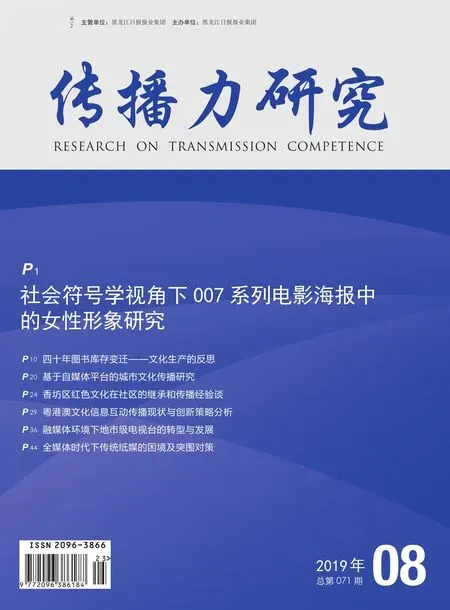社會符號學視角下007系列電影海報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熊沁 貴州師范大學傳媒學院
一、引言
詹姆斯邦德又名007,長期以來被視為是英雄和冒險的象征。在每部007 的電影中,總有女性角色圍繞著主角詹姆斯邦德,她們被統一稱為“邦德女郎”。在過去的50年里,邦德女郎一直被認為是用來發展邦德的性格、推進情節并為觀眾創造一種替代性的性體驗的[1]。邦德小說和電影中的女性肖像一直受到許多學者的討論,但大部分都是基于電影的敘事或場景。電影海報作為電影與廣告的結合,可以提供電影人物和即將到來的日期的主要直接觀看信息,或揭示人物關系和位置等深層信息。007 系列的女性肖像也出現在電影海報上,并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變化。本研究以007 系列電影海報上的女性肖像為研究對象,從社會符號學的視角對海報上女性肖像進行分析來考察不同時期海報所展現女性角色的意義和地位。
二、007 系列電影海報的視覺語法分析
社會符號學主要研究的是符號系統在社會環境所傳達的社會意義。Kress 和van Leeuwen 在社會符號學研究方法中構建了視覺圖像的語法框架,為視覺符號的分析和多模態話語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分析方法,并確定了視覺語法分析的框架:再現意義、互動意義和構圖意義[2]。
(一)再現意義
再現意義是通過形象本身來講述故事的內容和方式,可以分為敘事結構和概念結構[3]。概念結構為圖像中的人物、事件提供信息,而敘事結構中存在給觀看者提供一種動作過程的發生方向,稱為矢量。矢量項的存在與否是這兩種結構的最大區別。
在1962-1974年間的海報上,畫面中總是有三個以上的女性角色。邦德被她們包圍保持著典型的拿槍姿勢,而邦德女郎都以性感的姿態出現,她們的胸部和臀部總是指向邦德的方向或與邦德的身體接觸。這種模式表明了他們之間呈現的是誘惑與被誘惑的關系。海報中的邦德身體形態展示的往往是拒絕被誘惑,同時他拿著槍的方向也成為了一種指向矢量。槍不是直接指向女性人物,而是靠近女性人物,這對女性來說是一種威脅和警告,表明女性可能是一個反派角色。
在1977年到1987年的海報中,每個海報上都只有一個女性角色。這段時間的海報中,她大都依靠邦德,身體直接接觸成為了一種載體,似乎沒有邦德的支持女郎就會倒下。同時在這個時期,邦德拿槍的方向發生了變化。在這個時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槍直接指向邦德女郎相反的方向表明他們是在同伴,另一種是指向邦德女郎表現她是邦德的敵人。當槍指向邦德女郎時,女郎也拿著槍,這是邦德女郎第一次以相對平等的方式與邦德抗爭。
從1989年到2015年的海報來看,邦德和邦德女郎之間不像之前那樣具有強有力的媒介與矢量指向。這表明邦德女郎不再依靠邦德,這表明她們更加獨立,與邦德站在同一個位置。
(二)互動意義
互動意義表示圖像和觀看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在一定意義上提示觀者對圖像所表征事物應該有的態度。互動意義分為三個層面:接觸、社會距離和態度,其中接觸和社會距離將是影響觀眾與海報人物關系的最重要因素。接觸是指圖像中的參與者與觀看者通過目光的指向性構建的一種關系,社會距離是指圖像中的形象與觀看者之間的距離所反映的社會關系。
從1962年到1974年,詹姆斯邦德的大部分形象都是與觀眾有直接的目光接觸的,仿佛在像觀眾索取一些東西,這被稱為“需求模式”[3]。與邦德相比,并不是所有邦德女郎都會盯著觀眾看,而這些不指向觀眾的目光被Kress&Van Leeuwen 稱為“提供模式”[2]。
在1977年至1987年的海報中,邦德在“需求模式”和“提供模式”兩個方面都有所體現。然而,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當邦德女郎處在需求模式時,邦德肯定是在同一個模式中。當邦德轉變為提供模式時,邦德女郎則不可能呈現為需求模式。而從1989年至今,無論是邦德還是邦德女郎的肖像,大多數海報都呈現需求模式。
互動意義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距離,它代表了和觀眾之間的親近程度,距離越近,與觀眾越親近。1962-1974年的海報中,根據繪畫中的透視規則,邦德看起來比邦德女郎更接近觀眾。在1977-1987 的海報中,邦德和大部分的邦德女郎都離觀眾很遠。有的海報中雖然看起來邦德女郎的距離更近了,但她們是背對觀眾的,地位相比起來并沒有提高。從1989年到1999年,雖然沒有具體的模式,但邦德與觀眾的距離都比邦德女郎近。兩者與觀眾的距離從海報《擇日而亡》(2002年)開始變得相同,他們出現在近社會距離中,在相同的位置上表現出同等的力量。
(三)構圖意義
構圖意義是指圖像的再現意義和互動意義聯系組成有意義的整體的方式[4]。Kress&Van leeuwen 提出了三種實現構圖意義的方式,即信息值、取景和顯著性[2]。
當涉及到信息值時,在22 幅海報中,女郎有4 幅在邦德的右側,8 幅在左側,2 幅在頂部,8 幅在底部。根據Kress 和Leeuwen 的觀點,左側可以被視為“給定的”,而右側則是“新的”。頂部是“理想”,底部是“現實”[2]。大多數海報中的安排都表明邦德是“新的”和“理想的”,是創造了超越觀眾想象的新事物,成為了不僅吸引邦德女郎而且吸引觀眾的理想英雄。相反,邦德女郎更像是“給予的”和“真實的”。她們被安排為一個工具,刻板印象使她們在觀眾中可預測。他們是“真實的”,容易犯錯誤,容易改變態度。這種“給定的新的”和“理想的真實”的定位,可以構成邦德式的杰出英雄形象,而邦德式的女孩只是普通人。
當涉及到取景和顯著性,在早期海報中邦德一直是中心人物,邦德女郎則被定位在側面作為背景。從1977年起,女性肖像開始出現在了中心附近,顯示出與邦德的關系更為密切。從1989年到1999年的海報上有兩個女人,不管是在中間還是在側面,她們和邦德都呈現出對稱關系以表現出女孩與邦德之間的平等地位。然而,從2002年開始,海報中心不再僅僅是邦德一個人,而是由邦德和女郎組成,更加反映了他們同等的地位。
三、社會意義與女性形象
通過海報的分析可以看出,邦德與邦德女郎的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改變,女性的形象也發生了變化。然而,這些海報中也存在著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使得這些變化始終停留在男性主導的地位上。
Neuendorf 曾經對邦德電影進行內容分析,認為邦德女郎的形象隨時間變化而發生的改變是多方面的。除了越來越多的女性主角外,女性的形象變得更加活躍,這些變化使女性角色具有自主性和參與性[5]。邦德女郎變得更加獨立、有能力和復雜,她們在身體和智力上逐漸變得更強,可以被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與邦德相抗衡。然而,女郎們仍然被描繪成普通人,即使在極端情況下,她們比邦德更弱,更不具標志性。
事實上,邦德女郎是在當今的社會語境中被描繪出來的。Funnell(2011)討論了過去幾年邦德電影中女性的描繪是如何受到女權主義和女權主義者的影響的[6]。在20世紀60年代左右的邦德電影中存在著女性的自由取向,這與第二波女權主義有關。當時海報上所顯示的大部分女孩都穿著比基尼,并以這種方式展現自由。然而,她們依舊是依賴邦德的衍生角色。Jenkins 從另一個方面進行了解讀,他說詹姆斯?邦德的電影是在冷戰時期創作的,女性被描繪成代表俄羅斯人的形象,而邦德則被描繪成傳統和明智的西方國家,如英國和美國,尤其是在《俄羅斯之戀》這部電影中[7]。此外,在20世紀70年代,為了回應美國的公民權利,黑人婦女第一次出現在《生死》(1973)中。然而,在海報上,她被放在右后方,很容易被忽視。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女性形象可以看作是邦德電影對女權和后女權主義的回應[5]。
盡管女性肖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但由于幾十年來一些刻板的描繪的存在,很難承認女性的地位已經上升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Seger 認為,在電影中相同的環境下,如果角色是女性,那么她需要比男性更聰明、更吸引人[8]。Kilburne認為,廣告中女性的理想寫照是非常苗條、嬉皮、性感、迷人的,甚至是現實生活中女性的理想目標[9]。從007 系列電影海報上的女性肖像可以看出她們都是苗條、性感和迷人的。她們的形象和其他媒體上的女性形象一樣,促進了女性刻板印象的形成,滿足了大眾審美,這種審美也可以看作是滿足男性需求的一種方式。
Mulvey 曾討論視覺藝術是從男性的視角來描述和構造的,這被稱為男性的凝視[10]。在視覺文化中,男性的觀點和態度主導著形象。男性的目光可以來自男性導演、男性角色和男性觀眾。導演根據自己的品位選擇女演員,并與男性角色進行比較,形成對比,取悅男性觀眾。邦德的海報上也存在男性的目光,所有的女性角色都苗條迷人,尤其是當她們站在邦德身邊時。以最新海報《幽靈黨》為例,邦德女郎穿著貼身的晚禮服,展現出良好的身體曲線,而邦德則穿著西裝,站直。衣服的黑色和銀色也用來產生對比。這些對比吸引了男性觀眾,讓他們關注女性,甚至把自己放在邦德的故事里。
四、結語
綜上所述,由于文化的發展進步及女性在現實中的地位的提升,無論是在海報還是電影中,邦德的女性肖像在過去幾年中都發生了變化。然而,這些變化仍然停留在男性主導的方式上,與其他媒體上的女性形象一樣鞏固著女性在社會中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