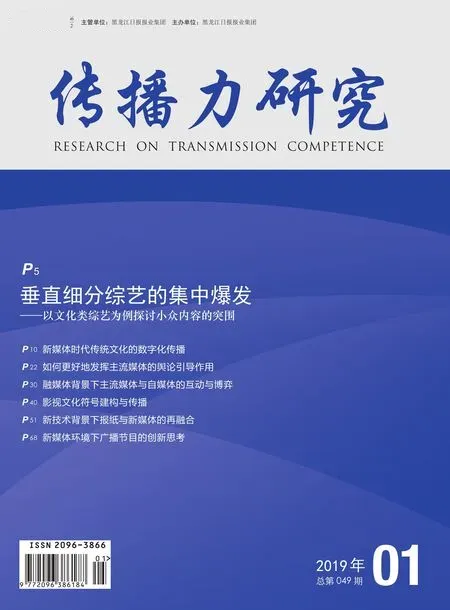影視文化符號建構與傳播
劉霜 廈門大學
一、視覺傳播與影像
人類傳播活動經歷口語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等,當今我們已進入“影像時代”或者稱之為“視覺傳播”時代,影像成為傳播活動中最為核心的表達語言和符號。鑒于圖像對于信息傳播的優勢,海德格爾早就指出,“世界圖像并非從一個以前的中世紀的世界圖像演變為一個現代的世界圖像;不如說,根本上世界變成圖像。”海德格爾的觀點強調了視覺文化的重要地位,同時也預告著視覺傳播時代的到來。
視覺傳播是伴隨媒介發展而興起的新傳播現象,其實質是視像符號空前發展。科技的發展、消費社會的形成,純粹的文字信息傳播已不能滿足個人和互動的需要,理性的邏輯思維讓位于感性的視覺呈現。視覺文化也出現了從語言主因型文化向圖像主因型文化的轉向,影像作為一種直觀性信息被大眾所青睞,日漸成為視覺傳播的主流。
在這種“視覺轉向”的時代背景沖擊下,形象所承載的符號意義也達到新的高度。復旦大學教授孟建曾說在以語言為中心的文化形態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是語言符號的生產、流通和消費,而在以形象為中心的文化中,影像符號生產的價值格外引人注目。
二、影視文化符號建構——水墨
色彩是影像符號中的重要一員,中國對于色彩的應用早從仰韶文化時期就有體現,并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豐富色彩的應用。水墨是中國色系中璀璨的一部分,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顯著的民族特色。以往我們多在繪畫、書法作品中了解到它的存在。但是,媒介技術的發展使得傳統文化符號有了表達的新可能,伴隨媒介變革成長起來的大眾也傾向于以更靈動、更現代的方式接觸傳統文化的魅力,在此過程中水墨符號的新表達成為社會發展的需求。
電影是影像符號聚集的重要產物,媒介技術的發展刺激當今電影影像的變革。2018年9月在中國上映的《影》對色彩符號的使用上大膽創新,創造性地使用水墨視覺作為畫面的主要表現,賦予水墨符號以情感價值,呈現獨特的文化感知。該片在金馬獎獲12項提名,最終獲得最佳導演、最佳視覺效果、最佳美術設計、最佳造型設計四個獎項。可以說在視覺表現層面得到了廣大觀眾和評委的認可,它的成功也刺激著我們重新審視色彩符號對影片敘事與視覺傳播的作用。
《影》中對水墨的全面應用,展現出蒼涼與遒勁的視覺風格。黑白兩色構成權利的對抗,連續的陰雨又調和了黑與白的沖撞,渲染出自然的灰色過渡空間,映示了撲朔迷離的關系。例如影片末尾子虞死時面具呈現的一左一右景象,左邊是物象上的征服,右邊是情感上的絕殺,水墨的表現方式代表了子虞在這場真身與影子決斗中的全面失敗,黑白畫面更直觀地傳遞出角色潰敗時的凄慘與悲痛。整體來看,《影》的色彩運用高度統一,連續的圖像、故事性場景為我們展現了色彩符號與人物性格、敘事邏輯之間的關聯,讓我們在色彩美觀的基礎上去探索蘊含的哲理。
除此之外,影視化的表現方式便于觀眾交流,社交平臺和人際傳播為影片帶來更多曝光,推動符號更大范圍的傳播。《影》中水墨符號的成功應用讓我們看到了色彩于敘事的作用,也讓我們感受到傳統文化創新的魅力,這樣的模式有助于建立文化符號的連續性、統一性,也為新時代視覺傳播帶來動力支持。
三、小結
當前,電影作為一種獨特的媒介形式,以符號化的方式實現電影藝術家與觀眾間的交際愿望。人們在符號化的世界中生存并進行敘事活動。大眾傳播時代下,我們已經了解到水墨作為視覺符號在電影中建構人物形象與內容敘事的影視化應用。不難發現的是,在影視表現中若是完善視覺文化符號與影片敘事的結合,可以更全面地構建角色的個性特征,增強故事的張力,也更能吸引觀眾的眼球,引發共鳴。
除去色彩這類視覺符號在影視視覺文化中已有所應用,服飾、道具等符號同樣是整體視覺的一部分,作為文化符號在視覺傳播時代也逐漸被重新解讀。但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表現形式都應該建立在對符號本身意義理解的基礎上,根據符號的文化特征賦予其時代性的視覺化呈現。未來研究需要明晰符號的組合與媒介選擇之間的邏輯,從而更好地把握視覺符號與媒介對大眾文化生活和文化傳承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