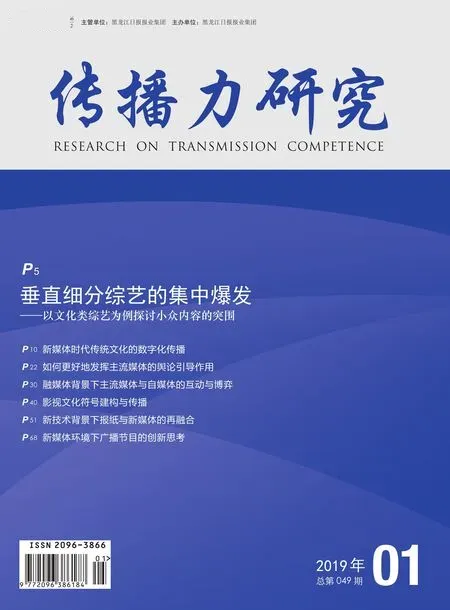細節承載對與對的抗爭
——評電影《十七歲的單車》的道具
李文倩 山東美術出版社有限公司
電影《十七歲的單車》通過一系列極其微小的故事情節為我們展現了盡可能多的要素,這其中有涉及人自身的,也有社會現實的,尤其是以自行車這一道具實現了道德力量的局部的對與對的抗爭。
首先,作為道具的自行車對情節的發展起到串聯和推動的作用。影片通過騎車、丟車、偷車、還車、毀車等一系列事件敘述,其中自行車既是道具,又是情節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它是聯系前后故事的橋梁,傳遞著一種特殊的信息。
其次,自行車承載著兩個人的夢想。對小郭來說,他是“新時代的駱駝祥子”,自行車意味著工作,即生存手段。而對于小堅來說,除了一種交通工具,自行車還象征著他的身份及炫耀的心理,同時也是其愛情的發端,如片中小堅為女孩修好車鏈后的移鏡頭,小堅騎車時明快的節奏體現出他的滿足感,矛盾和沖突油然而生。先是圍繞車的歸屬問題,小郭等車、偷車、搶車,而后被小堅等揍,把兩者的矛盾外化出來,這其中便是對與對的抗爭,小郭要車理所應當,車本該屬于他,而小堅用五百元買下車,不給也合情合理,雙方在一種沒有“錯”的狀態下展開了對自身的維護,這個矛盾是電影直接顯現的。
再次,自行車滲透著社會現實,體現著時代背景的特殊性。這其中影片詮釋著身份,人們對城里人和鄉下人有著嚴格的定位,在城市里,就連鄉下人也用城市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小郭的朋友曾說“不能讓人看出你是個外地人”,并用刷牙這一細節將城鄉兩種人區別開來。小郭最初騎車時的笑容表現著自己被這個城市接納的喜悅,他向往城市的生活,羨慕城市人的生活狀態,片中所有外地人幾乎都在表達著對自己的否定,他們渴望被城市同化。其中小保姆的前后變化以及別人看待她的眼光從側面映射著對兩種身份的界定。影片以自行車這一細節折射著社會的現實,這是在中國特有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問題。同時,兩者的對與對的沖突是擺在觀眾面前的,并沒有激化,更沒有解決。一個慢鏡頭展示了小郭騎單車游走于眾多的車輛,這是他與這個城市的對立,盡管雙方都有著各自的理由,但作為一個無法抗拒的沖突,這也是顯而易見的。
再者,自行車作為一個符號折射出人性的兩面。影片以自行車為聯結,通過一系列無遞進式的對話反映著個體人的內心變化及人與人的矛盾沖突。小郭在澡堂與服務員的對話類似張藝謀《有話好好說》中張秋生與趙小帥圍繞電腦索賠問題的爭論,兩者都是為一個問題各持己見卻沒有最終答案,這其中展現了各自“對”的成分卻沒有人為“對”作出解答,還有影片最后小郭為小堅的事挨揍,的確如他所說,“不關我事”,但戲劇沖突就是如此,人們總會被無端卷入游戲,并且游戲雙方都各有道理,即人性既有自我保衛的一面又有對外攻擊的一面。同時,17歲的小堅與其父因為自行車的來路而爭執的一場戲也為我們提出了對“成熟”這一概念的定位,這就是影片之所以選擇17歲的主人公而非成人的原因,他作為一個界于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的邊界年齡的人,其人性的展現便具有特殊性,我們不能用叛逆、反叛簡單定位,因為其特殊時期及社會現實決定了其行為的必然性。當然,這也是他的對與成人的對之間的抗爭。
影片以自行車為載體,以毀車為最終結局,充分調動了一切可使用的因素,也是所有矛盾沖突的集中詮釋,但其高潮恰恰不是所展示矛盾的激化,毀車的人與小郭是素不相識的,因此,影片是用矛盾外的因素介入矛盾中從而打破了常規,但最后的慢鏡頭展現了小郭扛車走入車來車往又反映了矛盾的回歸,人們只能無休止地卷入沖突卻無法從中真正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