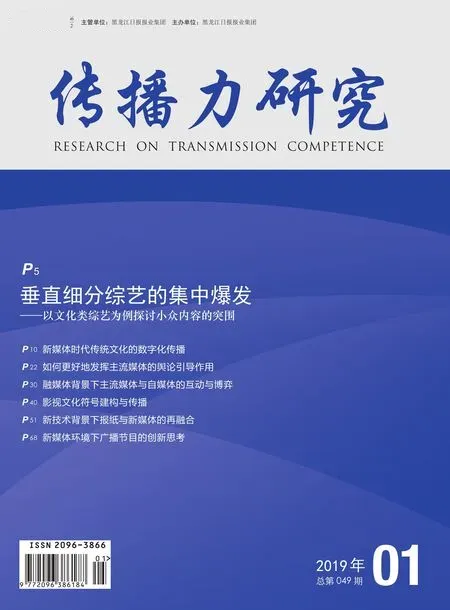淺析開心麻花系列電影的性別觀降維
劉小銘 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
一、消費社會性別背景建構
自2015年推出首部電影以來,截至目前開心麻花通過旗下子公司開心麻花影業已相繼參與出品 6 部電影作品,其中由開心麻花投資主創并據其舞臺劇改編的電影,有《夏洛特煩惱》、《羞羞的鐵拳》、《李茶的姑媽》這三部。由于之前開心麻花出品的電影在票房上表現不俗,所以《李茶的姑媽》在首映當天獲得了高達35.8%的排片占比,可見各大電影院對于這部喜劇的票房表現還是充滿期待的。但《李茶的姑媽》最終以5.1分的評分慘淡收場,票房表現也不盡人意。
開心麻花系列輕喜劇幽默戲謔,對準了普通人的喜樂與煩惱,聚焦討論能產生共鳴的大眾話題,創造了大量接地氣的本土原創故事。充當“情感事業指南書”的角色。但是其在性別角色塑造上仍局限于傳統社會性別建構的普遍性框架,把愛情披上消費文化的外衣,突出其時尚性和感官刺激性,在對大眾進行煽情的過程中,迎合并滿足社會大眾的心理需求。貫穿始終的還是“男性拯救女性”的男權話語。在開心麻花系類電影中這種性別角色建構一直為專家所詬病。在《李茶的姑媽》中更是成為觀眾批評的一個主要靶標。
二、傳統性別話語影視表達
性別角色是社會性別理論的重要概念,它是指“基于男女差異而形成的男人與女人不同的一套行為規范和行為方式”。[1]影視媒介建構性別形象,成為了具有社會意義的性別角色符號。那么,開心麻花系列電影中的性別形象是如何建構形成的,其是否真實地映射了社會現實,又產生了何種社會影響?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開心麻花系列電影通過強化傳統性別話語,夸大女性外在美的價值,推崇自我犧牲的賢妻良母形象,灌輸“男性拯救女性”的男權話語,淡化女性的個性張揚和獨立發展,以迎合消費主義的經濟邏輯,無視審美正義與文化倫理,強化“瞬間的快感”,看似現實題材,卻并非現實主義,缺乏能讓人動容的真實感染力,此外,如果觀眾辨別力和反思精神等媒介素養不足,易對觀眾產生不良的導向性影響。
《夏洛特煩惱》感情線索固化了以男性為主導的性別身份定位,當前中國社會對于男性成功人士的標配想象。女主角馬冬梅全程為男主角做出種種犧牲和放棄,作為個體的自我建構被極大地弱化甚至消失;《羞羞的鐵拳》里,盡管女主角馬小一開始被設計為睿智沉穩的著名女記者,但是身體變化不等同于“換位思考”,在“互換身體”后的重點情節敘事中馬小的事業發展和理想追求這條敘事線幾乎被完全放棄,無論再獨立現代的新女性角色外殼都無法掩蓋其喜劇敘事邏輯架構的基礎——對男女兩性的刻板印象;而同樣采用“身體互換”這一敘事噱頭的《李茶的姑媽》不僅沒有改進帶有主流父權話語性別歧視色彩的自我陶醉,反而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劇情充斥著大量有“性暗示”意味的低級庸俗的笑點,情感模式存在敘事的內在缺失和有違常理的邏輯漏洞,整體情節推進十分勉強,難以說服觀眾。
通過分析不難發現,在開心麻花的系列電影中所展現的性別價值觀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在男性主導的視覺文化下言說“女性天生是弱者”的話語,理想成功是男性追求的最終目的,女性只是對其能力的一種承認,但是男性卻是女性存在的全部目的。女性形象被極度夸飾,以此來滿足人們的感官需求。
三、國產兩性喜劇缺陷矯正
近年來,在以“情感制作”與“快適倫理”為表征的“后情感主義”社會語境里,國產喜劇電影總體呈現同質化競爭、低俗化發展、審美化疲勞的走低態勢。放在與國產喜劇平均水平的對比視野中,開心麻花的表現不乏可圈可點之處。但是,喜劇的精神內核,是要做到“含淚的笑”,根本目的是再現社會現實、引發讀者深思。[2]開心麻花若想使品牌系列電影走得更遠,有必要改進并做到兩性喜劇的立體化和“去污化”,對電影故事所指涉到的社會矛盾不只是淺嘗輒止、點到為止,通過強行設置完滿結局予以想象性的解決,而是要克服碎片化和斷裂感,挖掘更深層的美學意義和精神內涵,激發人們的審美余情并由此引發深思,把握創作導向,矯正迎合市場帶來的低俗化缺陷。而影片的性別價值觀作為影片敘事建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可以成為開心麻花鞏固品牌效應,避免走向爛俗及自我復制,從而走得更遠的重要抓手和依托。
女性不僅是客體、獵物和陷阱,其自身的精神和能力的成長和獨立對于自身及對于整個社會都十分重要。使熒幕上的女性形象跳出“看”與“被看”的框架,在男女平等的參照系中建立中國女性自己的話語權,凸顯女性獨立品格,表達和反映其個性特質、工作及生活狀態,以正確的性別價值觀引導當下電影市場的風向和社會審美心理,引發觀眾思考、關照社會現實,潛移默化地對社會產生影響。女性人物形象在各種復雜關系中逐步獲得主體意識,和男性一樣以更廣闊的視角來生存與思考,有助于實現影片中人的精神價值的延展。
不僅有利于婦女的生存和發展,也有利于兩性和諧社會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