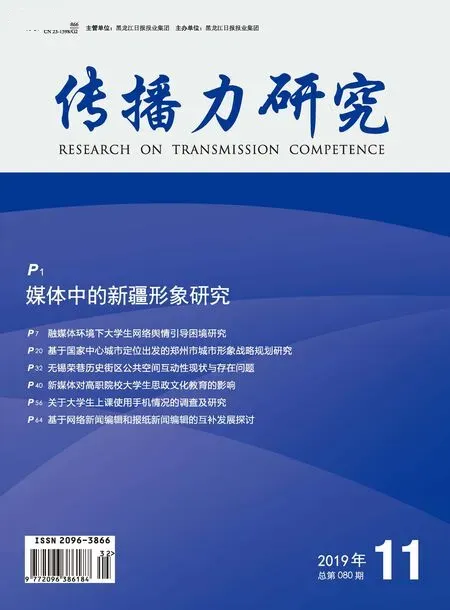淺談新媒體傳播下微電影敘事特征
陳淑萍 重慶航天職業技術學院
以微博為中心,延伸出的微小說,微訪談、微信等新興網絡事物,已經預示著一個“微”時代的到來,這也正迎合了人們逐漸碎片化的思想,符合現代人獲取信息的習慣。微電影,便是“微”時代的產物,傳統電影在時長上往往是微電影的幾倍甚至幾十倍,因此電影在敘事主題上通常圍繞著一個核心人物或者核心點引出多個分支,由此來組成一個相對宏大豐滿的故事。而微電影在較短的時間內主要人物數量相對較少,多數微電影只有一兩位核心人物,因此微電影在新媒體傳播下的也呈現出其獨特的敘事特點。
一、微電影之“微”
大眾對微電影的理解,或許就是電影片長、制作周期相對短一些的電影,而某知名業內人士提出的“微而足道”頗為深刻,并不是短一點就成了微電影,巴爾扎克給我們留下的名言是,藝術品就是“在小小空間里驚人地集中了大量思想”,“它是一種概括”。微電影的一個美學信條應當是,在短小的篇幅里驚人地集中大量的審美概括。
說到審美概括,《創城記》微電影系列總的《爸爸的蛋糕》做到了,影片借助兩塊蛋糕用細膩的手法表達了父女間濃濃的親情,不論從場景的選擇、演員表演、拍攝角度、構圖、光影等都做了精心的設計。印象深刻的一個鏡頭是,爸爸走出房門時,屋里那個偌大的風扇,前景與人物的對比表達了爸爸心中的失意。
值得一提的是法國的一部微電影《調音師》,也絕對稱得上是審美概括,真正做到了在小小的空間里集中了大量的思想,看完一遍,沉思良久,或許很自然地再看一遍,甚至有些臺詞:“人們相信失去會更敏感”,“人們不是偷窺癖就是暴露狂”等都會給我們帶來很多思索。
二、微電影之“反”
“反”是指微電影的反常規構思,意思是微電影經常關注一些反常態的人的生活,如美好2012 大師微電影的四部影片:《我的路》、《你何止美麗》、《行者》、《龍頭》等,甚至包括《調音師》都是記錄一些反常態的人和事。
筆者對“反”字的理解是創意,或許表達的是一個簡單的事,但是用很有意思的鏡頭語言來表達。比如雅虎的微電影廣告,分別邀請了陳凱歌、馮小剛、張紀中這三位風格全然不同的導演來拍攝,觀眾對《阿虎篇》、《貴族篇》和《前世今生》都有自己的看法,不可否認的事,這三個具有相同主題的影片都極具創意,正是這種創意,讓觀眾對其久久難忘。
微電影的主題一般都是常規的,如表現親情、表達愛情、記錄一個事件等,只有創意才能出彩。
三、微電影之“深”
這個“深”不是所有導演都能做到的,由于微電影帶有后現代主義精神,其文化內涵夾雜在虛擬和現實之間、現象與本質之間,其中的分界線愈發模糊,這也就導致了微電影的文化內涵缺乏深度感。
那么什么是深呢,就是深度的探索,深度的挖掘。比如校園微電影中很多片子喜歡用青春友情、愛情、夢想做為拍攝取材,微電影《南城舊事》和《那年夏天》,選景突破了慣用的校園和本地,到了云南大理,可以說是千里跋涉,十分用心,十分辛苦。片子中也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地方,如《南城舊事》中飄散的長發,和《那年夏天》中男生所講的那個有點冷的笑話,始終沒有打破觀眾的預期視野,沒有留下啟迪思考的鏡頭或者臺詞,片子中還是有“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感覺。說到預期視野的話,微電影《囚》表現出色,中間很多鏡頭設計都有創作者深深的探索和思考,讓觀眾印象深刻。
四、微電影之“思”
如果說“深”是創作人員的探索,那么“思”就是影片留給觀眾的探索。導演姜文在回應一位記者對他的《太陽照常升起》質疑其鏡頭語言晦澀難懂時,曾回應:“一個電影被人家看了,記住,能爭論,能討論,甚至反復地在想,它里邊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的觀念里邊,這對一個創作者來說,是最大的收獲。”
姜文的微電影《看球記》便帶給觀眾很多思索:影片講述了父親帶著兒子去看球賽,在進場時去發現忘記帶票而引發的一些故事。其中那個假票販子的角色設計的頗有意思。下面看一段爸爸與假票販子之間的對話:
爸爸:“你誰啊?倒票啊!”
假票販子:“危機公關啊!”
把倒票行為理解為危機公關,很有創意,結合當時的娛樂新聞,經常會提到“公關”二字,我想這段臺詞也表達了創作者對娛樂圈、政治圈以及社會上各種“假”的反抗。
另一段對話,依然是爸爸和假票販子之間:
爸爸:“我買票,多少錢你說”
假票販子:“足球和貨幣都不重要,我談的是尊重”
……
假票販子:“咱們都成了朋友,你卻急躁得不愿和我多聊一句”
在短短五分鐘內,姜文用自己的方式對人性的表達既犀利又浪漫,臺詞既簡單又深刻。帶給觀眾深深的思索。
五、結論
微電影應運而生,順應時代需要,依靠短小精悍,節奏緊湊,貼近生活的特征,開辟了新媒體語境下獨特的敘事表現方式。希望校園微電影創作者們能不一味地拍攝惡搞、低俗的只停留在感官層面的作品,能做到“微”、“反”、“深”、“思”,創作出具有專業性、藝術性、人文性的具有更多內涵的有意義的微電影作品,傳遞正能量,傳播符合時代精神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