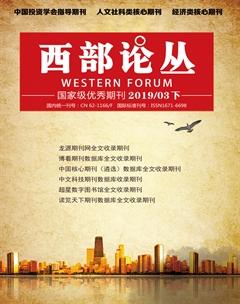多民族國家的國家認同問題研究
呂鶴霄
摘 要:《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后,“民族國家”這一概念被廣泛使用。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國家內(nèi)部包含較多民族,當個體對自身族群的認同高于國家認同并將次民族的認同置于民族國家認同之上時,就會出現(xiàn)國家認同危機并引發(fā)諸多政治性后果。解決多民族國家認同危機的關鍵在于塑造“民族”與“國家”的統(tǒng)一邊界,強化各民族間共同的政治認同。
關鍵詞:多民族國家 民族認同 國家認同 認同危機
一、多民族國家的國家認同危機
Nation在西方語境中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概念,它包含了民族與國家的雙重內(nèi)涵。作為一種國家形態(tài),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通常以民族與國家有機結(jié)合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其形成是為解決歐洲王朝國家內(nèi)民族與國家二元對立問題。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定了“國家至高無上”原則,民族國家正式取代王朝國家成為新的國家形態(tài)。民族國家實質(zhì)上是一套保障民族認同國家的制度機制,自出現(xiàn)以來就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國家認同危機:
(一)國家認同危機出現(xiàn)的原因
首先大多數(shù)國家是多民族國家,經(jīng)常出現(xiàn)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沖突,兩者邊界并不統(tǒng)一。厄內(nèi)斯特·蓋爾納認為,“地球上存在大量潛在的民族”,潛在民族數(shù)字“可能比能夠獨立生存的國家的數(shù)字要大得多”。當個體對自身族群認同高于國家認同并將次民族的認同置于民族國家認同之上時,國家認同危機出現(xiàn)。周光輝和劉向東稱之為地方民族成員對次級群體的“狹隘的忠誠”,周平則將這種多民族內(nèi)國家認同問題視為一種“集體忠誠沖突”。在成功創(chuàng)造國家后,統(tǒng)治集團必然會強化相應的單一民族意識,以神圣化國家的歷史文化根源,當國家能力較弱而無法有效強化這種意志時,就會引發(fā)社會運動和革命。
其次,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是不同類型的認同,民族認同是文化認同,而國家認同則是政治認同。民族是一種文化共同體,所謂的民族認同就是個體基于客觀的血緣或主觀認定的族裔身份而對特定族群產(chǎn)生的歸屬感,基于民族文化之上的民族認同形成歷經(jīng)很長時間且難以改變;而國家是“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政治實體,所謂的國家認同個體感覺他屬于特定的政治單位、地理區(qū)域和團體,將其視為予以強烈效忠、恪守義務或責任的對象以確定他屬于哪一國家。多民族國家的合法性是基于國內(nèi)各個民族群體的認同,當多民族國家內(nèi)的某個民族群體的國家認同較低,國家就不能從這里獲得合法性。
(二)多民族國家認同危機的政治性后果
首先,國家的法律、政策往往會受到質(zhì)疑,導致國家的合法性降低。在政治生活中,國家政策的實施和在社會中的政策效果往往會以迥異于國家初衷的形式告終,很多國家的統(tǒng)治范圍甚至僅僅局限于城市甚至是首都附近。根源在于國家的統(tǒng)治建立在國民的忠誠、服從基礎之上,如果國家內(nèi)部存在較多民族群體不愿意遵守國家的法律、政策或?qū)ζ浔в械钟|情緒,就會導致國家統(tǒng)治成本過高、治理能力低下,尤其是在國家認同弱化的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隨時會產(chǎn)生各種社會與政治運動。
其次,引發(fā)民族間沖突和民族分裂運動。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大都伴隨著激烈的民族沖突,那些具有鮮明族群中心主義而經(jīng)濟剝奪感強烈的少數(shù)族群群體,更容易陷入與其他族群的沖突。民族沖突可能采取從非暴力對抗到暴力沖突等多種方式,包括言論攻擊、集體抗議、暴力斗爭、種族屠殺等,不論何種形式其本質(zhì)都是對現(xiàn)有政權的顛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民族分裂者長期利用民族、宗教等進行反動宣傳,煽動民族間的對立、制造恐怖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會產(chǎn)生各大民族間的隔閡、影響民族團結(jié)。即便是擁有強大國家機器的蘇聯(lián)、民主法治最為成熟的美國,也面臨著潛在的民族沖突與分裂運動。
此外,國內(nèi)民族問題嚴重會給境外勢力的介入國內(nèi)事務提供可乘之機,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和主權、領土的完整。威脅主要來自于兩大方面:一是境內(nèi)的民族分裂勢力與境外敵對勢力勾結(jié),通過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獲取反對國家政權的軍事、經(jīng)濟等支持;二是外部國家會以民族自決、保護人權為由采取軍事措施,悍然入侵。一個獨立、穩(wěn)定、繁榮的民族國家是贏得國際地位的前提,一旦出現(xiàn)國家認同危機,將導致綜合國力的急劇下降。
二、消除多民族國家的國家認同危機的路徑
多民族國家認同危機無法回避,抑制民族沖突、實現(xiàn)民族整合是多民族國家的一項重要職能,必須借助國家政權,制定相應措施,對多民族進行有效整合,以保證國家穩(wěn)定與發(fā)展。
(一)給予一定的民族自治權
自治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治理方式,其實質(zhì)是對少數(shù)群體權利的一種制度保障。隨著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在保證國家統(tǒng)一的前提下,許多國家開始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將民族自治作為國家層面的一項重要政策。民族自治的優(yōu)勢在于通過一定的政治權力分配與制度設計,可以將基于一定血緣紐帶、文化傳統(tǒng)基礎上的民族情感性意識引導到充滿理性的政治認同中,實現(xiàn)民族成員對國家政權的認可并主動地進行政治參與,從而增強少數(shù)族群國家認同感。聯(lián)合國大會于2007年通過了《聯(lián)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明文規(guī)定了“土著民族享有自決權”,他們可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謀求自身的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發(fā)展。我國的民主自治政策始于1947年成立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新中國成立以來又先后建立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和西藏自治區(qū)五個少數(shù)民族自治區(qū),并將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寫入國家憲法,在維護民族團結(jié)方面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二)塑造各民族間共同的政治認同
建構族群認同所依據(jù)的基礎要素,主要來自于血緣紐帶或族裔身份。從國家認同的塑造路徑上看,個體首先在文化上對特定民族(例如中華民族)產(chǎn)生認同感,在此基礎上接受一定的政治制度安排,由此形成國家認同。作為政治認同的主體是多樣的,主要包括對國家政權、制度、政府與執(zhí)政黨、政治人物等的認同:所謂國家政權認同是對掌權者權力來源的認同,按照韋伯劃分有傳統(tǒng)慣例或世襲、他人崇拜與追隨、法理基礎三大來源;就制度認同而言,越來越多的經(jīng)驗表明,穩(wěn)定、高效的制度設計是凝聚國民對國家向心力的關鍵;就政府與政黨認同而言,政黨政治時代國家權力由執(zhí)政黨行使,對執(zhí)政黨的認同意味著對政府、國家政權的認同;政治精英認同是指人們對政治領袖、政治家產(chǎn)生的情感上的歸屬感。總的來說,人們之所以認同某個國家,是這個國家在政權組織、政治制度、社會政策等各方面能切實保障國民利益,能夠讓內(nèi)部成員過上一種有尊嚴的生活。對多民族而言,塑造各民族對國家的政治認同將會促成對國家的認同。因此較多學者認為民族主義情感是一種盲目的國家優(yōu)越感,它帶有對外部群體的蔑視和排外傾向,并具有對外部群體的支配感,而愛國主義是一種健康的、建設性的、寬容的愛國情感。
(三)強化領土認同
按照國家的經(jīng)典定義,現(xiàn)代國家就是在特定領土內(nèi)成功宣布了對正當使用暴力的壟斷權,因此領土是構成國家的要素之一。江宜樺將國家認同分為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和制度認同,不論國家采取何種建構模式,由于認同對象的不確定,始終無法消除國家認同危機,領土認同較之文化、民族和制度認同,最大特點是具有明確的物理邊界,決定了領土認同可以成為多民族國家認同的客觀基礎,離開領土認同,制度認同會流于世界主義,民族認同也無法形成于地方性族群認同的合圍之中,因而它們都不能起到塑造和強化國家認同的作用。多民族國家的領土認同往往會在國家面臨主權危機和國家安全的時候強化并最終有助于國家認同的鞏固。近代中國在對外敵的不斷抗爭中,民族意識在不斷成長,并在全面抗日期間達到一個高峰:以“民族”一詞為例,1911年年底前《申報》可檢索出的條目為243條;到1925年、1928年、1936年、1939年,“民族”一詞可檢索到的條數(shù)分別增加到了502條、1119條、1507條、2369條,可以說外部勢力的侵略催化了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讓中華民族這一文化概念逐漸被賦予了政治性,并成為了新中國的國家認同基礎。
三、余論
對于一個多民族國家,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并非都能合二為一,能否在保持對族群忠誠和認同的同時培育對國家的認同,是學術界持續(xù)關心的話題。多民族國家的認同危機問題不僅困擾著二戰(zhàn)后走向獨立的亞非拉發(fā)展中國家,也困擾著具有成熟民主體制的西方發(fā)達國家。只有保持“民族”與“國家”邊界的統(tǒng)一,才能保持多民族國家的穩(wěn)定。
參考文獻
[1] 周平.多民族國家的國家認同問題分析.政治學研究.2013(01):26-40.
[2] 江宜樺. 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1997(25): 83-121.
[3] 高永久等.民族政治學概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3
[4]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222.
[5] 黃道炫.戰(zhàn)時中國民眾的民族意識[J].史學月刊. 2008.(05):16-25.
[6] 周光輝,李虎.領土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構建一種更為完備的國家認同理論.中國社會科學.2016.(07):4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