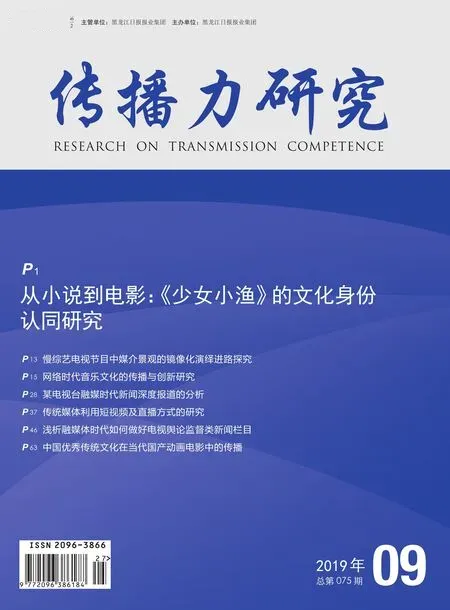404 Not Found
404 Not Found
變革,從講故事開始
——論中國電視的“敘事革命”
盧小豆 安徽廣播電視臺
“我認為電視也如同一個荷馬時代的吟游詩人,因為盡管媒體技術在進步,但是電視所不斷效仿的仍然是最傳統和最簡單的講故事的情景。”
——[美]莎拉-考茲洛夫:《敘述理論與電視》
一、講“好故事”與“講好”故事,從“內容為王”到“敘事為王”
相傳古時候,在古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海島上,有一個薩桑王國,國王山努亞荒淫殘暴,每天要娶一個妻子,在王宮過夜,但每到第二天雄雞高唱的時候,便將她殺死。這樣持續了三個年頭,國王整整殺掉了1000多個女人。宰相的女兒桑魯卓于是主動要求進宮為妃。夜幕降臨,她就給國王講故事,天亮時分,故事到了最精彩的部分,她突然打住不講了。國王為了知曉故事的結果,只好特許她再活一天。就這樣,桑魯卓每天講一個故事,國王每天都想:“我暫且不殺她,等講完故事再說。”日復一日,桑魯卓的故事無窮無盡,一個比一個精彩,一直講到第一千零一夜,一共講了一千零一個故事,終于感化了國王。他說:“我決定不殺你了,你的故事讓我感動,我要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永遠保存。”于是,就有了現在流傳世界、家喻戶曉的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譚》)。
今天,當我們翻開《一千零一夜》,每個故事的情節都足夠引人入勝,精彩紛呈。但是,如果你就此認為桑魯卓成功地化險為夷,扭轉乾坤,僅僅是因為她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講不完的故事,那就大錯特錯了。試想想,在那生死一線的夜晚,如果沒有她繪聲繪色、出神入化的講述,如果她不能審時度勢,巧妙設置懸念,每到天亮便戛然而止,讓國王深陷其中,欲罷不能,那么哪怕她故事再多再精彩,恐怕也會和之前那一千多個女子一樣,難逃一死的厄運。因此,桑魯卓絕對是一個頂級的故事大師,是她獨到的講述技巧與表達方式,給這些故事注入了無窮的魔力,讓自己轉危為安。
實際上,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也會經常碰到這樣的情況:同樣的事情,有的人講起來聽者索然無味,而在另一個人嘴里,立馬就變得活靈活現起來。因此,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故事如何講述,比故事本身更為重要。美國傳播學者羅伯特-艾倫在著名的傳播學論著《重組話語頻道》中就一針見血指出:“每一個故事,都是由某一個人用一種特有的方式講述的。”
也就是說,沒有講述者,就沒有故事;或者更確切的說,是講述者,他對事實的取舍、認知、理解以及敘述的方式,最終決定故事的內容、情境、意義和傳播效果。而在現代社會,媒介扮演的正是這樣一個講述者的角色。
二、敘事革命,改變語態只是開始
《華盛頓郵報》資深撰稿人威廉-E.布隆代爾說:“因為我們的注意力總是放在了讀者對信息的需求上。于是,我們忽視了一個所有讀者最普遍的要求,一個所有要求中最基本的要求:給我講一個故事,看在老天爺的份上,讓它有趣一點。”(《〈華爾街日報〉是如何講故事的》)很明顯,對于受眾而言,他們需要的不僅是一個故事,而且必須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如何讓故事變得有趣?不僅取決于情節內容,講述的方式同樣重要。美國傳媒學者莎拉-考茲洛夫在《敘述理論與電視》一文中明確指出:“每一個敘述故事都可以被分為兩個部分:故事部分,即究竟發生了什么和對誰發生的;再就是話語部分,即這個故事的講述方式。”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60分鐘》是美國歷史最悠久而且收視率最高的欄目之一,它的制片人唐-休伊特在回答為什么欄目會具有長久的生命力的時候,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所要做的只是講好一個故事。對《60分鐘》來說,好的節目就是,一個精彩的故事在第二天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唐-休伊特舉重若輕的一句話令人回味。愛聽故事是人與生俱來的天性,如果你在節目中把一個故事講述得跌宕起伏,懸念迭出,把人物個性塑造得鮮明突出,敘述結構清晰流暢,語言通俗易懂,那么觀眾就會不由自主的被吸引,一直看下去并且用心去體會,這個故事就一定能穿越很多人的感官認知,而激蕩他的思想甚至靈魂。但問題的關鍵是你會這樣講故事嗎?
始于上個世紀90年初的中國電視新時期十年改革,被業界定義為“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孫玉勝:《十年》)電視不再唯我獨尊,高高在上,自說自話,對觀眾進行“說教”,實施“話語暴力”。而是漸漸開始放低姿態,增強親和,與觀眾平等“對話”。但就像改革的標志《東方時空》的宣傳語——“真誠面對觀眾”所說的,它更多解決的只是電視媒體如何面對觀眾、怎樣說話的問題,只是改變了語態,遠沒有推進到重構電視敘事的高度。因此,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批電視精英們先知先覺而引導的自我改良。其實,在那一輪改革的初始就出現過“敘事革命”的萌芽——《生活空間》,該欄目的創始人陳虻當時提出了開創性口號:“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電視界石破天驚。其突破性意義不僅在于題材上聚焦“老百姓的故事”,更體現在電視敘事方式上。它以紀實的手法,樸實的畫面,生動的現場,個性的采訪,每天講述一個精彩的百姓故事,在觀眾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其中很多作品在今天看來仍然堪稱經典。可惜的是,這樣一個極具先鋒實驗意義的欄目,只進行了不到兩年,就由于種種原因停辦了,雖然它的電視理念幾乎影響了一代電視人。及至后來,《新聞調查》等欄目也在敘事方式上進行了一些實驗,但也僅僅局限于個體的探索而已,并沒有真正引發電視從“改變語態”到“重構敘事”的革命。以至于上一輪新聞改革的主要發起者之一孫玉勝,后來仍然發出這樣的感嘆:“有時候我們不是缺少好的主張,而是缺少好的表達。”(趙華:《央視〈新聞調查〉臺前幕后》)
其實,對于電視而言,敘事絕不僅僅限于新聞和故事類的節目,所有的節目類型,都充滿了敘事,也離不開講故事,只不過在表現的形式上各不相同。電視劇自不待言,談話節目象《魯豫有約》、《鏘鏘三人行》等,主持人與嘉賓之間的對話,就是故事的起承轉合;娛樂節目象《中國新歌聲》、《我是歌手》,通過選手參與,觀眾互動,看上去是一場“才藝秀”,實質上是在講述一個個場內場外團結、奮斗,成功、失敗的故事;即便是廣告,也同樣離不開敘事,那些光知道一味吹捧產品性能的廣告,只會讓人看了倒胃口,只有那些蘊含動人故事和美麗意境的廣告,才會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好感,最經典的莫過于不久前陳可辛為蘋果手機拍攝的短視頻宣傳片《三分鐘》,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讓人記住了紀錄它的產品,讓人回味無窮。
三、敘事能力是媒體的核心競爭力
今天,數字傳輸技術的快速發展,不僅使印刷(報刊)、廣播、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發生著深刻的變革,更直接催生了第四媒體—網絡媒體的橫空出世。不斷涌現的新媒體,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其超強的互動性與廣泛的參與性,不僅顛覆了過去媒體—受眾的單向傳播模式,同時也進一步模糊了媒介與受眾的界限,每一個受眾個體,都有可能實現角色轉換,成為傳播主體,甚至成為一種媒介。
技術的進步帶來了傳播生態的革命,于是地球變小了,遙不可及的世界變得唾手可得,傳統媒體也因此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三度普利策獎得主托馬斯-弗里德曼于是得出這樣一個著名的論斷:“世界是平的。”他說:“人類歷史上從來未有這樣的時刻:越來越多的人會發現他們能夠找到越來越多的合作對象和競爭對手,人們將和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人互相競爭和合作,機會將越來越平等。”(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如果說在過去,電視可以依仗自己的壟斷地位實現“話語霸權”,無論播什么,人們都不得不收看,因為別無更多選擇;那么在今天,“傳播渠道的擁有和掌控能力對于傳媒產業核心競爭力形成的貢獻越來越小。”(喻國明:《“去碎片化”:傳媒經營的新趨勢》),任何一家媒體都很難再獨享信息和故事資源。那么,在傳媒開放、資源共享的時代下,大家都擁有同樣的素材,誰最能受到受眾青睞?毫無疑問,是那個最會講故事的。對此,南京大學潘知常教授甚至做出這樣的判斷:
“如果把電視節目的核心競爭力的諸多內涵集中到一點,應該是什么呢?在我看來,就是電視敘事的能力。”(潘知常 孔德明:《講“好故事”與“講好”故事》)
在當下,中國社會正處于劇烈的變革轉型期,在大發展的進程中,交織著各種利益紛爭,矛盾糾葛,幾乎每一天都會發生很多讓人拍案驚奇的故事,一個比一個離奇曲折。難怪作家張賢亮會發出這樣的感嘆:“我現在已經不寫小說了,因為我發現現實生活遠比小說要精彩的多。人們每天看新聞就夠了,誰還會看小說?”現實生活提供了無比豐富的題材,故事有了,媒體再也沒有理由抱怨自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何提高敘事能力,把“好故事”講“好”,是媒體,尤其是電視面臨的當務之急。
今天,數字技術催生了電視的大發展,新媒體強勢崛起,更讓電視臺越來越深切的感受到生存危機的迫近。這情境像極了《一千零一夜》:手握遙控器的觀眾好似薩桑王國的暴君山努亞,電視臺就是嫁進王宮的弱女子桑魯卓,命懸一夜之間,是生是死,就看你會不會“講好”故事了。只不過,觀眾比國王更冷酷,更無情,他們可不會在聽完一千零一個故事就被感化,放你一條生路。電視臺要想“活”下去,“活”得好,就得沒完沒了地給他們講好聽的故事。否則,觀眾的拇指一摁,就讓你在屏幕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就這么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