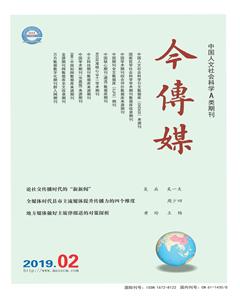中美媒體對“2017習近平訪美”的報道框架分析
周永金
摘要:對國家領導人出訪活動的新聞報道,既具有深遠的外交意義,也關乎媒體的話語權。媒體的報道框架是國家利益博弈的產物,框架的選擇能夠反映媒體的報道立場和觀點。本研究以臺灣學者臧國仁提出的新聞框架的三層次為理論基礎,圍繞《人民日報》和《紐約時報》關于2017年習近平訪美的報道內容展開分析。研究發現,《人民日報》在報道中突出責任框架,積極構建訪美成果議題,呈現中美關系和平穩定發展的現狀。《紐約時報》則受到媒體性質和國家利益的影響,強調沖突框架,對訪問成果持消極態度。
關鍵詞:框架理論;話語;報道;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2-0000-03
一、 研究背景
應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邀請,2017年4月6日至4月7日,在美國弗羅里達州海湖莊園,習近平和特朗普進行了會晤,國內外媒體都對此進行了跟蹤報道。研究中美兩國媒體對“2017習近平訪美”事件的報道,對于深入分析兩國政治傳播的特點,探討我國領導人在國內外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的意義。《人民日報》和《紐約時報》在國內擁有絕對數量的閱讀受眾,影響力較大,對政治性議題關注程度也較高,因此本文選取兩報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二、 研究方法
框架這一概念最早源于心理學家貝特森(Bateson),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Goffman)將其引入社會學領域,并賦予其理論意義。高夫曼指出,“框架是指人們用來闡釋外在客觀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們對于現實生活經驗的歸納、結構與闡釋都依賴于一定的框架。”[1]臺灣學者臧國仁提出框架包含選擇和重組兩個過程,在“看不見的手”的控制下,同一事件按照不同的排列順序和時空意義被呈現,媒體報道框架自然呈現出不同的特征。臧國仁提出了框架的高、中、低三層次結構理論,高層次的意義是指對事件主題的確定,中層次包含多重環節,如主要事件、先前事件、背景、歷史、結果、影響、歸因等等,低層次則從文本出發,分析字詞的修辭以及風格等等。[2]本研究將基于框架分析的方法,先對報道的總體情況進行描述,再從高層次上的主題框架、中層次上的結構框架和低層次上的話語框架三個方面展開具體分析,對中美媒體選擇的報道框架進行呈現。
三、中美媒體“2017習近平訪美”報道的框架分析
(一)報道的總體情況分析
1. 報道數量和周期
通過樣本搜集,《人民日報》總報道數量為18篇,《紐約時報》為11篇,這體現中國對該話題的關注度要更高。另外,在報道周期上,《紐約時報》在會晤前期的預熱上表現突出,在4日到6日都有相關背景的報道,《人民日報》的報道則從6日開始。在后期的評價和反應中,《人民日報》表現更好,10日和11日的報道有5篇,主要是對會晤本身的評論和對中美關系的展望,而《紐約時報》在10日和11日均無報道。因此《人民日報》可以發揮自身優勢,并借鑒《紐約時報》在會晤前期的預熱報道,使得報道周期更加完整。
2. 報道體裁
《人民日報》在報道中主要以消息為主(44.4%),形式也在不斷創新,主要體現在專訪形式的采用,借“中美議題”專家的聲音傳遞觀點,使讀者能理解中美關系的發展近況。《紐約時報》則在評論上占據一定優勢(27.3%),同時注意深度報道的集中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報道中《紐約時報》中加入了兩則漫畫報道,以戲謔的方式進行時政新聞的報道,(分別為When Trump Met Xi和Heng on President Trumps Meeting with Xi Jinping)增強了可讀性和趣味性。總之,兩家報紙均涉及了基本的報道體裁,但是在創新性上,《人民日報》還需向《紐約時報》學習,不斷創新報道形式,吸引受眾的注意力,同時也要加強對評論的重視程度,提升報道內容的深度。
(二)報道的“三層次”框架分析
1.高層次結構分析:報道主題框架
通過閱讀,本文歸納出的5個主題框架分別為:元首會晤、中美關系、敘利亞和朝核問題、經貿關系以及其它。《人民日報》的報道集中在“中美關系”(50%)和“元首會晤”(33%)有關的話題,報紙將中美關系定位于和平穩定向前發展,與中國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要求相一致,利于社會的穩定。如通訊報道《中美關系的大廈建設得更牢、更高、更美——記習近平主席赴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同特朗普總統舉行中美元首會晤》(《人民日報》2017年4月9日02版)將此次習近平訪美行動定位為“友誼之旅”,強調未來中美需走“合作之路”,才能“通向未來”。整體而言,《人民日報》肯定此次訪美取得的成果,對未來中美關系的穩步前進充滿信心。《紐約時報》的報道中于對敘利亞問題和朝核問題(36%)的報道,而有關中美關系的報道上相對較少(18%)。《紐約時報》的報道認為此次首腦會晤“… a chance for the Chinese leader to witness a raw display of American military might”(是為中國領導人提供了一次目睹美國軍事力量真實展示的機會)”,在會上,特朗普向習近平施壓,要求中國用其杠桿來遏制朝鮮。此議題的選擇是基于美國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力圖保證美國國內的安全和霸權地位。
2.中層次結構分析:報道結構框架
臧國仁認為,“重組是同樣的內容經過不同的排列順序與時空變換,就產生了不同意義。” [3]重組的表現是報道結構要素的選擇,本文確定的5種結構要素分別為主要事件、先前事件、預測、影響和評估。兩家報紙都以主要事件作為主要的結構要素(分別為33.3%和36.3%),但是《人民日報》比較重視對事件的影響和評估進行報道(44%),比如事件本身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尤其是對中美關系的影響。而《紐約時報》在此結構要素上的占比僅為27%,報道更傾向于對先前事件的報道(36.3%),比如對 “敘利亞問題”和“朝核問題”進行強調,突出本國在此次沖突事件中占據著主動地位。
3.低層次結構分析:報道話語框架
語言與符號信息在傳遞社會真實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新聞文本內部使用的關鍵詞反映了一定的感情色彩和社會心理內涵。通過詞頻統計,《人民日報》排名前十的詞語分別是習近平(145)、合作(128)、發展(130)、關系(111)、中美(119)、會晤(110)、美國(110)、中國(103)、元首(94)和雙方(92)。《紐約時報》排名前十的詞語分別是Trump(115), Chinese(100), Xi(94), Said(82), trade(45), American(45), President(45), North Korea(42), Meeting(35)和Syria(24)(括號內的數字是詞語出現次數,中文詞頻依據rost軟件進行獲取,英文詞頻依據國外WORDCOUNTER網站進行獲取)。《人民日報》在報道中多次使用“中美”、“合作”、“發展”和“對話”等詞匯,強化此次會晤在中美關系的塑造上起到的積極作用。而《紐約時報》則較少存在有關此次會晤的評價性詞匯,而是更多的關注“trade”(貿易)、“North Korea”(朝鮮)、“Syria”(敘利亞)和“nuclear”(原子核的)等議題,體現出兩國對待此次會晤的態度上也有所不同。
通過文本細讀,可以發現就會晤本身而言,《紐約時報》強化美國的主動地位,希望中方對美方提出的限制對朝供應問題保持“amenable”(順從的)態度,就習近平所處境地,用“tough”(艱難的)一詞進行描述,突出中方在會晤中面臨敘利亞問題的“兩難”境地。另外,多用“press”(壓迫)、“overshadow(使暗淡)”等動詞突出美方的主動地位,強化朝核問題和敘利亞問題在此次報道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在談到訪問成果時,美方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此次會晤的積極意義,將會晤氣氛描述為“warm and welcoming”,(溫馨且熱情的),針對會晤達成的具體成果,美方肯定“100-day-plan”(百日計劃)的作用,并將其描述為“way station of accomplish”(階段性成果)。然而整體性仍然認為此次訪美達成的協議較少,“百日計劃”也被認為是“only tangible announcement”(唯一實際性內容),在人權問題和環境保護等問題上尚未取得較大進展。在《人民日報》的報道中,就會晤本身而言,報道將會晤情境描述為“燈光璀璨、鮮花綻放”,認為此次會晤是一次“匠心獨運”的安排,用“熱情洋溢”修飾領導人的講話,強調會議的“友好氣氛”,多次使用“深入、友好、長時間”等積極詞匯描述會晤,肯定了會議的正面作用。就訪美成果而言,習近平連用“加深理解”、“增進信任”、“達成共識”和“建立關系”等多個動賓短語,肯定了此次會晤的重大歷史意義,訪問成果是“豐碩的”、“卓有成效的”,肯定了訪問所取得的實質性進展。在中美關系議題上,將合作描述為“唯一正確”的選擇,此次會晤使得中美關系迎來了“新篇章”。
四、 結論與討論
瑟曼特克(Semetko)和沃肯伯格(Valkenburg)認為,媒體報道中存在沖突(conflict)、人情味(human interest)、經濟影響(economic consequences)、道德(morality)、責任(responsibility)這5個“通用框架”,這些框架可以在不同媒介形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報道中普遍存在,雖然這些框架可能并不是同時出現。[4]通過對兩家報紙的總體報道情況和高中低三個層次進行樣本分析,結合以上5種“通用框架”,研究發現《人民日報》在報道中以正面報道為主,突出“責任框架”,《人民日報》肯定此次事件在推動中美關系和平穩定發展上的積極作用,強調中國真誠致力于與美國進行合作和交流,積極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國家形象。《紐約時報》則以負面報道為主,強調沖突框架,報道鮮少對中美領導人會晤的成果進行提及,而是將重點放在對“朝核問題與敘利亞問題”的報道上,希望能對中國施壓,強化本國在國際舞臺的主動地位。
報道框架的選擇主要受到媒體性質和國家利益的影響。在媒體性質上,《人民日報》是黨的“喉舌”,要堅持正確的辦報方向,突出報道的宣傳作用。因而其在報道中更加突出領導人形象塑造和會晤的積極影響等內容。《紐約時報》作為商業型報紙,則更多地受到市場的影響,報紙主要選取爭議性較大的“朝核問題和敘利亞問題”等議題來吸引受眾的注意力,這類議題具有通常具有較高的新聞價值,具有時新性、沖突性和重要性等特征。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兩國均有從自身出發來報道事件的偏好,這主要是受到國家利益的影響。兩國報紙都通過“轉喻”和“缺席”來傳達一定的意識形態,保障本國的國家利益。
總之,《人民日報》在“2017習近平訪美”這一議題上主要建構責任框架,這一框架與我國的現實環境和國際地位相一致。未來在國家輿論的競爭之中,我們還需要不斷對框架進行調整,找準定位,把握文化內涵和國家利益,如此才能在對外傳播中占據主動地位。
參考文獻:
[1]? 張榮剛.新聞敘事框架與新聞視角之關系[J].新聞與寫作,2004(6):20-22.
[2] [3] 臧國仁: 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M].臺北:三民書局,1999.
[4] 李新烽,李玉潔.沖突框架與中立轉向:2002-2016年BBC中非關系報道分析[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25(3):6-25+126.
[5]? 雷曉艷.報道框架、國家形象與新聞生產:《華爾街日報》的涉華報道研究(1979-2013)[D].華中科技大學,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