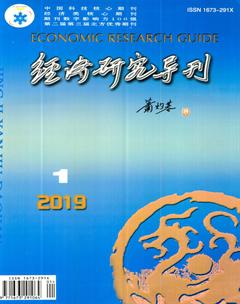農村項目制供給“內卷化”及其消解
張昊
摘 要:農村稅費改革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造成了巨大的沖擊,鄉鎮財政呈現出“空殼化”狀態,無法繼續履行其供給農村公共產品的職能。鑒于此種情況,國家及政府嘗試運用項目制供給這種轉移支付的方式來填補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空缺。但實際情況表明,這種供給方式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遭遇了“內卷化”的困境,即隨著供給投入的增加,供給效能卻絲毫沒有提高。從調整供求方向,完善供給機制,切實提高轉移支付效能出發,是消解“內卷化”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公共產品供給;供求偏離;供給效能;內卷化
中圖分類號:F323?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19)01-0009-02
一、單向主導與頂層設計:項目制供給運行機理及其內卷化
(一)農村公共產品的項目制供給運行機理
近年來,農村稅費改革給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方式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分稅制改革之后,基層政府喪失了之前擁有的依靠征稅得來的財權,不再具有自主籌資籌勞的能力,進而導致鄉鎮政府財政出現了“空殼化”的特征,同時也造成上級政府財權大于事權、基層政府財權遠小于事權的窘境。
項目制供給的運行機理,從項目制供給的內涵來看,它是指“中央或上級政府出于緩解基層政府財政壓力的目的所采取的一種轉移支付的方式”。從項目制供給具體實行過程來看,中央或上級政府為基層政府設計或提供某項目,并提供項目專項資金,各個地方政府通過公平、公開競標的方式去爭取項目,之后按照項目要求達到上級所要求達到的效果,并自覺接受上級政府的考核,最終獲取專項項目資金[1]。
(二)農村公共產品的項目制供給內卷化及其表現
1.項目制供給中配置失衡。早在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過渡時期,配置失衡問題就一直存在,當時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軟硬不均”,軟件服務設施與硬件設施不能夠匹配。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經濟文化水平相對落后,農民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農村的基礎建設、基礎設施等肉眼可見的公共產品上。在推行公共產品項目制供給之后,這種問題又進一步得到了強化,中央和上級政府近年來不斷增加轉移支付的比例,這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中央和上級政府對于基層政府的不信任。所以表現在項目制供給中,中央和上級政府作為項目的發放方,站在他們的角度上來看,他們會更加注重項目完成之后的考核與評估[2],硬件設施相對比較容易量化與考核,且發展變化會比較顯著。反觀軟件設施,大多數軟件設施都不是獨立存在的,且軟件設施通常需要一個漫長的周期才能夠出效果,所以相對來說量化考核的難度大。所以在項目制供給中,軟件設施通常被舍棄,這就直接導致軟硬不能平衡,整個項目制供給陷入困境[3]。
2.“官僚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項目制供給。項目制供給的初衷是增加公共產品供給的數量,提高供給的效能,填補基層政府由于“懸浮化”所造成的空缺。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雖然項目制供給是一種超越科層制的供給方式,但卻無法真正擺脫科層制運作中的通病;他們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考慮更多的是如何通過項目制供給的方式來提升自身的政績,由于項目與資金是一體的,出于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他們更傾向于發放一些“面子工程”的項目,同時由于項目制供給的連續性,這些“面子工程”往往是既有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這些供給嚴重偏離農民對于公共產品的需求。這就直接導致資金不斷投入后,卻由于供求偏離的緣故,實際的供給效能沒有得到提高,項目制供給陷入“內卷化”[4]。
3.競爭機制導致項目制供給的“馬太效應”。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項目的發放方會制定一系列要求去讓項目的競爭方(各鄉鎮)來匹配,這種變相的競爭機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項目競爭方通過改善自身條件來與項目匹配的積極性。但另一方面,這種競爭機制帶來了一種“馬太效應”:經濟基礎較好、先天條件占優的鄉鎮往往會爭取到資金、規模更大的項目,然后通過這些項目的運作進一步完善和提高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能力[5]。反觀那些經濟基礎比較薄弱、條件無法與所發放項目相匹配的競爭者,則會在項目制供給的競爭中不斷被邊緣化,直至被淘汰。加之在很多情況下,在一個項目中,基層政府需要拿出一部分資金與中央和上級政府提供的資金相匹配共同完成項目,這同樣也進一步加劇了分化。這種項目制供給中的“馬太效應”,直接加劇了項目制供給水平的分化,導致農村項目制供給呈現零散、錯亂、分配不均的消極狀態[6]。
二、結構性供求偏離與財事權弱化:深入剖析項目制供給“內卷化”
(一)“條線式”供給導致供求偏離
在農村公共產品項目制供給中,采用的方式主要是“條線”的方式,中央和上級政府主要依據其所要貫徹的政治目標及政治傾向,并將政治目標與政治傾向滲透于項目制中。所以,地方及基層政府在競爭項目的過程中無形中被禁錮于中央和上級政府設計的“枷鎖”中,加之其自身實力有限,進一步限制其在項目制選擇中的自主性。這就造成地方及基層政府在整個項目制供給中只能被動承載發放者的政策意圖,卻不具備資源分配的自主權。從長遠來看,這種方式錯置了農民的需求,將農民的真正需求消散于中央和上級政府的政策意圖與政策指向中。
(二)財政“空殼化”導致基層政府財權、事權弱化
中央和上級政府所發放的項目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貫徹了上級的政治傾向于政治意圖,但項目的載體及項目的具體實施是在農村,由于管理層級及管理幅度的原因,中央和上級政府只能夠負責宏觀的項目具體內容、競爭程序、考核評估機制的制定,但是項目的具體運作與實施則依然要落到基層政府身上,項目的運作與實施離不開基層政府的管理,而基層政府的管理又需要相應的事權做保障。
(三)過度功利化忽視了農民體驗與集體偏好
項目評估環節是整個項目制運作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它關系著項目實施主體在整個項目實施期間的成果檢驗,關系著項目實施方能否順利拿到項目資金,因此考核評估的指標必須具體、明確、清晰且具有可操作性。但在實際進行考核的過程中,由于項目所涵蓋的方面眾多,涉及的因素也不是單一、具體的,這就給考核單位造成了巨大的阻礙與困難。所以,他們選擇采取一種完全“數字化”的考核指標去進行項目的考核,這種“數字化”的考核指標僅僅能反映項目最終呈現狀態的水平[7],缺錯置忽視了項目實施過程中的農民體驗與集體偏好。由于地方財政“空殼化”帶來的“農民集體失語”,本該成為項目評估主要考慮因素的“農民體驗與集體偏好”,被迫于無奈的錯置、忽視。
三、創新多元整合:消解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內卷化”的必由之路
(一)創建“階梯式”資金補償機制
在項目制供給的資金分配時,往往是中央財政提供一部分資金,并要求基層政府相應提出配套資金,中央這樣做的目的是想通過這種方式建立一種中央政府與基層政府之間的合作機制,讓中央政府與基層政府共擔風險。但現實情況是,這種資金強行配套的方式嚴重拖垮了基層政府財政,導致本身就“空殼化”的財政進一步陷入危機。基于此種情況,可嘗試在項目制供給的過程中建立一種“階梯式”資金補償機制:中央財政的撥款數額不定,在整個項目完成、評估結束之后,以最終評估結果為依據,選擇一個平均指標,將最終評估得到的具體指標與其比較,將比較結果按照從高到底呈“階梯式”排列[8],在頂端的項目主體將獲得最多的資金,從上到下依次遞減。這種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給予基層政府財政一定的自主權,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基層政府投身于項目運作、管理中的積極性,也能逐漸將基層政府財政從“空殼化”的泥潭中拉出。
(二)創建“多維式”農民體驗主導的項目評估機制
在整個項目制供給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提供符合農民需求、農民體驗的公共產品,如果不能滿足這一點,所有的供給都只能是一紙空談,都只能是用來提高指標、獲取資金的手段和把戲。所以針對這種供求偏離的現象,在項目制供給中可以嘗試建立一種“多維式”農民體驗主導的項目評估機制,從多維度、多因素出發,由之前的“精英決策”轉變為“村民體驗決策”,不再只考慮項目的統一化、標準化。而要真正結合農民的需求偏好與民生體驗,從每一個項目所在村莊的特殊性出發,以村莊的實際情況為準去制定考核指標。并針對“農民集體失語”的現象,將農民的想法與建議作為評估項目的一個重要維度,將農民體驗植入項目內容,讓農民體驗影響項目開展,讓農民體驗主導項目的實施,真正讓發放到農村的項目能夠在農村立足并真正惠及到農民。
(三)創建“多元式”鄉村科技內生動力助推機制
前文提到,在基層項目制供給中,普遍存在一種“軟硬不均”的現象,即在供給中過于重視易于量化考核的硬件設施,而對于具有一定科技含量、對農村長期發展具有內生推動作用的“軟”項目,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在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中,提到了農村發展的兩大支撐,包括科技支撐和基礎支撐。
參考文獻:
[1]? 黎民.公共管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 劉紅云,張曉亮.多元視角下解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問題的路徑選擇[J].北方經濟,2007,(13):5-6.
[3]? 詹建芬.對公共產品短缺現象的困惑和釋疑[J].江淮論壇,2005,(1):8-9.
[4]? 林萬龍.中國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5]? 蔡秀云,李紅霞.財政與稅收[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8.
[6]? 朱鋼,賈康.中國農村財政理論與實踐[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6.
[7]? 何菊芳.公共財政與農民增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
[8]? 常偉.農村公共產品問題的歷史演進[D].合肥:安徽大學三農問題研究中心,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