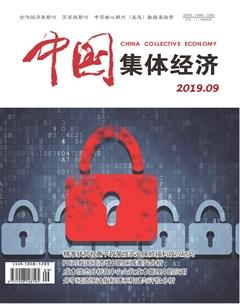精準扶貧視角下政策性農業保險福利效應研究
任石
摘要:文章基于四川省9縣市入戶調查微觀數據,從精準扶貧視角實證研究了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反貧困福利效應,研究表明30%低收入農戶由于陷入“貧困陷阱”,福利效應不顯著,而70%高收入農戶能夠利用農業保險平滑消費,極大提高社會的福利效應。最后,從政府精準補貼、實現自主造血,開發特色農險、提高精準覆蓋,普及農保政策、提高農戶意識三個方面提出政策建議,以有效促進農保扶貧。
關鍵詞:精準扶貧;政策性農業保險;福利效應
一、引言
精準扶貧戰略思想是我國農村扶貧開發的重要指導方針,也為農村保險扶貧運行開辟了道路。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已經連續十五年聚焦“三農”問題,從2004年提出要以“擴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的品種和區域覆蓋范圍”作為改革目標,到2017年再次重申脫貧目標并提出要“要進一步推進精準扶貧各項政策措施落地生根”,每年中央一號文件都對農業保險的發展方向做出了重要的部署。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進一步提出“支持貧困地區開展特色農產品價格保險,通過中央財政以獎代補等措施有效拓展農業保險覆蓋面和保費補貼”的戰略目標。
四川位于我國的西部地區,雖然近幾年農業保險扶貧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其貧困人口規模仍然很大,扶貧開發工作已經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 的沖刺階段,剩下的貧困人口貧困程度較深,脫貧的難度也就更大。受四川省的地理位置影響,干旱、洪澇等自然災害及流感病毒、農作物病蟲害等疾病頻發。作為傳統的以農作物多樣性揚名的農業大省,傳統的農業經營性收入依然是貧困地區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其生活生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業經營性收入的增長。2007年4月,財政部率先提出在四川、湖南、內蒙古、新疆、江蘇、吉林6省開展全國政策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試點工作。緊隨其后,四川省財政廳以及省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綱領性文件以保障政策性農業保險的順利開展。自開展以來,保險試點品種從最開始的小麥、水稻、玉米等少數幾個品種,到宜賓的能繁母豬保險,再到養殖業中的奶牛、育肥豬等各大品種的全面覆蓋,特別是近年來針對貧困地區量身定制的特色農產品保險,一是為支持藏區農牧業發展,積極開展“牦牛保”;二是“惠農保”造福彝區;三是“特農保”扶持彝區產業發展。四川保監會提出積極推動“扶貧保”產品在深度貧困縣落地擴面增量,針對深度貧困縣特點創新保險產品,開展特色農險,引導保險資源向深度貧困縣傾斜,加大保險保障廣度與深度。這從農業保險的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促進了農業保險精準扶貧的可能性。
雖然政策性農業保險在扶貧方面具有特有的機制優勢,但是從精準扶貧視角來看,四川乃至我國農業保險扶貧依舊還存在扶貧對象識別不精準、項目安排不精準、保險補貼不精準與扶貧到戶措施不精準等問題。
二、文獻綜述
針對農業保險參與精準扶貧,當前的研究大都是定性研究農業保險扶貧存在的問題以及保險扶貧模式的優缺點。付正等(2017)以保定市為例,從農戶、保險公司和政府多角度提出農業保險精準扶貧存在的問題:農戶對農業保險的認識不足,農業保險產品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李鴻敏等(2016)和陳新等(2017)基于河北省“阜平”模式提出農業保險參與精準扶貧的幾條路徑:政府精準扶持、保險公司精準開發、農戶精準教育,指出農業保險是精準扶貧的有效工具;黃延信與李偉毅(2013)認為農業保險扶貧問題的根源在于農業保險產品設計不合理,產品單一,大多都是實行統一費率和統一保額,農民的可自主選擇余地很小;譚正航(2016)研究提出,從精準扶貧視角來看,我國農業保險扶貧還存在扶貧對象識別不精準、項目安排不精準、保險補貼不精準與扶貧到戶措施不精準等問題,法律制度不完善是主要的原因。
在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福利意義的研究中,鄧維杰(2014)根據其對四川省79位各市(州)縣扶貧移民局負責人調查得出,四川省精準識別存在規模排斥、區域排斥和識別排斥,精準幫扶存在需求排斥和市場排斥等各種排斥現象,這極大地減弱了政策性農業保險參與精準扶貧福利效應。姚壽福(2016)利用我國1982~2014年的數據對農業保險的福利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從短期來看,農業保險對農業生產具有穩定作用,能夠促進農產品質量的提高和產量的增加,并對農業資源合理配置有顯著作用,具有很強的社會效益,而從長期來看,保障農業的順利運行,擴大再生產,最終實現社會效用的增加以及帶來社會福利的凈增加。這一結論在李軍(1996)、俞雅乖(2008)、鐘甫寧(2008)等學者的文中也能找到相同點。聶榮等(2013)利用其對遼寧省8個縣實地調研數據實證分析,提出微觀上農業保險有助于實現農戶自身福利效用最大化,而在宏觀上能夠促進農村社會福利保障體系進入良性循環。
國外學術界沒有“精準扶貧”這一理念,但是貧困是全世界都面臨的問題,他們主要從國家整體福利水平方面和政府補貼效應對政策性農業保險運行的福利效應進行研究。Richard(1982)利用福利經濟學理論模型研究得出,政府對農業保險進行補貼能夠有效的促進農民收入的提高,因為這極大降低了農民因災受損的程度,近似形成了穩定的補貼效應。隨后Yamauchi(1986)利用日本農業保險的案例對農業保險的穩定補貼效應進行了驗證,得出了相同的結論。Ozaki(2007)利用1993~2004年的數據對美國農業保險研究得出,農業保險能夠有效轉移風險,而政府較高的補貼可以促進農民對保險的需求以及提高對農作物的保障水平,進而增加農民的福利效應,這與Babcoke (2002)得出的研究結果相似。但在另一方面,Chambers(1989)運用帕累托最優約束得出政府過度的補貼會導致多風險作物保險失敗,農民會用農業保險代替傳統的金融工具進行盈利而不是為了規避風險,從而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這就違背了政策性農業保險設立的初衷。國外大多數學者認為合理的農業保險補貼制度不僅能夠穩定農戶收入、減小貧困程度,而且農業保險的正外部性可以保障農戶的基本收入,極大提高社會的總福利水平,許多的案例都表明政策性農業保險有很大的存在必要性。
綜上所述,農業保險具有消費的正外部性、合理配置資源、穩定農民收入、分散風險和促進農業發展的特點,目前學者主要針對農業保險扶貧模式、財政補貼、政府調節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但大部分相關成果缺乏精準扶貧理論指導,研究思維有些單向,對農業保險扶貧福利效應更是鮮有研究。國外學者對農業保險運行福利意義的研究主要從國家整體福利水平方面進行的,很少有從微觀數據對農業保險的福利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的,本項目的研究主要從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反貧困福利效應進行。
三、數據來源、變量選取與描述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本課題組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對農戶戶主的入戶調查微觀數據。綜合考慮四川省各貧困地區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實施情況與經濟發展狀況,選取調研地點,采用隨機抽樣和分層抽樣相結合的方式,向選中的農戶發放問卷,收集了包括樣本農戶的基本信息、政策性農業保險相關信息及消費需求等,收回問卷482份,最后進行數據處理,提出不真實的問卷及刪除離群值,最終得到有效問卷443份,問卷有效收回率為92%。
(二)實證模型設定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農業保險反貧困的福利效應,考慮到被解釋變量是連續型變量,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Consume=β0+β1subsidy+β2insurance+β3evaluate+β4Controls+μ(1)
本文利用消費作為反貧困的替代變量,為了探究影響消費的因素,從農業保險、家庭特征、戶主特征、家庭農業投入四個維度來研究。
(三)描述性統計
在443份有效問卷中,農戶投保率為40.2%,說明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覆蓋率偏低,結果還發現有75個農戶不知道政策性農業保險,占總數的17%,其表示從來沒有聽說過,說明農業保險的宣傳力度還不夠。表1呈現了本文模型中主要變量的說明及描述。
四、實證結果分析
對于貧困地區來說,農業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來源,收入越高,家庭消費占總收入的比重就會上升,所以家庭的貧困程度可以通過家庭消費行為直接反映。本文利用家庭消費支出作為家庭貧困程度的替代變量,假設越貧困的家庭,家庭消費越低,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反貧困的福利效應就越顯著。
表2回歸結果顯示,第(1)是全樣本下的回歸結果,第(2)、(3)列分別是參保農戶樣本和非參保農戶樣本的回歸結果。政府補貼與消費支出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全樣本中,把未參保農戶的政府補貼設定為0,表明農業保險補貼效應能夠緩解貧困,增加農戶的社會福利。教育水平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明消費會隨著教育水平的上升而增加,與未參保農戶對比,參保農戶的系數值較大,可以認為教育水平對參保農戶的邊際影響更大,可能是由于教育水平會提高認知能力,使農業保險的保障效應得到驗證。農業收入占比與消費顯著的正相關,且參保農戶的邊際效應更明顯,說明收入能夠極大促進參保農戶消費,減弱其貧困程度,從而也驗證了農業保險的反貧困效應。
為了進一步更準確研究,本文將全樣本分為低收入和高收入,以30%為界,再分別對參保和未參保農戶進行分樣本回歸, 表2中第(4)和(5)列分別是低收入農戶參保和不參保的結果,可以看出其系數基本都是不顯著的,也就是說收入、儲蓄、教育水平等因素的變化不會明顯影響消費,可能是由于低收入者正處于脫貧的初級階段,沒有財富的積累,說明其可能正處于“貧困陷阱”中,這時需要進一步實現脫貧目標。第(6)和(7)列分別是高收入的參保和未參保農戶的回歸結果,其系數的正負和顯著程度與表2大致一致,說明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反貧困福利效應在高收入農戶得到了驗證,其有能力實現消費平滑,這正和政策性農業保險的作用一致。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通過對四川省9縣市微觀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政策性農業保險在精準扶貧視角具有顯著的福利效應,其能夠促進農戶家庭消費,具有顯著的反貧困的福利效應。故本文提出如下三點建議。
第一、政府精準補貼,實現自主造血。政府加大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補貼品種和范圍,因地制宜,大力發展特色種植和特色養殖農業基地,要充分發揮家庭農場和種植大戶的帶動和組織作用,實現“先脫貧”積極帶動“后脫貧”的轉變、從“政府輸血”到“自主造血”的脫貧目標。
第二、開發特色農險,提高精準覆蓋。保險公司應根據貧困地區不同的農業發展情況以及物質生活水平的的差異來制定因地制宜的特色農業保險,如四川貧困地區的“牦牛保”、“惠農保”、“特農保”等,讓每個農戶都能選擇自己需要的農業保險,有效提高投保率。
第三、普及農保政策,提高農戶意識。農戶是農業保險的主動方,而每個決策者都是最大化自己的福利效應來制定生產決策的,所有只有農戶自己對理賠程序和保費補貼等有了很好的了解之后,他們才會積極參與投保,享受農保扶貧帶來的好處。目前貧困地區的農戶農保意識不強,需要政府予以引導,加大宣傳。
參考文獻:
[1]付正,宋蔓蔓,徐佳怡. 農業保險實現精準扶貧的路徑分析——以保定市為例[J].河北企業,2017(03).
[2]李鴻敏,楊雪美,馮文麗,等.農業保險精準扶貧路徑探索——基于河北省的“阜平模式”[J].時代金融,2016(30).
[3]黃延信,李偉毅.加快制度創新 推進農業保險可持續發展[J].農業經濟問題, 2013(02).
[4]譚正航.精準扶貧視角下的我國農業保險扶貧困境與法律保障機制完善[J]. 蘭州學刊,2016(09).
[5]鄧維杰.精準扶貧的難點、對策與路徑選擇[J].農村經濟,2014(06).
[6]姚壽福,馬理瑤,粱曉鳳.關于加快農業保險發展的思考——基于我國農業保險經濟效應的實證研究[J].西部經濟管理論壇,2016(01).
[7]李軍.農業保險的性質、立法原則及發展思路[J].中國農村經濟,1996(01).
[8]俞雅乖.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補貼政策及績效——浙江省“共保體”的實踐[J]. 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5).
[9]孫香玉,鐘甫寧.對農業保險補貼的福利經濟學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8(02).
[10]Just R E, Rausser G C, Zilberman D. 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s[J].Cudare Working Paper,1982.
[11]Yamauchi T. Evolution of the crop insurance program in Japan[J].1986.
[12]Ozaki V A, Shirota R. The Experience with Crop Insurance in the USA: Evolution and Performance[J].Funenseg.org.br,1970.
[13]Chambers R G. Insurability and Moral Hazard in Agricultural Insurance Markets[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9(03).
*基金項目:省級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項目“精準扶貧視角下農業保險運行模式及福利績效研究——基于四川省入戶調查微觀數據證據”(項目號:201710626080)。本研究為四川農業大學創新訓練計劃項目資助。
(作者單位:四川農業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