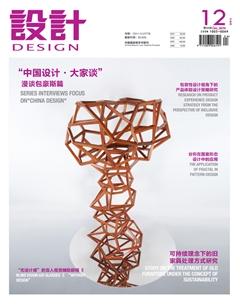周志:包豪斯與生活工藝-現代設計語境下手工藝的“作”與“用”
湖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在包豪斯100周年之際開展了“紀念包豪斯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來自國內外的近30多位藝術設計、設計教育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及設計工作者在兩天內進行了多場專題報告,共同探討包豪斯的前世今生、現實意義,探索未來中國藝術設計教育的前進方向,推動中國藝術設計的飛躍式發(fā)展。《裝飾》雜志編輯部主任,副編審、設計學博士周志應邀進行了以包豪斯與生活工藝:現代設計語境下手工藝的“作”與“用”為題的主題演講。
生活工藝是日本當代的一種設計,或者說是手工藝的一種現象,為什么把這兩個聯系起來?因為這兩者聯系起來的時候,實際上是目前國內的一個現象,把手工藝擴展到非遺、傳統(tǒng)工藝,或者是做過與鄉(xiāng)村有關的項目。這到底是一個虛假的火爆,還是一個有著現實困境的現象?
首先講包豪斯,我給它起個名字叫“被隱藏的手工制作”。為什么是“被隱藏的”呢?大家都知道早期包豪斯實行的是工坊制度。我們一直認為包豪斯是一個設計學校,但是實際上早期的包豪斯特別強調跟工藝的結合,包括它的基礎課程和工作坊訓練。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于大多數的城市來說,手工藝都是一個重要的制造業(yè)基礎,那時候機器出現了但并沒有完全占上風。魏瑪這座城市也是由傳統(tǒng)手工藝支持經濟,當時魏瑪是整個城市的轉型。格羅皮烏斯在1915年成為魏瑪工藝美術學校的校長,幾年之后他就受命開始將美術學院和重開張的工藝美術學院進行合并,建立了包豪斯。“Bauhutten”這個詞在中世紀實際上就意味著手工藝,這是它的根。當時的宣言為:“建筑師們、畫家們、雕塑家們,我們必須回歸手工藝!因為所謂的“職業(yè)藝術”這種東西并不存在。藝術家與工匠之間并沒有根本的不同。藝術家就是高級的工匠。由于天恩照耀,在出乎意料的某個靈光乍現的倏忽間,藝術會不經意地從他的手中綻放出來,但是,每一位藝術家都首先必須具備手工藝的基礎。正是在工藝技巧中,蘊涵著創(chuàng)造力最初的源泉。”這個是包豪斯1919年的時候的提出的宣言,可以看出來對手工藝的特別強調。包豪斯真正的課程基礎在于基礎課程和工作坊訓練,正是這兩者使它能夠探索兼具藝術創(chuàng)造與手工制作、手工技能的綜合性人才。也就是說,包豪斯最早探索藝術創(chuàng)造精神的前提下,還有一個工藝技能,這兩個都是要同時訓練。“雙師制”背后隱藏著包格羅皮烏斯的一個個人的想法,就是包豪斯并不是一所工藝美術學校,之所以采用的是手工藝的訓練技能,目的是為大規(guī)模生產設計做準備。
比如包豪斯設計的燈,有多少人知道這也是手工制作的?威廉·華根菲爾德曾經說過,他們在展會上擺放的時候是成排的,顯得像是批量化生產。他也提到了,價格始終是無法忽視的障礙。包豪斯當時實際上是試圖通過一種傳統(tǒng)的手工制作的方式來探索一種現代機器美學。格羅皮烏斯只是選擇了適合其包豪斯新計劃的外觀。因為,在此時顯現工藝的感性會顛覆包豪斯試圖建立的機器風格,即便創(chuàng)建這種風格的手段仍然完全是手工的。這時候如果你要強調工藝性的話,就跟包豪斯所強調的、所追求的、所探索的這種現代主義機械生產的精神相違背,所以他刻意要把這個隱藏掉、模糊化,不去宣傳它。
這里實際上就形成了一個悖論,手工制作和機器制作是特別難以彌合的。包豪斯是一個很理想的、充滿探索精神的學校,但它自己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悖論是美好、昂貴、丑陋和低廉之間如何平衡。那么,像華根菲爾德那樣強調能降低成本,又能保證美觀,工藝如果不能實現,通過什么才能實現?實際上,到包豪斯后期,包括格羅皮烏斯在內的很多人已經意識到這種方法有問題,所以它的口號也變了,從“藝術與手工藝:一個新的統(tǒng)一”,改為“藝術與技術:一個新的統(tǒng)一”。研究包豪斯要注意這種轉變。
后期的包豪斯實際上已經找出一種新的手段來彌合批量生產和造型之間的關系。走得更遠的是烏爾姆,直接就把設計的任務定義為生產,設計師的任務就是從設計物品的風格開始轉向對生產過程本身的研究。所以烏爾姆的課程中包含了大量的這種生產方面的技術、工程方面的這種課程,甚至包括社會學、消費學、傳播等方面的課程。也就是說,烏爾姆已經不把設計看作是一種藝術行為、手工藝行為,而是一種生產行為。設計,不管是研究還是發(fā)展,最終是要以成果來呈現。真正把烏爾姆的和包豪斯這一貫的思路延續(xù)下來的是博朗,真正奠定了德國設計在世界的地位。博朗是一家重視設計的生產企業(yè),從管理到設計到工程制作再到銷售,是一條龍的整體,然后進行設計思維的灌輸,所以它的設計才能夠真正地貫徹到整個生產,一直到銷售,整個渠道才能夠貫通起來,單一所學校是完不成這個任務的。
總結來說,早期包豪斯試圖通過手工制作的方式來尋找符合時代要求的、適合機器生產的產品美學,但是這個做法存在著悖論——風格和制作技術、美學和成本之間的矛盾。后期包豪斯拋棄了原有的手工作坊式的教育,改為提倡藝術與技術結合,所以取得了一些進步和發(fā)展。烏爾姆在找個基礎上走得更遠,主張設計為生產服務。最終,在博朗公司,一種真正的設計美學得以塑造。也就是說,真正在德國推動設計向前發(fā)展的是把設計作為一種工業(yè)制造的生產過程并推動到盡頭的企業(yè),這才是關鍵。
講日本,得從民藝運動開始,因為東方的現代設計跟西方不太一樣,西方的現代設計根本出發(fā)點還是從經濟、生產的角度進行思考,但日本跟中國一樣,有一個文化主體性存在的問題。如何在保證現代性的同時,還要保證文化主體性的存在,是中國、日本當時都面臨的問題。所以我要提到的民藝概念,是由柳宗悅開始提倡的。后來擔任民藝館館長的濱田莊司和河井寬次郎是他的重要支持者、合作者,兩位是工藝家,柳宗悅是個純理論家,從來不做工藝。第四位館長是柳宗悅的兒子柳宗理,第五位是深澤直人。大家都知道深澤直人,都知道無印良品,但很少人知道深澤直人本身也是民藝館的館長。
柳宗理是一個工業(yè)設計師,但是他繼承了他父親民藝的思想,并把民藝的思想貫穿到其工業(yè)設計之中,他是研究日本現代設計特別關鍵的一個人物,而且他特別致力于在民藝和設計之間搭起一座橋梁。他曾經講到,與工業(yè)設計有關的人要注意到,用手工制作的工藝品,一旦供庶民使用,就必然產生出燦爛的美。手工藝必須追求手工制作的美,而工業(yè)設計則應該尋求機械生產的美。但是,與人類生活有關的物品所產生的美感是同樣的。
深澤直人為無印良品做設計的時期正是日本經濟的一個轉型期,無印良品很敏感地抓住了這個時期,不再是強調刺激消費,而是強調設計要回歸生活。當時很多同質化產品產生,與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契合,所以他主張從里邊掙脫出來,尋找一種跟我們生活相關的設計。這是作為一個設計師的深澤直人所思考的,也是他后來兼任民藝館館長的原因。
“生活工藝”這個詞差不多有近20年了。20世紀90代末至今,日本工藝發(fā)展的一個新趨勢,很多工藝家都認為出現一個新的現象,體現出這個時代對生活與生計的關心。從柳宗悅的民藝到當下的生活工藝,在這種藝術的范式轉換中,民族主義的情緒、階級論(平民主義)的色彩,從藝術中逐漸模糊乃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日常生活的回歸與關注、對平常之物更為細致的凝視與移情。
生活工藝為什么會興起?實際上大概的可以歸為四個原因:1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日本泡沫經濟破滅,開始重新從使用價值的角度來理解物品產品;2當時整個日本設計行業(yè),刨去生活工藝和手工藝品,已經發(fā)展得規(guī)模非常大,制造業(yè)也非常大,但這個時候會帶來一種審美疲勞;3日本對于文化保護的重視,對手工藝傳承和發(fā)展的一種關注,是自始至終都有的,我們國內是從近幾年來開始注意和提倡;4民藝思想的影響,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影響。
所以生活工藝的發(fā)展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它并不是由一個團體或一個人或一個組織發(fā)展,而幾乎是全面的。這背后也隱藏著很多的概念,從商業(yè)到經濟到生活到工藝家到設計師,幾乎人人都在這個時代之中,所以,與其說它是一種現象,還不如說是一種潮流。日本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潮流?在日本,所有人的身份是融合的,擺脫消費社會,面向新世紀,重新思考物與人之間的關系,從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之中尋找美術工藝的存在方式,有大規(guī)模的一些雜貨鋪,他們還出了自己的雜志。在這一個時間段,這樣的雜志有數十本,在推廣這種生活方式、生活工藝這種傳播的思想,包括它推動的生活理念。一種精致但健康、自然又貼近生活本源的生活方式,對生活方式的一種推崇,也通過雜志來推廣各種展覽。而且展覽的思考和所貫穿的理念是統(tǒng)一的,甚至有一批人在致力于同類型的展覽,或者是不斷開設同類型的展覽,尤其是松本手工藝祭。
還有影視紀錄片也很有意思。為什么中國手工藝在推廣和傳播方面沒有力?我發(fā)現一個特別有力的例子,就是章丘鐵鍋,但它不是通過手工藝節(jié)目而是食品節(jié)目推動的。因為鐵鍋是拿來用的,你不說拿這鍋做的肉香,就沒人去買。手工藝的關鍵在于用,你用的好才會有人去關注它,你只強調它的制作、它的精美華麗,大家頂多很遠地看一看,你必須跟人的生活產生聯系,人們才會有消費和購買的欲望。
總結來說,手工藝不強調手工制作的精致與精巧,價格位于中高檔,一般老百姓可以買得起的,可以小批量生產,允許機械化生手段介入,不強調個性特色,但強調易用性和材質的親和性,強調生活方式的塑造和空間環(huán)境的塑造,尤其注重對大眾樸實的生活方式的塑造和健康的消費價值觀的傳播,這是我們最欠缺的。
所以最后回到這個話題,設計到底是為了生產還是生活?當代手工藝的作用在于“做”還是“用”?如果說,在德國,德意志聯盟、包豪斯、烏爾姆、博朗,從100年前所做的努力,是在舊時代下的探索和重塑生活;那么現在日本在做的事情,就是回歸生活和反思生活。在物質極大豐富的情況下,其實我們不僅要去探索一種改變現代生活的方式,更要反思已經存在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問題。
如果說,包豪斯更專注于技術和造型方面的考察和探索精神,關注手工藝的制作,試圖從制作方面尋找手工藝對于設計、產品促進作用的話;那么生活工藝并不關注“做”,它更關注產品出來之后有沒有人去買,有沒有人去用,更關注傳承的文脈,衣食住行等使用方面,更關注的是生活。所以,如果把這兩者進行一下比較,包豪斯所體現的是一種制作精神探索,最后的工匠精神是凝聚在所有的生產企業(yè)之中,而不是手工藝制作中。生活工藝關注的是致用的美,就是關注于每個人的生活態(tài)度的塑造。包豪斯更多的目的是生產的一種再組織、再發(fā)現,生活工藝更關注生活的一種塑造手段。包豪斯最終的設計必須要跟生產企業(yè)合作,而生活工藝則要更注重向大眾傳播的手段和方式。
因此,個人認為,在設計語境下,手工藝研究的未來,第一在于深化技術研究,注重與生產企業(yè)的聯合,以工匠精神注入當代產品;第二在于加強對消費觀念、生活方式、使用情境等方面的研究;第三在于通過報刊、電視、展覽、網絡等途徑擴展大眾傳播工作;最后是樹立樸素、綠色、可持續(xù)的使用價值觀、消費價值觀。
本文由紀念包豪斯一百周年誕辰國際研討會現場內容整理而成(湖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