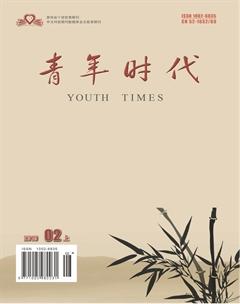真愛勿言
胡赟
摘 要:宗白華先生的短詩《我們》以一種絕對包容的姿態講述了愛情的美妙存在方式。作品站在至愛的角度,超越了世俗性愛情觀念的牽絆,以無拘無束的方式展示了純粹而明凈狀態的愛情給人的內心帶來的和諧感。在作者看來,愛是生命的本能,愛要有一顆淳明的心,而這顆淳明的心是屬于哲學的。從某種角度而言,宗白華先生的詩歌《我們》超越了愛情的一般形態,進入到了生命哲學的高度。
關鍵詞:宗白華;《我們》;愛情
愛情是文學作品永恒的主題,亦是連接生命體與生命體的核心元素。而愛的表達方式卻各有千秋。詩人宗白華先生的作品《我們》將愛的純粹、明凈、動人推向極致。全詩共七句,透過簡單卻不失深厚力量的文字再一次讓我們感受到文學作品的可貴之處不在于篇幅之長、情節之曲折、抒情之震撼。《我們》將一切復歸平靜,在寧靜又不失悠遠的狀態中傳達了最為圣潔的愛,“一切終將黯淡,惟有被愛的目光鍍過金的日子在歲月的深谷里永遠閃著光芒。”愛之深,卻無言,呈現的是中國古典詩學中不著一字而盡得風流的雅韻。
詩歌的標題是一個簡單的人稱代詞——我們。“我們”這一代詞從現代漢語的角度來看,相對于第二、第三人稱是最有親和力的選項。詩歌的題目從一開始就醞釀了一種親切的氛圍,只需要有人的出現,可以淡化外圍的一切。簡單的一個代詞奠定了詩歌的基本品格,即內心深沉的親密召喚。這樣的發自內心的情感生來就具備凝重的凝聚力量,是不需要喧嘩與騷動的。這也是人的情感的一種常態。文學作品在幾千年發展的過程中,常態反而失去了正宗地位,繼而被“歇斯底里”所取代,從某種角度而言,內中折射的是文學自身發展的一種焦慮感和迷失感。盡管“工業社會的語言里,物理、生物和其他各類工業方面的技術詞匯部分已經很發達,并且仍在發展。從更普遍的情況看,有些領域一旦屬于有代表性的活動或者富于文化表征,就會出現一套特別豐富的稱謂詞。”但后來者的新鮮和數量的劇增,并不一定和生命內質相關聯,更多的只是媒體時代的語言表象,惟有內含生命提純能量的作家才能做到舉重若輕,重歸文學的本體位置,這正是詩歌《我們》帶給大家的永恒性思考。同時,“我們”的指代又是及其寬泛的,它可以包容一切形式的相愛者,必備前提則是愛情的在場。我們指稱的對象可以從“我們倆”延伸到內心所有深懷著愛的人。這樣的包容性不僅是當前文學作品的創作者缺乏的一種情懷,更是人在發展自我的過程中產生狹隘主義視角的致命性弱點。而宗白華以一種輕盈的方式解決了人自身的自我負面性發展的重要傾向及其問題。
詩歌前兩句“我們并立天河下。人間已落沉睡里。”描述的是相愛雙方所處的一種情境。兩句內容以對比的方式展示了相愛雙方內心的強大熱量。夜深人靜了,情感處于相對平靜狀態的人們已經進入“深睡眠”狀態,這是人類生活的基本時間表,是一種常規行為。而非常規的行為則是那些情感生活處于波動期的人們。“我們”作為其中之一例被愛充實得忘乎所以,夜不能寐,所以必須借助外在的方式去表現、展現出自身的愛,使內心逐漸獲得一種平和。于是,在空曠的天河下,出現了我們并立的身影。而正是這種空曠,使得我們有了釋放愛的空間。詩句有著重要的圣化和神話愛情的傾向。在作者看來,愛是人類情感的最高形態,“人間”二字可資作證。常態中的人們,生活得平庸,內心被世俗生活所侵壓,已經日益遠離了某種激情。而身處愛情中的“我們”卻可以拋卻塵世的煩惱,進入到精神生命的極致狀態,去享受圣潔的愛情。在宗白華的心靈世界里,心中是否有愛是對人群性質區分的一個重要標志。所以,詩歌要贊頌的并不是可一一對應的愛情對象,而是人類需要的一種愛的狀態。這是詩人從審美的角度對人類精神生活的某種期待和想象。簡單的兩句詩既可以作為實寫處在戀愛狀態中的人的情狀,又可以作為虛寫對充滿愛情的人世間的一種向往。但無論實寫虛寫,作品都沒有簡單、淺表地通過語言來對愛進行釋義,而是通過客體的行為形象地使人通達愛的獨特存在。如此朦朧的表達方式一方面是宗白華先生所鐘愛的,另一方面又是詩歌品格的內在要求。“在一個藝術表現里情和景交融互滲,因而發掘出最深的情,一層比一層更深的情,同時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層比一層更晶瑩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為景,因而涌現了一個獨特的宇宙,嶄新的意象,為人類增加了豐富的想象,替世界開辟了新境,正如惲南田所說:‘皆靈想之所獨辟,總非人間所有!”
天河之下,風景無限,卻不入敘述者的法眼。只有“天上的雙星,映在我們的兩心里。”天上的雙星自是象征愛情的牛郎、織女星。而對于相愛的二者來說,世界的意義正在于愛情本身,其它都形同虛設。所以,才會出現心中有什么,眼中才有什么的排他性景觀。也就是說,愛情成為了“我們”精神世界的主導力量。而這種愛具有一種超越性的力量,它可以排除外在、世俗世界所有的敵視狀態,以一種絕對自我的方式而存在。愛情本是有排他性的,而作品中的愛情因為濃郁之至更加將這種排他性推向了頂峰。詩句巧用映襯的手法,在現實龐雜的世界里剝離出了雙星和兩心,對其內在意義進行對接,實在有巧奪天工之效。無論在語音還是在語義上,詩句都體現了水到渠成的自然感。而更不得不讓讀者感嘆的是,愛情的純粹性、純真性也得到了徹底的表達。在全力排除外在干擾之后,“我們”共同接受雙星的信號。也就是說,真正的愛情可以超越世俗力量的博弈而達到純凈的質地。更讓人感動的是,“兩心”互相的體貼、融合的過程是春風化雨般溫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介入力量。所以,與其說“雙星”映在了“兩心”,不如說“兩心”照亮了“雙星”,幾千年前的神話故事,如果沒有代代相傳的愛情故事作為注腳,美麗的故事最終將顯得虛渺。人間、天上在此形成一個環形結構,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所以,愛情的力量是超越時空的,它的美妙之處就在于它不會出現斷層現象,因而,也有著持久和旺盛的生命力。從這個角度而言,就不僅僅是愛情是否美好的問題,而是人類因為愛情而獲得了精神的相通之處,獲得了永恒的不可磨滅的風景。宗白華先生的高妙之處在于,世界性的話題可以巧妙地濃縮在一個簡單的意象之中,真正做到了超凡脫俗。
相愛的“我們握著手,看著天,不語”,似乎有違愛情的常態。在一般的意義上而言,愛情是充滿溫度的,而且是高于常溫的。所以,在表達愛情的過程中至少需要把這種溫度慢慢釋放出來,最終達到一種和諧的相處。而宗白華先生的路數卻是一上手直接通往和諧。這個過程具有三種可能性:其一為——我們已走過那個高溫期而復歸寧靜;其二為——天生和諧的相處方式是詩人心中向往的至境;其三為——我們的生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相通性,而這種相通性可以剔除外圍干擾,直接通往和諧佳境。詩歌之美恰恰在于只言片語當中的多義性及其無限可能性。而不管此種和諧屬于哪種形式,但基本代表了宗白華先生的愛情美學觀念,即在靜謐的過程中感受愛情的無限豐盈,甚至走向愛情的潔癖和唯美。外在所有物質性的和介質性的行為和動作都將作為一種干擾因素被排除,包括類似于“牽手”、“情話”這樣的戀愛必備品。而剩下來的僅僅是在一個獨立甚至凝固的時空里,感受愛本身的存在。這樣干凈的愛是不能言明的,也是毋須言明的,它需要的是“我們”雙方心靈的碰撞。而“兩心”在前此就彼此讀懂了對方,因而,所有的動作和語言都顯得多余。“許多人誤解情感思想和語言的關系,就因為有一個第三者——文字——在中間攪擾。”在此,愛情因為減少了外在的負累反而顯現出了自由奔放、無拘無束的姿態,它不用考慮任何所謂外在文化及文化疊加的思考,只需要一心奔赴愛情本身,獨自品位和享受,進入真正唯愛情獨尊的境界。或許,從這個意義而言,作者的描述尚屬于脫離了現實生活的唯美想象,但詩歌作為文學作品的一種是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的。在生活中不能實現的,我們可以在文學作品中抵達,也算是人生的一種快慰。
當所有的心照不宣被取締之后,“一個神秘的微顫,經過我們兩心深處。”至此,“我們”的愛情以一種“神交”的形式表達出來。“戀愛因此可以說是宇宙的意義。”也就是說,從最初映出“雙星”到而今的進入“兩心深處”,“我們”的愛情已經逾越了一個階段,從而走向心領神會的高級形態。從而,美好的愛情感覺不期而至。在作者看來,愛情是無法解釋的一種情感連接的密碼,所有的世俗的程序都可以取消,而唯一可以連接愛情的紐帶就是心靈的呼應。而所謂的神秘實際上是不神秘的,但卻可遇不可求。與其說是神秘的微顫,不如說是難得的微顫。
整首詩歌作品,短短七句,卻寫盡了人世間最綿長、悠遠的愛。愛不難,愛走向圣境卻是生命的一種修煉。
參考文獻:
[1]周國平,《人與永恒》,北岳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頁。
[2](法),海然熱,張祖建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68頁。
[3]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頁。
[4]朱光潛,《詩論》,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89頁。
[5]周作人,《生活之藝術》,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