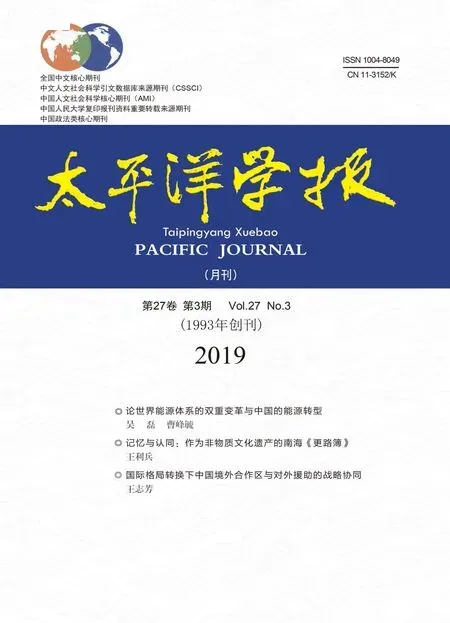“美國優先”及其對美韓同盟的影響探析
楊 悅 張子介
(1.外交學院,北京 100037;2.天津外國語大學,天津 300204)
“美國優先”自問世之日起就飽受外界的質疑,批評者認為其過于激進、充滿民粹主義、顛覆了戰后歷屆美國政府的內外政策路線。作為一套執政理念,“美國優先”確實存在諸多不成熟的地方。其內容蕪雜,散見于特朗普內閣成員各種演講及政府出臺的各種報告之中;內在邏輯鏈條不夠清晰,不同時期、不同閣員對其所做的表述間存在著不小的差異;理論方面也乏善可陳,流于口號和情緒化的表達。即便存在著諸多不足,“美國優先”卻動員起美國社會中部分利益受損群體的參政熱情,幫助特朗普成功問鼎總統寶座,并且已經開始在政策領域指導特朗普政府的內政外交實踐,而這部分內容極具政策價值和學理價值,又時常為評論者所忽視。本文旨在剝離“美國優先”情緒化與反邏輯的部分,全面闡述“美國優先”產生的社會基礎,從現實主義角度詮釋“美國優先”的思想內涵,同時從特朗普政府各種演講、報告中提煉出一套中性的分析框架,并以美韓同盟再調整為例,運用上述分析框架從制度和國際行為體層面分析“美國優先”對美韓同盟的影響,從中揭示特朗普政府同盟外交的特點及其可能對國際秩序造成的影響。
一、“美國優先”的緣起、思想內涵及其分析框架
1.1 “美國優先”的緣起
冷戰結束后,美國失去了蘇東集團這一最強大的外在制約因素,開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國際日程。在“華盛頓共識”的影響下,一大批發展中國家放棄了對本國金融市場的管制,方便了美國資本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要素配置,從而開啟了新一輪全球化進程,為美國帶來近三十年的經濟繁榮。在這個過程中,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積累了巨量財富,它們積極地塑造美國的國內政治,將自身在全球化中的獲利轉化為政治優勢。與此同時,以藍領工人為代表的低技術勞工階層卻承受著工作機會流失、收入下降帶來的負面效應,逐漸從中產地位跌落下來。西方經典理論認為,進口廉價產品在減少發達國家相關產業部門工作機會的同時,會在出口導向型部門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從而保證整個社會的充分就業。在現實中,新工作誕生的速度遠遠趕不上舊工作流失的速度。把工人從低收入工作部門驅趕出來只會加劇失業、無助于增長。①See Joseph E.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Re?visited:Anti-Globalization in the Era of Trump,W.W.Norton& Com?pany, 2017.然而,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長期為全球化受益者所壟斷,出現了所謂的“排斥政治”(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即將那些在全球市場中既不能扮演消費者也不能扮演生產者的劣勢群體從社會中排斥出去,形成了富者愈發得勢,貧者愈發沉淪的惡性循環。②Ankie Hoogvelt,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8.最終,全球化利益受損者只能以民粹主義運動的形式打破政治上的僵局,“美國優先”正是這一過程在美國重復上演的結果。
西方學者研究表明,如果將從中國的進口額平均到每個工人身上,那么進口額每增加1 000美元,美國的就業人數就會減少0.6%,制造業則減少0.18%,失業率上升0.22%,勞動參與率下降0.55%。③David H.Autor, David Dorn and Gordon H.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3, No.6, 2013,p.2143,轉引自周琪、付隨鑫:“美國的反全球化及其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太平洋學報》,2017年第4期,第6頁。由于美國白人藍領就業崗位主要集中在制造業,與全球化相伴而來的產業外移對他們日常生活造成的影響頗為顯著。據統計,1999年至2013年,美國45~54歲白人無高等學位群體的死亡率每年上升0.5%。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將這一現象稱為“死于絕望”。④“The Forces Driving Middle?Aged White People’s‘Death of Despair’”,National Public Radio, March 23, 2017, https://www.npr.org/sections/health-shots/2017/03/23/521083335/the-forcesdriving-middle-aged-white-peoples-deaths-of-despair.與此同時,美國社會的代際流動速度正在日趨放緩。2018年,美國收入超過父代的子代占全體子代總數的比例較1980年降低了3%。⑤Jonathan Davis and Bhashkar Mazumder, “The Decline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fter 1980”, p.1, Chicagofed, 2017, ht?tps://www.chicagofed.org/~ /media/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017 /wp2017-05-pdf.pdf.出身位于美國收入最底層1/5家庭的子女上升到最頂層1/5的幾率只有7.5%,低于英國的9%、丹麥的11.7%和加拿大的13.5%,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位居中后位置。⑥Raj Chetty, “ Improving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Mobility: New Evidence and Policy Lessons”, p.37,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https://www.stlouisfed.org/publications/bridges/fall-2016/improving-opportunities-for-economic-mobility.
此外,白人藍領階層還要面臨新移民帶來的職場競爭壓力。世界體系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核心國家向邊緣國家擴散,打亂了邊緣國家的經濟、政治結構,導致大量人口從原來封閉的社會遷移到其他地方,觸發大規模跨國移民現象。⑦See Saskia Sassen,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由于美國的經濟影響力輻射到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受到美國工資、福利和創業環境的吸引而選擇移民。2000年至2010年,有1 000萬移民涌入美國。①Philip Martin, “ Trendsin Migration to the U.S.”,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May 19, 2014, https://www.prb.org/us-migration-trends/.和本地勞動力相比,移民較少受到接收國規范的制約和保護,具有較強的商品屬性,更受接收國雇主的青睞。雙重勞動力市場理論(The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認為,發達國家的就業市場已經分化為本地人占據的高收入、高福利、工作環境優渥的高級就業市場和由移民占據的低工資、低福利、工作環境惡劣的低端就業市場。②Michael Piore, Birds of Passage: Migrant Labor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52-53.因此,從整體上看移民對美國就業市場造成的沖擊并不大。但是對于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藍領階層而言,移民帶來的“擠出效應”就非常明顯了。1994年到2000年,移民占據了新增低于收入中位數工作的58%,③Erik Olin Wright and Rachel E.Dwyer, “The Patterns of Job Expansions in the USA: A Comparison of the 1960s and 1990s”, Socio-Economic Review, Vol.1, No.3, 2003, p.309.導致白人藍領階層的收入降低了4.7%。④George J.Borjas and Lawrence F.Katz, “The Evolution of the Mexican-Born Work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George J.Borjas ed., Mexican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13-15.轉引自付隨鑫:“美國的逆全球化、民粹主義運動及民族主義的復興”,《國際關系研究》,2017年第5期,第36頁。
同職場競爭相比,全球化給保守白人帶來的文化不適感則更為強烈。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美國的社會制度是由18、19世紀以集體的形式移居新大陸的英國開拓者確立的,他們帶來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構成了美國認同的核心組成部分,即新教倫理、有限政府、英語。雖然日后來自其他地區的移民數量遠遠超過早期定居者后代,但他們均是以分子形式融入美國社會的,無法對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的統治地位構成根本性挑戰。⑤Samuel P.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 Schuster, 2005, pp.39-40.與之前數次移民潮不同,本次移民潮為美國社會帶來了經濟和文化上的雙重改變,包容、開放的多元主義正在逐步取代封閉、保守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成為美國主流意識形態。但是包括白人藍領在內的中低收入白人在精神層面較為保守,對知識精英倡導的文化多元主義持一種懷疑甚至批判的立場。在他們看來,多元主義帶來了眾多宗教上危險的“他者”,玷污了美國新教信仰的純粹性,移民對福利政策的依賴則威脅到倡導自力更生、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的美式生活方式。上述變化均讓白人藍領階層產生文化上的焦慮感。他們認為有必要采取措施阻斷非本土因素的負面牽扯和介入,以免淪為自己故鄉的陌生人。⑥刁大明:“‘特朗普現象’探析”,《現代國際關系》,2016年第4期,第33-34頁。
經濟上的沉淪、文化上的不適讓白人藍領階層充滿了憤怒與挫敗感,但是他們又無力改變現狀。自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以來,白人藍領階層一直是民主黨的堅定支持者。民主黨政府推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最低工資制度也基本符合白人藍領階層的需求。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傳統制造業日趨讓位于高科技產業、金融服務業,辦公室白領逐漸取代藍領階層成為美國勞工階層的主力軍。同后者相比,前者在經濟政策、意識形態方面更趨近于富有階層。這導致民主黨在經濟領域日漸趨近于共和黨,鼓吹對外貿易和全球化;在意識形態領域,選擇擁抱以性取向、性別、族裔為導向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失去了追求整體性社會改良的動力。在民主黨建制派眼中,白人藍領階層已經淪落為經濟、文化上的落后階層,成了被揶揄、批判的對象。⑦Francis Fukuyama, “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8, pp.99-108.政治上的邊緣化促使白人藍領階層逐漸右傾,開始從民粹主義政治人物的口號里尋求心理慰藉。2016年,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異軍突起,讓這部分群體看到了一絲曙光。特朗普口無遮攔,挑戰政治正確,批判自由貿易、移民政策和文化多元主義,在觸怒美國社會精英階層的同時,也為他在白人藍領中間贏得了另類的魅力。在本次大選中,有高達64%的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藍領選民將選票投給了特朗普,幫他在大眾選票少于希拉里的情況下贏得了多數選舉人票,①Alec Tyson and Shiva Maniam, “Behind Trump’s Victory:Divisions by Race, Gender, Education”,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9, 2016,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11/09 /behind-trumps-victory-divisions-by-race-gender-education /.成為決定大選走向的關鍵少數。
1.2 “美國優先”的思想內涵及其分析框架
不難想見,作為特朗普政府的執政理念——“美國優先”在思想內核上必然會盡可能迎合白人藍領階層的世界觀和利益訴求。與可以超越傳統的國家邊界、在世界范圍內逐利的全球化精英不同,白人藍領階層依舊需要依賴國家的庇護才能夠維持生存。②Giandomenico Majone, “The European Community between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Regul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1, No.2, 1993, pp.153-170.重振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因此成為“美國優先”的邏輯起點和終極目標。
在特朗普政府看來,美國的核心國家職能已經衰朽。曾經的經濟引擎制造業因為沉重的賦稅、過多的政府管制、不對等的貿易政策而不得不大規模外移,不僅導致寄身其上的產業工人經濟地位滑坡,還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③“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p.29-3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Peter Navarro, “Economic Security as National Security: A Discussion with Dr.Peter Navarro”,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November 13,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conomicsecurity-national-security-discussion-dr-peter-navarro.價值鏈理論認為,企業應該專注于自己最擅長的生產環節,而將其他環節外包給更具競爭優勢的企業。這為發達國家將生產基地外移到勞動力成本更廉價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理論基礎。④See Michael E.Por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Free Press,1985.發展中國家因此掌握了技術、積累了資本,同時在勞動力成本上依舊保有優勢,可以生產出質量更好、價格更低廉的產品,⑤See Joseph E.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Re?visited:Anti-Globalization in the Era of Trump,W.W.Norton& Com?pany, 2017.成為發達國家強有力的競爭者。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發達國家不得不借助財政與金融擴張維持經濟增長,過度依賴這些替代性工具會造成金融市場扭曲,一旦債務鏈條斷裂,就會爆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舊的國際經濟秩序也將隨之解體。⑥See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1994.
此外,全球化使得國家的邊界越發具有穿透性,每年都有大量移民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涌入美國,帶來大量的異質性文化,而文化多元主義的盛行又為新移民維系對母國的認同提供了便利。奧利·維夫(Ole Waever)認為,社會安全(Societal Security)取決于社會在變動的環境中或威脅面前維持其語言、文化、社會、宗教和民族認同以及習俗的能力。如果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管理制度無法同化移民,或者一部分移民群體拒絕被同化,就有可能影響接收國的社會穩定,進而影響政權的合法性和民族的自我認同。特別是在經濟停滯、政治極化、行政效率低下的情況下,社會安全最容易出現動搖。⑦Ole W?ver, Barry Buzan, Morten Kelstrup and Pierre Le?maitre, Identity, Migration and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in Europe,Pinter, 1993, pp.23, 162.
再次,“美國優先”認為,美國的沉淪與一個不甚友好的國際環境息息相關。戰后,美國一手締造了自由主義國際制度,以之作為與共產主義陣營對抗的工具。在經濟領域,美國建立了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世貿組織在內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此主導國際經濟制度與經濟秩序。在安全領域,美國組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中央條約組織等多邊軍事安全機制、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中國臺灣簽署了雙邊軍事條約,建立了美國支配下的安全同盟體系。⑧孔繁穎、李巍:“美國的自由貿易區戰略與區域制度霸權”,《當代亞太》,2015年第2期,第 84-85頁。但是,維持這樣一套復雜且龐大的制度體系離不開主導國強大的單邊支付能力。⑨單邊支付概念參見 H.Richard Friman,“Side-Payments Versus Security Cards: Domestic Bargaining Tactic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No.3,Summer 1993, p.390.為此,美國在經濟上長期奉行“不對稱合作”貿易政策,單方面向盟友、伙伴關系國開放美國市場,同時允許后者向美國關閉本國市場;在安全領域,美國主動分擔了盟友相當大的一部分防衛義務,而盟國則可以把這部分國防支出節省下來用于國民經濟建設。這套國際體系是美國遏制共產主義陣營擴張、取得冷戰勝利的重要工具,但也在經濟上為美國制造了以歐日為代表的新的競爭者。它們在貿易上對美奉行保護主義政策,從而獲得了不對等的競爭優勢,迫使許多美企不得不直接在上述國家投資以減輕競爭壓力,加快了美國工作流失的速度。①高柏、草蒼:“為什么全球化會發生逆轉——逆全球化現象的因果機制分析”,《文化縱橫》,2016年第6期,第30頁。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為了提升戰后國際制度的合法性,在制度設計時著意維護其他國家權利的平等性和廣泛性,對自身權利予以一定程度的自我抑制。在利益日益分化的當下,這也成為了其他成員國遏制美國利益伸張的工具。特別是崛起中的新興大國也試圖通過修改現有國際制度來分享、謀求這些制度帶來的私人利益,與制度設計者美國競爭規則制定權,②李巍、張玉環:“美國自貿區戰略的邏輯——一種現實制度主義的解釋”,《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8期,第151-152頁。令后者愈發難以利用現有國際制度實現自身目的。現實制度主義認為,國際制度必須在為其他成員提供公共服務和為主導國維護權力地位之間維持平衡,③李巍:“國際秩序轉型與現實制度主義理論的生成”,《外交評論》,2016年第1期,第32-33頁。否則主導國就會喪失繼續維系這一制度的動力。
在國際行為體層面,“美國優先”認為以中俄為代表的“修正主義大國”、朝鮮和伊朗為代表的“流氓國家”以及以圣戰者組織、跨境犯罪集團為代表的跨國威脅團體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主要挑戰。在三類行為體當中,中、俄利用自身的經濟、軍事優勢對美國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國際影響力構成了長期的根本性挑戰。朝鮮、伊朗則通過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支持恐怖組織、破壞地區穩定,對美國構成了現實的、緊迫的挑戰。而圣戰者組織、跨境犯罪組織雖然從事恐怖主義活動、毒品和人口走私,卻只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零星的、次級的威脅。④“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2-3,7, 13, 26,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這一排序標志著美國對外戰略中心的重大調整,即從反恐和介入個別地區事務回歸到傳統的大國競爭路線。⑤Teng Jianqun, “Trump’s‘America First’ Security Strategy:Impact on China-US Relations”,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2018, p.126;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3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綜上,“美國優先”是對冷戰結束以來歷屆美國政府秉承的自由主義內政外交路線的反動,帶有強烈的“美國本位主義”色彩,不僅奠定了特朗普的執政風格,也為研究今后美國的內外政策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見表1)。從國內層面看,特朗普政府力圖修復民族國家的物質生產職能,通過減稅、翻新基礎設施、去管制為企業松綁、減負,鼓勵制造業從海外回流,以便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與此同時,加強民族國家對邊界的管控能力,打擊非法移民和跨境犯罪活動,收緊移民政策、維護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的核心認同。從國際層面看,特朗普政府志在修正現有的國際經濟制度和同盟體系,革新在特朗普政府看來業已過時的部分,調整對美國不公平、不對等的部分,使之回歸“私人工具”屬性。就同盟體系而言,“美國優先”強調盟友必須提高國防開支、承擔起更多的安保義務;就國際經濟制度而言,美國希望在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性壁壘、服務貿易等方面有所斬獲。而對于來自國際行為體的挑戰,特朗普政府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要求甚至脅迫同盟、合作伙伴承擔更多的義務,與美國共同應對。

表1 “美國優先”的分析框架
二、“美國優先”與美韓同盟再調整:制度層面
韓國是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軸輻體系中的重要一環。1953年,美韓簽署共同防御條約,韓國以讓渡部分主權為代價換取了美國在安全上的保護,美國則保留了在朝鮮半島維持的軍事存在,維持著對朝鮮和周邊大國的震懾。與此同時,美國向韓國提供了大量援助、貸款和技術,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向韓國單方面開放國內市場,保護后者初生的民族工業。2012年3月,美韓兩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在經濟層面為同盟關系予以再保險,使之更好地服務于美國的半島政策和防擴散政策。①李巍、張玉環:“美國自貿區戰略的邏輯——一種現實制度主義的解釋”,《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8期,第144頁。可見,美韓同盟已經超越了安全范疇,逐漸向經濟、意識形態范疇延伸,成為美式制度、價值觀活力的象征。然而,美韓同盟內部又是不平衡和充滿張力的。從經濟關系看,美國曾經長期向韓國奉行單方面開放市場的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美國對韓貿易逆差。②See Charles Lee, “The Future of U.S.?R.O.K.Defense Cost Sharing”, The Diplomat, January 21, 2017.美國對韓貿易赤字已經由自由貿易協定締結前的132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231億美元。③Lee, Hyo-Young, “Future Outlook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Korea-U.S.FTA Amendment/Modification Negotiations” , IFANS?Focus, IF2017-39E,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17, p.3.從安全關系看,美國處于支配一方,韓國則處于追隨一方。后者至今不掌握本國軍隊的戰時指揮權,前者則在半島維持著總計2.85萬人的軍隊,年開支高達16億美元。隨著美國國力的相對走弱,韓國國力的相對上升,兩國都有改變這一制度安排的強烈動機。出身中左翼的文在寅政府渴望在國防自主、南北和談、半島無核化等問題上有所突破;特朗普政府則堅持要求韓國修正對美經貿往來中的“不對等”現象,提升其承擔的防衛義務比例,使之成為美國調整國際制度的杠桿,同時,調整對朝政策和同盟定位,幫助美國更加高效地應對來自中朝等國際行為體的挑戰。下文將美韓同盟關系分為不同問題領域,運用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從制度與行為體兩個層面逐一加以分析,以期對“美國優先”在美韓同盟關系上的影響做一個全景式呈現(見表2)。

表2 “美國優先”對美韓同盟的影響路徑
2.1 重新劃分駐韓美軍開支與戰時指揮權移交
自盧武鉉時代開始,韓國就逐年縮減國防開支,即便日后保守派重新入主青瓦臺,依舊延續了這一政策。④2016年12月23日,第7-8頁。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指責韓國消極對待國防建設,要求韓方擔負起駐韓美軍的全部費用,否則他將在勝選后從韓國撤軍。目前,美韓兩國根據《防務費分擔特別協定》(Special Measures Agreement)劃分彼此承擔的駐韓美軍開支。2014年1月達成的第九版協定規定,韓國政府需要為駐韓美軍支付雇傭的韓方工人工資、使用韓方設施產生的開銷、儲藏軍火產生的開銷,總計8.66億美元的費用,占駐韓美軍全部開銷的一半,每年還會根據通貨膨脹率自動追加4%。①Stephan Haggard, “ The Alliance Burden Sharing Agreement”,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anuary 24, 2014, https://piie.com/blogs/north-korea-witness-transforma?tion/alliance-burden-sharing-agreement.
朝韓、朝美分別舉行領導人峰會后,半島的緊張局勢得到了一定程度地緩解。外界普遍預期美方會在駐韓美軍開支問題上降低要價。但是,特朗普政府認為目前的緩和局勢尚不明確,堅持要求韓方承擔更多的駐韓美軍開支,并在2018年6月舉行的第十版《防務費分擔特別協定》磋商會議上希望韓國能夠為駐韓美軍提供作戰保障支持,即承擔包括隱形戰斗機、航空母艦在韓國的部署費用。在此以前,美國從未要求任何一個有美軍駐防的國家承擔此類費用。韓國外交部表示,美國的這一要求是不可接受的。到目前為止,第九版協定已經到期,美韓兩國依舊沒有在駐韓美軍開支分擔問題上達成一致。②Kim Ji-eun, “U.S.Pushes to Increase South Korea "s Share of Defense Costs”, Hankyoreh, July 25, 2018, https://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 /e_international/854833.html.
而戰時指揮權(Operational Control)是軍事指揮權的衍生物。理論上,韓國總統是本國軍隊的最高統帥,只是在戰爭時期將對軍隊的指揮權暫時讓渡給美韓聯軍最高指揮官——駐韓美軍總司令。但是自朝鮮戰爭結束以來,韓國軍隊的戰時指揮權一直由聯合國軍司令部及日后成立的美韓聯軍司令部中的美籍指揮官把持。③See Clint Work, “The Long History of South Korea’s OPCON Debate” , The Diplomat, November 1, 2017.2007年,在倡導“自主國防”的盧武鉉政府推動下,美韓兩國商定于2012年4月完成戰時指揮權移交工作。韓國保守派重掌政權后,先后以延坪島炮擊事件、天安艦事件和本國防空反導系統尚未投入使用為名,兩次推遲移交日期,最終將時間定在2023年。④Mark E.Manyin, Emma Chanlett Avery, Mary Beth D.Ni?kitin, Brock R.Williams and Jonathan R.Corrado, “ U.S.-South Ko?rea Relation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23, 2017, p.24, https://fas.org/sgp/crs/row/R41481.pdf.
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削減美國為盟友分擔的防衛義務,鼓勵甚至強迫后者肩負起更多的自主防衛責任;而作為民族主義者,文在寅政府則認為缺少對本國軍隊完整指揮權的韓國在主權上是不獨立的。兩者在戰時指揮權移交一事上找到了契合點,使得這一議題成為同盟關系調整中罕有的摩擦較少的領域。⑤Min Jeonghun, “Assessment of President Trump’s First Year in Office and Implications” ,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cember 15, 2017, p.1, http://www.ifans.go.kr/knda/if?ans/eng/pblct/PblctView.do.2018年10月31日,美韓兩國國防部長在第50屆安全協商會議上簽署“同盟指導原則”(Alliance Guiding Principles),確定了戰時指揮權移交后美韓聯軍司令部的指揮結構。根據新方案,未來聯軍司令將由韓籍四星上將擔任,副司令將由美籍將軍出任,這突破了美軍長期以來所堅持的不接受外國指揮官領導的原則。⑥Hwang Joon-bum and Yoo Kang-moon, “Defense Minister Says‘Foundation for OPCON Transfer Has Been Laid’”, Hankyoreh,November 1, 2018, http://www.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international/868406.html.此外,“同盟指導原則”還規定,駐韓美軍未來將會繼續駐守在朝鮮半島,打消了韓國保守派對于戰時指揮權移交后同盟將面臨解體命運的擔憂。⑦Clint Work, “The Long History of South Korea’s OPCON Debate”, the Diplomat, November 1,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1/the-long-history-of-south-koreas-opcon-debate/.
2.2 重修《美韓自由貿易協定》
《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的初衷之一是為兩國提供一個公平的貿易平臺,逐步消除存在于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現象。協議規定,80%由美國出口到韓國的工業產品以及三分之二的農業產品獲得免稅。韓國將為美國的知識產權提供更加嚴格的保護,并向美國開放價值5 800億美元的服務市場。⑧“The 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KORU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March 15, 2012,https://2016.export.gov/FTA/korea/index.asp.數據表明,該協定確實將美國商品在韓國的市場占有率從8.5%提升至10.65%,①Lee, Hyo-Young, “Future Outlook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Korea-U.S.FTA Amendment/Modification Negotiations” , IFANS?Focus, IF2017-39E,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17, p.3.卻未能從根本上扭轉美國對韓貿易逆差。2017年7月12日,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Emmet Lighthizer)正式向韓國政府致函,要求重新修訂《美韓自由貿易協定》。文在寅政府最初嘗試通過擴大從美國進口的商品總量、加大對美國的投資力度,避免對協定內容做出實質性修改。但是,這種暫時性的讓利并未換來美方的妥協,后者堅持要求對《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的內容重新進行修訂。2018年1月和3月,特朗普政府先后引用《貿易法案》第201條和《1962貿易擴張法案》,對韓國生產的鋼鋁產品,洗衣機及其零部件、太陽能電池及洗衣機征收關稅。此時適逢朝韓關系出現重大轉機,急于推進南北關系的文在寅政府迫切需要得到美方的支持,不得不接受后者的修約要求。
2018年3月26日,美韓兩國完成了《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的重修工作,修改內容主要集中在汽車和鋼鐵行業。新協定規定美國將在30年內(從2012年算起)逐步取消針對韓國皮卡征收的25%關稅。比原協定規定的日期延后了20年。韓國同意將美國汽車生產商的進口配額增加一倍,每家公司年均對韓出口由2.5萬輛增加至5萬輛。新協定還規定,凡是符合美國安全標準、排放標準的汽車可以直接進入韓國市場,不需要再進行額外檢測。為了得到美國的關稅豁免,韓國同意自我設限,今后將對美出口鋼鐵制品數量維持在2015年至2017年年均出口量的70%。同時,韓國接受美國對韓國生產的鋁制品征收10%的關稅。②“New U.S.Trade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Outcomes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U.S.Trade Representative, March 2018,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8 /march /new-us-trade-policy-and-national.2018年9月24日,美韓正式簽署了雙邊自貿協定的修訂版。這也是特朗普上任以來完成的第一項貿易協議。從內容上看,新版《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對原版內容改動并不大。韓國目前并未向美國出口皮卡,沒有任何一家美國汽車生產商能夠完成每年2.5萬輛的銷售配額,延長對韓國皮卡車的征稅期、提高美國汽車進口配額都不具有實際意義。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如此迫切地要求修改《美韓自由貿易協定》,除了回報集中在鋼鐵、汽車這兩個行業的核心支持者、減少韓國產品在美國的競爭優勢以外,更重要的是為接下來一系列雙邊、多邊貿易談判做好鋪墊。《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由于牽涉范圍較窄、生效時間較短,因此在技術層面上重修的難度較低。特朗普政府以該協定為突破口,可以給未來的談判對手制造更大的壓力,迫使后者做出更多的讓步。同時,修約也為約束文在寅政府提供了新的手段,避免后者在對朝政策上脫離美國的軌道。
三、“美國優先”與美韓同盟再調整:行為體層面
冷戰時期,美韓同盟的首要目標是抵御來自朝鮮的侵犯,其次是對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維持軍事震懾。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在東北亞地緣政治中的地位大幅下降,而中國則通過改革開放極大地改善了同美國的關系。作為東北亞地區唯一長期堅持反美立場的國家,朝鮮受制于其國力,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對美國構成實質性的威脅。在外部環境總體緩和的趨勢下,美韓同盟在冷戰結束后的近二十年時間里總體上維持著防御態勢,美國不僅撤出了部署在半島的全部核武器,還縮減了駐韓美軍規模。從2010年開始,上述趨勢出現了逆轉,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朝鮮則制造了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美國的63.11%③“World Bank Open Data”, World Bank, 2017,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朝鮮在洲際彈道導彈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具備了打擊美國本土的潛在實力。上述變化促使特朗普政府修正了東北亞地區國際行為體威脅的排位順序,將“修正主義大國”中國列為首要競爭者,而“流氓國家”朝鮮則緊隨其后。特朗普政府因此希望美韓同盟也能夠相應地作出調整,跳出東北亞地區的局限,在整個印太地區配合美國遏制中國影響力的上升,同時在對朝政策上展現出更強的進攻性,迫使朝鮮重新回歸無核化立場。
3.1 對華:“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
特朗普政府在先后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家防務戰略報告》及其官員的各種講話中對中國的定位,否認了冷戰結束后歷屆美國政府的對華共識。中美關系也因此發生了新的根本性變化。特朗普政府認為,之前美國政府奉行的對華接觸政策已然失敗,中國并沒有因為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而轉化為值得信賴的伙伴,反而通過工業補貼、配額制、操縱匯率、強迫技術轉讓等方式破壞了現行經濟秩序,①“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3, 17,25,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 "s Policy to?wards China”,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4, 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并希冀通過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試圖在印太地區建立一個以自身為中心的封閉體系。②U.S.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2,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現實制度主義認為,國際制度和規則的競爭是大國競爭的重要表現形式,它既是主導國之間的權力競爭,也是主導國提供公共產品能力的競爭。③李巍、張玉環:“美國自貿區戰略的邏輯——一種現實制度主義的解釋”,《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8期,第135頁。因此,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1月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以下簡稱“印太戰略”)④“Briefing on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U.S.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 2018, https://www.state.gov/r/pa/prs/ps/2018/04/280134.htm.帶有鮮明的制度競爭意味,其本質是針對中國的一套戰略,旨在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規則主導權和制定權。經濟方面,“印太戰略”支持由私營部門主導的發展模式,鼓勵私人資本投資印太地區的基礎設施項目,提升本地區的聯通性和能源供給。安全方面,“印太戰略”在現有的軸輻體系基礎上,力圖建立一個以日本為東翼、印度為西翼、澳大利亞為連接點,自己遙控指揮的“民主四邊形”(Democratic Quad)安全結構,并涵蓋韓國、越南、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盟友、伙伴關系國,通過維持該框架內權力結構的動態平衡,約束中國影響力的過快上升。
在“印太戰略”的大背景下,美國有意將美韓同盟的適用范圍由東北亞擴展至整個印太地區,并將現有針對朝鮮的美日韓三邊軍事合作升級為三邊軍事同盟。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一個地區的霸權國樂于借助另一地區的強國制衡該地區的崛起國,自己則充當離岸平衡手、置身事外觀察態勢的發展。⑤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Norton & Company,2001, pp.236-237.可見,“印太戰略”的推進高度依賴于盟友與伙伴關系國的介入。只有那些在地理上毗鄰崛起國,具備一定的國力基礎,且存在接受離岸平衡手指揮的主觀意愿的國家才擁有成為平衡者的資格。⑥顧煒:“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是復合式離岸平衡戰略”,《東北亞學刊》,2013年9月第5期,第57頁。韓國在地理上與中國隔海相望,同時又是印太地區少有的發達經濟體,具備一定的經濟、軍事、文化實力。但在主觀層面上,韓國缺乏在印太地區介入中美角力的意愿。作為一個中等強國,韓國長期陷于大國紛爭之中,一直希望能夠從東北亞地緣格局中突圍出去。從盧武鉉政府的“東北亞均衡者”構想到李明博政府的“新亞洲倡議”再到樸槿惠政府的“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其出發點都是平衡周邊大國的影響,避免成為任何一方的附庸。⑦凌勝利:“韓國的中等強國外交演變:從盧武鉉到樸槿惠”,《當代韓國》,2015年第1期,第42頁。而印太地區為韓國提供了一塊擺脫對中美在經濟和安全上的依賴、實現外交獨立自主的新場域。2017年11月,文在寅在東盟之行中提出了“新南方政策”,明確主張將韓國的外交、經濟邊界推進到東南亞和印度洋區域,力爭在2020年與東盟的貿易量達到2 000億美元,并在外交領域將東盟提升到與中美日俄同等重要的地位。①姜兌和、許振:“文在寅總統與東盟10國領導人舉行對話”,韓國《中央日報》,2017 年 11 月 11 日,http://chinese.joins.com/gb/article.aspx? art_id=173370&category=002002。
因此,文在寅政府不希望在印太地區繼續卷入新的大國紛爭。2017年11月,特朗普在訪韓時單方面提出了“印太戰略”概念,強調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共同價值觀基礎之上的美韓同盟是印太地區安全、繁榮與穩定的支軸。②“Joint Press Release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8,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press-release-united-states-america-republic-korea/.此舉令文在寅頗感意外,在隨后發表的《美韓領導人聯合聲明》中韓方沒有為“印太戰略”背書。文在寅的首席經濟顧問金顯哲()表示,“印太戰略”是日本發起的倡議,其目的是將日本、美國、印度、澳大利亞連接在一起,韓國沒有必要加入其中。③Hiroshi Minegishi, “ South Korea Balk at Joining USJapanese‘Indo-Pacific’ Push”, Nikkei Asian Review, November 11, 2017,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South-Korea-balks-atjoining-US-Japanese-Indo-Pacific-push.對于將美日韓軍事合作升級為三邊軍事同盟的建議,文在寅也沒有接受。他在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表示,美日韓現有的軍事合作足以應對來自朝鮮的軍事挑釁,將其升級為軍事同盟不僅不利于中韓關系,還為日本再軍事化提供了借口。④Lim Yun Suk, “Cooperation with US, Japan Important to Deal with Tension with Pyongyang: South Korea’s Moon”, Channel News Asia, December 3, 2017,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asiapacific/cooperation-with-the-us-japan-important-to-deal-with-tension-9373348.
3.2 對朝:極限施壓
“美國優先”力求為重振美國營造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決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對其本土安全構成挑戰,而一個擁核的朝鮮顯然與這一目的背道而馳。特別是在朝鮮初步具備打擊美國西海岸的實力后,朝鮮核武器的威懾范圍由東北亞延展至美國本土,使得原有的“戰略忍耐”政策難以為繼。在經歷了短暫觀望后,特朗普政府推出了極富進攻性的“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政策,試圖用壓倒性的權力優勢迫使朝鮮就范。
經濟領域,特朗普政府借助聯合國多邊制裁和美國發起的單邊制裁,盡可能地打擊朝鮮的出口創匯能力,瓦解朝鮮在海外的地下融資網絡。⑤Lee Hyo-Young, “Future Outlook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Korea-U.S.FTA Amendment/Modification Negotiations”, IFANS?Focus, IF2017-39E,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17, p.1.外交領域,特朗普政府游說各國政府切斷或降低與朝鮮的外交聯系。軍事上,美國先后向朝鮮半島派遣了“里根”號航母戰斗群、B-1B超音速轟炸機、薩德反導系統,承諾進一步擴大對韓軍事出口,同時強化了美日韓三國軍隊針對朝鮮的情報偵察、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合作。⑥Scott A.Snyder, “ America First or U.S.?South Korea Alliance First in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7, 2017, https://www.cfr.org/blog/america-first-or-us-south-korea-alliance-first-dealing-north-korea; Yeo Jun-suk,“Nuclear North Korea Never Be Tolerated: Allies Defense Chiefs”,Korea Herald, October 28, 2017, http://www.koreaherald.com/view.php? ud=20171028000049.與消極等待的前任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認真考慮過對朝鮮發動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行動,美韓兩國的軍事演習完全按照實戰標準進行,并用主張對朝強硬的前太平洋艦隊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取代反對動武的小布什政府朝鮮問題高級顧問車維德(Victor Cha)擔任駐韓大使一職。⑦David Brunnstrom and John Walcott, “Trump Administration Plans to Nominate Harry Harris as South Korea Envoy”, Reuters,April 25,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southkorea-harris/trump-administration-plans-to-nominate-harry-harris-assouth-korea-envoy-sources-idUSKBN1HV2OI.在“極限施壓”的同時,特朗普政府依舊為美朝和談預留了后門。特朗普政府表示,如果朝鮮認真落實了全面、可核查、不可逆的無核化方案,美國可以容忍其政權的存在,并將其迎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之中。在文在寅政府的牽線下,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河內舉行會晤,雙方同意在半島建立可持續的和平機制。但是,特朗普政府始終拒絕與朝鮮簽署停戰宣言,并繼續維持對朝制裁,使得建立半島和平機制流于空談。
作為中左翼勢力的代表,文在寅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實現半島統一、民族獨立,其次才是如何在盡可能少的外來干涉下實現半島無核化,因此文在寅政府的朝鮮政策以和解為主,更加務實,也更具靈活性。文在寅上臺后,明確表示會保證朝鮮體制的安全,不追求吸收式的統一,并且開辟多種渠道改善南北關系。在文在寅的授意下,韓國政府恢復了部分南北民間交流機制,制定了統一的朝鮮半島經濟開發政策,并且成功舉行了南北領導人峰會。對于朝鮮的無核化進程,文在寅政府的態度較為模糊。在總共有3款13條的《板門店宣言》中,雙方花費大量篇幅去描繪南北統一、共同繁榮的愿景,直到最后1條才提到無核化問題,并且沒有為無核化進程設置具體的時間表。①“朝韓聯合發布《板門店共同宣言》全文”,觀察者網,2018 年 4 月 27 日,https://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8_04_27_455143.shtml。
在“美國優先”的背景下,文在寅政府在對朝政策上的自主傾向勢必會與特朗普政府對本土絕對安全的追求產生矛盾。在美方看來,南北接觸必須在自己設定的范圍內進行,決不允許韓國有任何越軌之舉。文在寅平壤之行結束后,美國駐韓大使館違反外交慣例,越過青瓦臺和韓國外交部直接與三星、現代、鮮京、樂金四家企業溝通,確認文在寅訪朝期間與平壤達成的合作項目內容。這被韓方視作一種警告,即美國不愿看到南北關系進展過快而脫離自己的掌控。出于對美國壓力特別是貿易報復的忌憚,文在寅政府在軍事上通過參加聯合軍演、擴大對美軍購規模維持對平壤的武力震懾,以配合“極限施壓”政策的需要,②“Address by President Moon Jae-in on the 69th Armed Forces Day”, Ceong Wa Dae, September 28, 2017, https://english1.president.go.kr/BriefingSpeeches/Speeches/25.并借機要求美方放寬對其導彈最大荷載、最遠射程的限制,督促海軍提高諸如殺戮鏈先發制人打擊系統、韓國防空反導防御系統等國產武器的打擊能力,③Lee Chi-dong, “Moon Seeks to Adjust U.S.Alliance, Rein?force Independent Defense Capability”, Yonhap News, May 10,2017, http://english.yonhapnews.co.kr/news/2017/05/08/02000000 00AEN20170508006100315.html.在經濟上通過能源禁運、切斷融資渠道打擊朝鮮的國民經濟。
結 語
“美國優先”迎合的是部分在全球化過程中利益受損群體的訴求,其各項政策的出發點是振興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修復因全球化而受損的各項國家職能,鼓勵制造業回流,強化邊境控制。與此同時,“美國優先”力圖廓清美國復興面臨的各項外部障礙。制度層面,修正現行國際經濟制度和同盟體系,使之與美國的利益之間更加契合;國際行為體層面,利用重新調整后的同盟體系、國際制度去約束“修正主義大國”和“流氓國家”的行為。換言之,“美國優先”是對冷戰結束后流行于世界的自由主義范式的反動,承認自由主義價值觀、制度、政策的局限性,主張回歸民族國家、回歸權力政治,用現實主義修正美國的內外政策。
同其他雙邊、多邊關系相比,美韓同盟體量較小、博弈對手相對明確,其所處的東北亞又與美國存在著緊密的安全、經貿、文化往來,構成了實現美國再次偉大的重要外部環境。因此,無論是從成本還是從難易的角度考慮,美韓同盟都是特朗普政府理想的優先調整對象。從國際制度層面看,特朗普政府修改《美韓自由貿易協定》、減少為韓國分擔的防衛義務比例都是為了給自身減負,并以此為杠桿撬動關系更為復雜、規模更為龐大、談判對手更為多元化的多邊、雙邊結構,避免它們成為其他國家制約和損害美國利益的工具。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特朗普政府頻繁向韓方施壓,不僅拉低了美國的國家形象,也動搖了同盟的道義基礎,加劇了其內部的不平衡性,進一步強化了韓國的追隨者地位。
從國際行為體的層面看,針對“修正主義大國”中國和“流氓國家”朝鮮,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宏觀層面的“印太戰略”和微觀層面的“極限施壓”,并要求韓國做出相應的調整。這反映了美國當局對兩類不同性質威脅的認知,前者對美國構成了根本性、全局性的挑戰,需要廣泛動員盟友與合作伙伴,借助制度性手段加以制約;后者對美國構成的是個體性、局部性的威脅,只需要拉攏個別盟友利用強力就足以應對。對于“極限施壓”,韓國在很大程度上予以配合,即便在緩和南北關系上有所突破,也沒有突破美國當局設定的框架。對于“印太戰略”,韓國表現出了一定的自主性,有意同美國拉開距離。這既體現出美韓兩國對于同盟外部威脅認知上存在分歧,也暴露出“美國優先”在調整國際關系時存在的短板,即強調使用強制性、物質性的權力,卻忽視使用說服性、制度性的權力。
本質上講,“美國優先”是一套鼓吹推卸責任的執政理念,幻想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與自由主義范式不同的是,它以工具主義理性去看待國際體系,主動放棄了自由主義賦予美國的諸多調節國際體系的工具,削弱了美國發起國際動議的道德感召力和合法性。雖然“以勢壓人”是其外在表征,“美國優先”單純依靠權力政治作為實現政策目標的手法還是暴露出特朗普政府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意愿和管理國際制度經驗的雙重不足,以其作為原則修正國際體系勢必會加劇體系內部的不平衡性和脆弱性,加速國際社會從“規則世界”向“自然狀態”的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