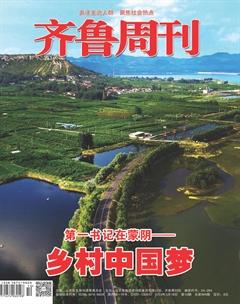東紫:“通往生命最隱秘處”
董忱 陸洋


東紫,本名戚慧貞,山東莒縣浮來山人。2004年始在《人民文學》等報刊發表作品。創作長篇《好日子就要來了》及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歌若干。出版中篇小說集《天涯近》《被復習的愛情》《白貓》。曾榮獲人民文學獎、中國作家獎、泰山文藝獎、《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獎等獎項。
東紫的本職是藥劑師,正因為從醫的職業經歷,使她能夠窺見生命深處的隱秘。在她的文學世界里,“小人物”往往輻射“大事件”。她記錄觸動她的生命個體,并與他們產生了千絲萬縷的關系,從而抵抗宿命的殘忍與不公。
執著于“發聲”的潛在根源
很多年以后,在和文友閑聊童年時,如春憶起啞巴東,總會不由得坐直了身子,回望著遙遠的生命歷程,在心底里驚問——難道是它墊起了自己自信和悲憫的第一塊基石?這是她執著于寫作,執著于“發聲”的潛在根源嗎?——《迎風帳》
東紫出生在魯東南的一個山村里,貧窮是她童年的記憶。
“冰冷的煮地瓜”“鍋底的肥肉渣”“被一切三瓣的蘋果”都曾是她成長過程中奢侈的味覺記憶。極度封閉的環境和匱乏的物質卻滋養了東紫細膩的情感,而被她所觀察、記錄的一切也成為她日后創作的養料。《迎風帳》中,如春就是東紫的影子。她用細膩而克制的筆觸完成了對童年的回望以及對自我的注解。
上世紀八十年代,讀初中的東紫第一次受到了詩歌的啟蒙。彼時,詩社在中國頗為流行,東紫的語文老師王世聯是農民詩社《山地》的主編,同桌就是社長張榮山。在他們的引領下,東紫榮幸地成為詩社的幫工——幫著刻板、油印、裝訂,目睹了詩歌帶給他們的快樂、分享、友誼、愛情……那一切,對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來說,既新奇又魔力無窮。
直到現在,東紫還常常想起那些日子。“我刻著那些似懂非懂的文字,聞著文字散發出的神秘氣息,就這樣愛上了文學。”偶爾,東紫也學著老師的樣子寫點什么。但那時她還不很清楚文學對于她的意義。
直到十幾年前,家中接連遭遇變故,東紫墜入人生谷底。在絕望中,東紫收到了《人民文學》,那一期的雜志上,有她的一部中篇小說,“一瞬間,我就覺得自己的脊柱仿佛被打上了鋼筋,我覺得我的人生不是垃圾筐式的人生,你遭遇的一切挫折和屈辱,都是你獨特的生命體驗,只要你真誠地對待文學,文學最終都會回報你,文學可以支撐生命,可以兜住你人生的底,文學不會讓你的生命脆弱地倒下。所以如今有人問為什么寫作,我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他:為你的生命寫作。”
寫作也是“孤獨地抗爭”
白貓一動不動。我突然想起五年前母親臨終的時刻。那也是個深夜,我孤獨地守在她的病床前,眼睜睜地看著她一點一點地衰亡。遠離。我被無能為力的悲哀控制了,看著自己的雙手痛哭不已。年富力強的它們竟然成為了一種擺設,絲毫沒有用處。幼年的時候,弱小的它們都能牢牢地拽住媽媽的衣角呀。我撫摸著白貓,生怕在抬手的霎那間丟失了它的呼吸。這一刻,我重新記起了守在親人病床前的強烈感覺——渴望著那呼吸是有形的,是能夠用手牽拽住的。渴望人和死神之間是有繩索的,是能夠由親人組成隊伍力拔的。但是,生命在危機的時刻總是孤獨的。孤獨地抗爭。——《白貓》
東紫的寫作過程往往從容而漫長。她喜歡把好的素材和故事焐在心里,焐人物的性格,焐寫作的語言,等到一切都成熟了,提起筆來,早已被“焐熱”的故事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來了。《北京來人了》《白貓》《春茶》《樂樂》等多部獲獎作品都是這樣被焐出來的。
但這樣的過程也是個“煎熬”的過程,每個漫長的創造,都是一場“孤獨地抗爭”。人物、情節不斷在東紫的腦海中浮現、發酵,故事一天沒寫完,他們就一天在東紫的心里裝著。
除了作家,東紫還要兼顧其他同等重要的角色,她是妻子、女兒、母親,還是一名藥劑師。白天,她穿梭于醫院中,與藥品、病人打交道;回到家中,她是賢惠的妻子和母親,沉浸在日常的生活瑣碎中。工作日以外,她把兒子的課外班全都安排在周六,周日這天,才是她奢侈的、自由的寫作時間。
與其他作家比起來,東紫的寫作時間少得可憐,她也常常用“自我寬解自我原諒的借口”來寬慰自己。但事實上,多種角色的切換反而為作家東紫提供了更多觀察生活的視角。當她午休時走過醫院大院時,坐在輪椅上被推出來“放風”的病人使她心生悲憫;陪伴兒子成長的片段是她的創作繆斯;與愛人、朋友間的交流讓她得以接觸更多值得被記錄的個體生命。
作為藥劑師,東紫精通藥理。作為一個作家,文學就是東紫的一劑精神良藥。她眼見生老病死、人生百態,以文字詮釋生命,以一顆作家的“仁心”敘述一個醫者、母親的內心世界。
消散自身的顏色博取一聲喝彩
她看著那個無法伸展成葉片的芽苞,那樹林一樣擁擠著拼命消散自身的顏色博取別人一聲喝彩的短暫,想到那其實就是一個個生活里的女人,在人生的舞臺上沒有兩只水袖的女人。或許水袖是有兩只的,但舞動的只能是一只。另一只必須是緊握著的,是永遠不能順應生命和情感的需要拋撒舞動的。——《春茶》
東紫人很溫和,外表單薄、柔軟,但她的小說“筆力銳利,常刺入人性中薄弱的間隙”。
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胡平稱她的作品銳利之外,筆調又是間離和幽默的,不斷以喜劇的色澤沖淡悲劇的壓抑,從中獲得一種奇特的修辭效果。東紫對人性的觀察是全面的、健康的,而不是褊狹和極端的,這種觀察也造成了她的創作的敦厚氣質。
在東紫長篇新作《好日子就要來了》中,以做假文憑為核心的小說情節,將日常生活的復雜性、諷刺性做了文學的表達。文學評論家李掖平評價說:“東紫的小說擅長在人性的善惡復雜糾結下,在生活的尷尬無奈中,在感情的微妙邊緣處,描寫個體生命悲歡離合的遭遇,拿捏其靈魂深處的傷痛,文字時而犀利冷峭時而纏綿悱惻,搖曳出一種迷人的風情。”
天才女作家奧康納認為寫作應該“沾染一身塵霾”,奧康納長期在很簡陋的環境中寫作:她的房間里窗上沒有窗簾,屋頂正中垂下一根長長的電線,系著光禿禿的燈泡。她總是獨自一人,拉下百葉窗,坐在打字機前,面前一疊黃色的紙,或是寫作或是修改。對此,東紫深以為然,寫作應該將自己置于一個現實生活中,不沾染世俗,又怎么看見個體命運在社會中的脆弱呢?
寫作就是要寫“和你生命相契合的東西”,寫“讓你疼痛的東西”。“文學是最公正的,只要我們真誠地去對待它,它就會真誠回報我們。這種回報,不僅僅是作品得到了發表、贊揚,它最大的回報是成為我們生命的支撐——因為它,我們生命中所遭遇所承受的一切不公、不幸、屈辱、挫折等等,都能成為可利用的材料,成為寫作時深入描寫人物生命體驗的一種直接經驗。由此,寫作成為我們日常的保健理療師,把那些容易導致人氣滯血瘀的東西,進行了排解轉化。”東紫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