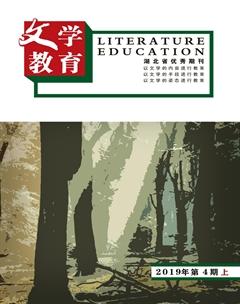擱淺
大頭馬
“我的狗死了。”
第一個電話打來的時候他剛準備瞇一會兒。如果不是同事有急事說要回家一趟,他這會兒本應該已經結束夜班,到家睡覺。“睡一覺一切都會迎刃而解。”這是他常對電話那頭說的,半夜打電話來的人本來就會因為身體的疲憊而導致激素水平降低,情緒陷入低谷,所以這么說也沒錯。“先睡覺,醒來再說。”他講。而這時已經是早上八點,他就沒法再這么說。
“嗯?是怎么死的?”于是他問。
“我不知道。大概是吞了什么東西。”
電話那頭的聲音聽上去不年輕了,他判斷是一個老頭,約莫五六十的年紀。
“是公狗還是母狗?”
“公狗。”
“現在呢,你在干嗎?”
“我不知道。我坐在家里客廳,它躺在我面前。”
他想了想,應該怎么說,“需要我幫忙叫動物檢疫站的人來么?”不,這不是他應該做的事情。“你感到傷心嗎?”從電話那頭的平靜語調來看,對方并未處在較高等級的自殺預警狀態,似乎也不應該這么問。他在心里給這個電話規定了一個時限——他們得把更多的時間放在那些更緊急的電話上。不過早上的電話總是最少的,一般人很少在早上想到死。他看了眼時間,決定繼續陪對方聊聊。
“嗯。”他說,然后等待。
過了好一會兒,對方才開口道,“我不知道今天早上要吃點兒什么。”
“怎么?”
“以往我都是牽著它出門,現在我好像找不到出門的理由了。”
“您是做什么的?”
他試圖分散一下來電者的注意力。
“我……我退休了。退休前我是一個工人。”
“您沒有子女嗎?”
“有,不過……唉。我再想一想。謝謝你了。”
對方掛了電話。
這是常有的事。大部分給他們打電話的人不會直接坦露想死的念頭,他們只是需要在陷入某種困境時跟人說說話。
他愣了半晌,然后擱下電話。
幾乎是立刻,第二通電話就響起來了。
他接了電話,那頭沉默著,于是他說,“喂?”
“你好。”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幫助你的么?”
“我很難過。”
“怎么回事?和我說說。”
“我丈夫……他……”那頭沒說兩句就開始啜泣。
哦,多半又是一位遭到家庭暴力的女性。這類的電話總是很多。
“他怎么了?”
“他離開我了。”
“因為什么?”
“是他們強制讓他離開的。”
“他們是誰?”
那頭沒有回答,又是一陣小聲的哽咽。
他想自己問得太著急了。往常他不會這么著急,第一步是和來電者建立聯系。建立聯系。建立聯系。建立聯系。他在心中小聲默念三遍。
“半年前我曾經給你們打過電話。”那頭忽然開口。
“是么?”
他在腦海中尋找這個聲音,他確實覺得這個聲音有些熟悉,只是每天的電話太多,他們通常只會對來電者進行兩次回訪,確定對方的后續狀況。三天后第一次,一周后第二次。大部分人在一周后都會放棄自殺念頭。當然了,他并不確認——他從來沒覺得自己救活過哪個人,他只是確保在一段時間內他們沒有死。
“那時我丈夫打我打得厲害。
“我記得你。”他其實沒有想起這個聲音的主人。
“我實在是活不下去了,所以給你們打了電話。”
“但是我記得你走出去了。”
“謝謝你當時的幫助。”
“不,這一切是你自己的力量,你靠自己活下去……你很棒呀!”他努力讓自己的聲音顯得積極。但他這會兒實在是有點兒累。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大部分處于婚姻暴力中的女性遲遲無法走出困境是因為她們缺乏獨立生活的能力。有相當一部分無法經濟獨立。
“哦?太好了,你找到了什么工作?”
“借錢做了點小生意。我開了一個炸雞店。”
“是嗎?生意怎么樣?”
“剛剛起步,店的位置不錯,還算有人氣。”
“那不是挺好的。”
“嗯。”
那邊又沉默了。于是他繼續問,“所以你后來和你的丈夫怎么樣了?”
“我出院后在我娘家住了一段時間。”
“他呢?”
“沒人照顧他,我又回去照顧了他幾次。”
“他需要人照顧?”
“他坐輪椅,沒法生活自理,我一周去看他兩次,幫他準備些飯菜,打掃屋子。后來開始做那個店,我就請了個人去。不過每次都被他打走了。”
他漸漸弄清了。電話那頭是個約莫三十多歲的女性,丈夫因為身患殘疾常年坐輪椅,極度的不安全感導致了強烈的占有欲。這是暴
暴力行為的來源。他自己不工作,也禁止妻子工作。和一般的家暴情況不同,她遭受的虐待得不到親友的援助,是因為人們的同情心總是先天放在了看似弱勢的那一方。甚至包括她自己。殘疾成了合理化丈夫一切虐待行為的借口。
“是我沒做好。我總想著重新來過……”
他沉默了。
他起初分配到晚班的時候以為晚上的事情少,可以容許他繼續想想數學題,或者是發發呆,看看書什么的。后來才發現晚上才是干預中心最忙的時候。周五尤甚。“黑色星期五啊。”同事感嘆,他聽了會解釋道,根據全國的電話頻率數據顯示,不管是什么電話,周五總是最多的。“這是一個樣本錯覺。”他講。“高老師,您不愧是數學專家。”他聽了也就是笑笑,剛來的時候同事們都會半客套半真誠地捧他兩句,時間久了,也就忘了他原來的工作是在大學教數學,把他當做他們中的普通一位自殺干預熱線接線員了。
實際上,他和其他接線員還是不太一樣。遇到再崩潰再危急的事件,只要把電話轉到他這兒,他總會保持一如既往的理性口吻,安撫住對方的情緒,確定問題,保證安全,給予支持。
產生自殺念頭的人都是因為生活中遇到了無法跨越的障礙。但是無法跨越的障礙往往只是眼前表面的那個問題,當跨過這道障礙之后,他們需要面對的可能是更長遠、更根本的問題。比如現在這一位。
脫離家暴環境之后的女性往往需要面對重新獨立生活的問題,而她呢,她需要解決的是自己對依賴者所產生的……
“我還是愛他的。沒有他我活不下去。”她說。
“不,你不是愛他,你只是因為內疚。”他平靜地說,“他離開你可以活下去,你離開他也可以活下去,不要沉浸在想象中。你現在在哪兒?”
“我在家。”
“時間不早了,今天炸雞店不營業嗎?”
“營業的。”
“那你快去店里,今天是他們送走他的第一天,我們先從今天開始看看好嗎?”
他等待著。
過了許久,電話那頭終于傳來一句,“好。”
“三天后你再給我打個電話,到那時我們再看看你會不會這么想,我們打個賭。我打賭你不會。”
“……好。”
掛上電話他看著桌前貼著的一張風景照發呆。那是他來這兒工作前上一位接線員留下來的,其實應當說是一張明信片,上面用英文寫著“Iceland”,畫面里是青翠欲滴的青山和氤氳的彩虹。“冰島?那不該是個冰天雪地的地方么?”有回同事趴在他桌前問他,“這應該是冰島的夏天。冰島是個地理多樣性非常豐富的地方,既有青山,也有冰湖,還有火山和平原。”“高老師,你懂得真多。你去過?”“沒有。”
沒有。他去過印度,看過恒河上漂浮的尸體,跟隨當地的禪師修習過六個月的禪修班。去過西班牙,在高迪的圣家堂里從日出坐到日落,觀察光線穿透彩色玻璃在空氣里形成的變化。去過南美,在智利的百內公園徒步五日,到達那座最為著名的百內三塔時,殘留的晚霞的余暉正撫摸著他的耳垂。他還去過美國——他就是從那兒出發的,在離開那所南部的大學,去了他原本計劃要去的各個地方之后,他又回到了那個校園,他站在平時散步的那棵樹下,思考了很久很久很久,那棵樹的葉子由綠轉黃,又由黃慢慢飄落和泥土結合為一體,在雪花壓彎枝丫之前,他回來了。回到了他曾經最熟悉的城市。
不過,他還沒去過冰島。
第三個電話響了五次時他才接起來。真的是有點累,今天他還想保留些力氣做些事。
“我要殺人。”
對方口吻來勢洶洶,又處于按捺某種激動情緒之上的冷靜中。他心里“咯噔”一下,困意一掃而空。
“你要殺誰?”
“我要殺三個人。第一,我們機械廠的廠長。第二個,我們縣政府的副縣長。第三個,是我老婆。”
“你為什么要殺他們。”
“這事兒不好說。”
“怎么不好說?”
“我不能讓你知道。”
“你可以說給我聽聽。”他說,“我們這里對來電者的信息是絕對保密的,你不用害怕。”他撒謊了,保密是有條件限制的。
“不,我不能告訴你。”
“你不用告訴我具體的。”他換了種舒緩的語氣,“你看,你打電話來,肯定是想說點兒什么對嗎。”
“我就是想告訴你……我就是想說,我要去殺人。”
還有得聊,他喝了一口水。
“我知道,你受到了很深的傷害,你很受傷,不過你殺了他們,你也會死。”
“我沒打算活。”
“你可以活的。你還有別的選擇。”
“沒有了!他們必須死!”
“你不殺他們,他們也會死,每個人都會死。”
“他們必須今天死!”
“可是你不用今天死。”
“他們不死,我也活不下去了。”
“所以你是想活下去的對嗎?”
那頭沉默了。
“我不能再跟你說了,我要去了!”對方著急要掛電話。
他看了看墻上的鐘,快到中午了。
“你吃飯了嗎?”他趕緊問。
“沒有。”
“那你先給孩子做頓飯吧。以后恐怕就沒機會了。”他試探。
“孩子在她爺爺家。他們會給她做的。”
試探成功了。這是一個有孩子的男人。勸阻他打消念頭的成功率提高了許多。
“那你不去看看她?”
“我都安排好了。”
“你安排什么了?讓她爺爺奶奶撫養她?”
“我留了一筆錢給她。”
“夠她用到什么時候?”
“我不知道,我只有這么多了。我能做的就是這些了。”
“你還能做很多。你可以撫養她,到她考上大學,能夠獨立生活。”
“我……我做不了,我做不了了……”那頭的聲音顫抖起來。
“為什么?天下沒有過不去的坎兒。能幫助你的人比你想象的多。你也比你想象的有能量。”
“有辦法我都試過了,不行了。”
“我不相信,你跟我說說?”
他花了好一會兒才從對方斷斷續續的描述中搞懂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這男人本是機械廠的高級技師,老婆和副縣長勾搭到了一起,被他發現了,去縣政府鬧過沒轍,反而廠長懾服于政府關系把他開除了,丟了飯碗,家中只有一個老父親,前些年剛因為一場病把家里積蓄消耗光了,現在他已經是走投無路,老婆要離婚,他在當地也沒有任何繼續生存下去的能力。人生走到了盡頭。
總是這樣,打電話來的人誰不是人生走到了盡頭呢。
“我不能再跟你多說了。刀子我都備好了。”他語氣又強硬起來,好像這通電話反而幫他梳理清楚了脈絡,恨意又起,心意已決。
“你就光一把刀能殺得了他們三個?”
對方猶豫了一下,“我先去廠里宰了那頭豬。”
“那等你再去殺另外兩個,他們早獲得風聲跑了。”其實他心里想說,估計你都出不了工廠大門。
“沒事,我知道他們下午在哪兒私會。我在那里已經備好了炸藥。”
他心里一驚,伸手把桌上的手機拿近了一些。他們會給來電者分這么幾個等級,有自殺想法,有自殺計劃,已有自殺做法。大多數來電者只是有自殺想法,這個等級的來電者多半是一時沖動,經過一段時間規勸會慢慢放棄自殺念頭。而眼下這位,已經處在最高預警等級。干預中心除了主臺一般還有輔臺,一旦主臺發現來電者處在危險狀態,會通知所有人,這時輔臺就會幫助收集信息,必要時報警施救。
但現在,這里只有他一個人。他不禁焦躁起來。干預中心夜班三個人,白班兩個人。剛請假回家的小李,是他一直就覺得不靠譜的一位同事。年輕人,總想著玩。而另一位白班同事是個五六十歲的老大媽,退休閑著沒事才跑到這里來做一份不賺錢的工作。她雖然對這工作挺熱心,但沒什么時間意識,有時到了中午才晃晃悠悠地過來。今天呢,到現在也沒見人影。
“高老師,咱們這里,就屬您最專業。”平常他們老這么跟他說,他有回實在忍耐不住,冷冰冰地回了句,“我只是按時上班,按需要做事,也沒什么。”他們也假裝沒聽出他的潛臺詞。畢竟這工作確實沒多少工資,來做就已經是出于公益目的,他也沒有更好的理由指責別人什么。
“那也不一定成功。你想殺他們,他們早該覺察了。”他盡量拖延時間,同時在手機上按了1,1……
“不會的,他們不知道。這事兒我到現在就和你說了。”
“他們對你做了這些,心里總該有點兒什么,肯定一直在提防你。兔子急了還要跳墻呢。”
“他們心里有什么也不會把我逼到這個地步!”
時間已經過了十二點。他按下了最后那個0,然后說,“你餓嗎?”
“餓?”那邊愣了一下。
“你不餓我都餓了。這樣吧,你先吃頓飯。”
“吃飯?哈哈,吃飯……”
“既然你決定了,你看,人總是要吃飯的。你去吃最后一頓飯吧。好好吃一頓,吃飽了也有力氣干你要干的事兒。”
那邊遲疑了。他的手放在撥出鍵上。
“最后一頓。”他說。
“嗯,你說得有道理。”
“你附近有飯館嗎?”
“有。”
“那就找個最好的。”
“好。”
“不過……”
“什么?”
“你吃飯的時候也不要掛電話好嗎?”
他沉默了。他等待。
“好。”他說。
他的手最終沒按下撥出鍵。
他把電話聽筒放下,然后轉成免提模式。
他確實也餓了,他本該吃一頓早飯。今天這頓早飯他本想好好吃一頓,他前一晚已經提前做好了,放在冰箱里。要不是今天多出來的這攤子事兒,他已經坐在桌前,把那些盤盤碟碟拿出來,整整齊齊地擺好在桌子上。草頭,熏魚,素雞,桂花藕。這是他老師愛吃的,老師是上海人,他剛去美國的時候,老師就是用一桌本幫菜招待的他。他初時很驚奇,他是北方人,完全沒想到漂洋過海去到另一個國家,這才第一回吃到了正宗的本幫菜。
他聽著電話那頭傳來的各種聲音,判斷對方走出了家門,然后走到了大街上,然后走進了一家餐廳。他聽出那應該并不是多么好的餐廳,因為沒有聽到服務員迎賓的聲音,他根據男人和服務員對話的聲音判斷那應該只是一家小館子,甚至沒有服務員,因為對方喊“老板”。
“喲,好久不見,今天吃點啥?”
哦,他是去了一家相熟的館子。他心里又稍微落定了一些,既然對方選擇去認識的地方,說明他還不想死。他祈禱重新走入往常的生活能幫助對方放下毀滅一切的執念。
他終于能夠放松些,向后靠在椅子上。他太累了。他需要躺一會兒。
電話那頭傳來了點菜的聲音——沒一會兒菜就上來了,他沒點幾個菜,他確實沒什么錢了,除去留給孩子的,和準備殺人計劃花去的,他估計沒給自己留下多少錢。
他盯著那張冰島的明信片,在電話里悉悉索索的白噪音下,感覺自己就快要睡著了。
他仿佛又看到了老師。在見到老師之前,他已經聽說過他的名字十年之久了。那會兒他還是個孩子,有一天他從一塊兒打游戲的同學那里撿到了一本書,他很快被吸引住了。“這本書能借我看看嗎?”“你拿去吧,我爸非逼我看的。”這之后他幾乎再也沒有去過游戲機廳。他就是從那本書上頭一次看見了老師的名字。他見到老師的第一句話是,“原來您這么年輕!”對方笑了笑。他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只顧投入在公式的世界里,從來也沒想過去檢索一下老師的名字。老師少年成名,實際也不過就大了他十歲。
“喂?”電話里傳出的聲音把他從半夢半醒的狀態里驚醒。
“啊,怎么?”
“我吃完了。”
這話結束之后他倆都有些不知該說什么。他感覺這頓飯結束對方的情緒已經平復了許多。于是他試著說道,“你在進機械廠之前是做什么的?”
“嗯?”對方沒想到他問這個,便答,“做木工活兒。”
“做木工怎么轉去做機械了。”
“原理都差不多,干機械賺得多點。”
“既然如此,你也可以接著干點兒別的。”
“干點啥?”
他想了想——他也不知道為什么要這么說,他說,“你懂數學嗎?”
“只懂些簡單的。加減乘除,這算數學嗎?”
“算啊,怎么不算。”
“我還懂點幾何。”他仿佛看到電話那頭靦腆地笑了一下,“幫孩子輔導功課自學的。”
“那就好辦了。”他沒說:其實你做木匠活兒,那就是幾何。
“怎么好辦?”
“只要你懂數學,你一定可以干點兒別的事。”
“比如呢?”
“你可以……你可以賣菜啊!”
電話那頭愣了,然后笑了。這回是真的。他都聽到那頭傳來的笑聲。他自己也笑了。兩人就這么笑了很久。
“你真是會開玩笑。”
“不,我是認真的。”他講,“你甚至能找到比干機械更賺錢的活兒,我相信你,你可以的。”
“可我在這個地方已經呆不下去了。”那頭似乎又痛苦起來,“你不知道……其實,其實,他們所有人都知道我老婆……我老婆的這個事。只有我不知道。”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個事情。”
“什么?”
“其實他們所有人都知道你要去殺人,只有你不知道。”
那頭又沉默了。
“其實他們都等著看你怎么崩潰,就等著你走到這一步呢。”
“嗯。”
“我覺得你這時候更應該好好活著。你覺得呢?”
“嗯……”
他看了看鐘,“現在是下午一點,你孩子該上學了吧?”
“嗯。”
“去她爺爺家把孩子接回來,然后送她去上學吧。”
他說完這句話,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等待,實際上,他只等待了不到三秒鐘。
“好。”他說。
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掛了電話,站起來,他等不到來交班的同事和那個聲稱只會“離開一小會兒”的同事來了。他必須走了,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他從抽屜里把那瓶藥拿出來揣進兜兒里,然后披上了外套。
電話又響了。
他已經走到門邊,準備開門出去,他又猶豫了。他奇怪今天的電話怎么這么多。平常不會是這樣。
好吧。這是最后一個。
他回來,接起電話。
“喂?”
“你好。”
“還是你?”
“嗯?”
哦,他似乎有點兒認出這個聲音,于是他說,“還是我。”
“你還沒走?”
“我正準備走。”
“哦,我沒什么事,我還和我的狗待在一塊兒。”
是第一個打電話來的那個老者。
“您沒出去吃點兒東西?”
“沒有。我沒法出門。”
他聽了不知怎么有些惱火,不就是死了一條狗嘛!他心想。
不過他還是說,“總有辦法的。”他說,“總有辦法的。”
“我不知道。”
“您很喜歡這條狗嗎?”
“也談不上吧,就是這么隨便養著。”
“它死了您很傷心?”
“好像也不。”
“那您是遇到了什么別的事?”
“也沒有。一切都挺好的。”
“那……”他沒說下去,這種情況不太常見。打電話來的總是那些陷入了真正的絕境的人。
“我就是找不到一個出門的理由了。”
“您餓了,就該吃飯,尿急了,就該上廁所,出門哪兒需要那么多理由啊?”
“說是這么說。可是我好像找不出一個活下去的理由了。”
“那么您想死?”
“我不知道。”
哦,那這就難辦了。一個人既不想活著,也不想死。沒有真正的麻煩,可是又沒有活下去的愿望。這太難辦了,這簡直超出了他的幫助范疇。
“您可能只是需要和人說說話?”他詢問。
“好像也不是,也沒什么可說的。”
唔。他沉默了。
“不如你跟我說說你吧。”電話那頭忽然說。
“我?”
“對,講講你為什么想活著。”
他想了想,說,“我也不知道。”
他又想了想,說,“我以前有個很尊敬的老師,他后來死了。”
“哦?怎么死的?”
“自殺。”
“為什么?”
為什么?這多難解釋啊,他想。那么多的痛苦和絕望,怎么能一句話和一個陌生人解釋清楚,他想。
“因為……他是研究數學的,他工作上出了點問題。”
“怎么了?”
“他和一個學生有了戀情。他那年正突破了一個很重要的研究。研究結果太驚人了,別人都不相信,正好這時他的戀情曝光,他們就轉而攻擊他的人品,連帶學術成果也沒通過,教職也差不多丟了。”
“這太不像話了,談個戀愛而已,至于么?”電話那頭倒是憤憤起來。
他苦澀地笑了一下,這又該怎么跟對方解釋呢。解釋不清,越解釋越亂。在美國都解釋不清,何況中國?
于是他說,“總之他沒承受住打擊,就自殺了。”
都是這樣的,都是沒抗住打擊,就自殺了。誰不是呢?每個驚天駭浪的死,到頭來說起來都差不多。
“那真是太遺憾了。”
“是有些。”
“是你的老師,那你也別太難過了。”
“十年前的事了,我早就不難過了。”
是啊。他說出來才發覺,都十年了。他的確已經不再難過了。
他死以后,他遵循著他們原本計劃一塊兒要去的地方列出的那張清單,一一造訪。他還活著的時候,他們原本有很多次機會可以動身,最后都因為他要做研究而沒能成行,后來那個清單就被他笑稱是他畫的餅,當他再說要去哪里哪里的時候,他就半是開玩笑半是埋怨似的說,“您又在畫餅啦!”他也沒什么反應,下一次仍然會在半夜突然發條信息過來,“咱們去里斯本吧。”于是,這個清單就越變越長。他光是勾掉那張清單,就花了好幾年的工夫。賺錢,攢足了錢就上路,錢花光了再繼續賺錢。勾完那張清單,他又回到了他們以前常常散步的那個校園,站在那棵他們總是一起坐而論道的樹下,他們在那里談論過費曼、芒德布羅集合、黎曼空間,談論過李白、莊子、《七俠五義》,談論過克爾凱郭爾,“信仰拒絕理解”,他問他,“數學是你的信仰么?”他答,“不,它是我的使命。”完了他問,“你呢?”他淺淡地笑笑,把那句話放在心里,“你是我的信仰。”后來,他不再覺得對方是自己的信仰了。他慶幸沒說出來。這話太流于抒情,怎么解釋得了愛呢。
他死了之后,他老是想起小時候讀《約翰·克里斯多夫》記住的那個結尾,克里斯多夫問那個被自己救下的孩子,“孩子,你是誰啊?”
“我是即將到來的日子。”
他想著這句話,這才挨過了前五年。后頭這五年,他回了國,換了幾份工作,都覺得不安寧,最后才換到這里,盡管他不是太喜歡他的同事們,也不喜歡繁瑣的表格和數據。他也不是想救人,也不是想麻痹自己,他就是想知道,其他人都是為什么想死,又怎樣活了下去。
嗯,十年了,他已經來到了他死去的年紀:他的確已經不再難過了。可他為什么還是覺得找不到一個出口呢。大部分時候,他平靜而不痛苦,那么,他又為什么決定要去……
“我明白了。”他講。
“怎么?”電話那頭問。
“你擱淺了。”
“什么意思?”
“就像一條魚被浪沖到了沙灘上,擱淺在一小攤水域里,暫時死不了,可又活不下去。”他感覺自己說這話的聲音有些不對,一擦眼睛,才發現哭了。這是他死后他頭一次哭。
“好像有那么點意思。”
“但是,”他清了清嗓子,努力恢復一點活力,“你看,旁邊就是大海,你只要用力跳一跳,就能回去。”
“要是旁邊沒有大海呢?”
“怎么會呢?魚總是從大海里蹦出來的。”他把眼淚抹去。
“嗯,好像是這么回事。”
“現在,出門吃個飯,然后找人來一起把你的狗葬了。”他頓了頓,“好好葬,讓它安心地走,好嗎?”
“好。”
他掛上這個電話,請假的年輕同事和那個大媽都來了。他終于舒了一口氣,這回可以回去睡覺了。
“高老師實在不好意思!”
“沒事。”他講,“誰家還沒有個急事呢。”
他走了之后,那位小李和那個大媽才走到他的桌前,翻箱倒柜,最后在垃圾桶里發現了那盒安眠藥。
“真懸啊!”小李拍著胸脯說。
“懸啥啊,我找的人,能不靠譜么?”
“真厲害,您是從哪兒找的這些人?”
“我們話劇團的演員啊。”
“演得可真像,說要殺人的那位,我都差點兒信以為真了!”
“可不。他老演殺人犯,這點兒水平哪還沒有?”
“就是那老頭差點兒意思,怎么翻來覆去也說不到點子上。
“你讓一個沒想過死的人演一個要自殺的人,他有那個意思也沒那個情緒啊。”
“不過好歹是讓高老師暫時放下尋死的念頭了。”
“這可沒準兒,說不定哪天他改跳樓了,那咱們就沒辦法了。”
“唉,也是,咱們拖得住他一時,拖得住他一輩子?”
“盡力吧,生死的事兒,誰能保證呢。”
他們正聊著,忽然一個電話響起。他倆都嚇了一跳,小李看手機,“是高老師打來的。”
兩人一下安靜了。小李接了手機,“喂?高老師?”
“下禮拜我想請個假。”
“請假?”
“嗯,我想出趟門。”
“去哪兒啊?”
“冰島。”
“好的,您到家了嗎?”
“到了。正準備睡覺呢。”
“好的。”他松了一口氣,“睡一覺一切都會好的。”他講。
(選自《山西文學》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