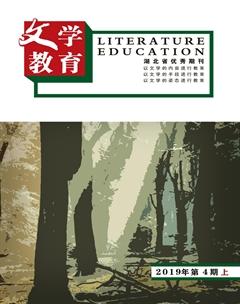試析清末民初西源外來詞漢化的審美心理
內容摘要:清末民初是中國近代社會重要的變革期,受到西學東漸的影響,大量外來詞涌入到漢語詞匯系統。在引介的動態過程中,勢必要經歷一個漢化的過程。本文從影響外來詞漢化的“審美心理”入手,探究其中規律和動因,從而進一步明確清末民初西源外來詞傳入和融合的特征。
關鍵詞:清末民初 西源外來詞 漢化 審美心理
一.清末民初西源外來詞概況
漢語史研究中,“清末民初”指的是1840年鴉片戰爭結束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1],此時正處于近代社會的重要轉型時期,社會的劇變,尤其是與外部世界接觸的增多,都為外來詞的大量產生創造了條件。我們以能反映此期語言特色的經典著作和字詞典作為語料來源,從中搜集并整理了“清末民初西源外來詞詞表”,并在此基礎上對此期的外來詞展開全面的探討。總的來說,在我們的統計范圍內,清末民初的西源外來詞共有615個,這些外來詞涉及科學技術、醫藥衛生、軍事、經濟、教育、社會文化等眾多領域。從類型來說,主要分為“單純音譯、諧音音譯、造字音譯、音譯、意譯結合、音譯+義標”這幾類。這些外源詞在納入漢語系統之前,勢必要經過“漢化”的過程,從語言內部來說,漢化不免受到漢語音節、文字等因素的影響,從語言外部來看,如何克服中西方的審美心理差異也是漢化的重要動因。本文即從其中的審美心理入手,重點探究其中的規律,從而進一步明確清末民初西源外來詞傳入和融合的特征。
二.西源外來詞漢化的審美心理研究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隨著外來文明的不斷涌入,新興外來詞也逐漸增多,但這并不意味著要不加選擇全盤吸收,外來詞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與漢民族審美心理的契合程度,這正如葛本儀所說,“在語言產生之后任何詞的產生都是人們思維活動和語言材料結合作用的結果。”[2]漢民族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逐漸形成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審美心理,對于美感的向往和追求也對外來詞的借入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下面結合實例說明。
(一)求美心理
漢民族歷來崇尚和諧的美感,在語音方面也不例外。漢語同印歐語不同,講求“聲韻調”的配合,這種“聲韻調”的和諧古已有之,這種“求美心理”在漢字及其使用中也有所體現。由于漢字具有表意特性,在長期使用的過程中,有些字會帶給人美感,有些字則會令人反感,這種積累下來的認識在人們的頭腦中形成了思維慣性。例如“鄙”,其本義是指“一種行政單位”,后來它逐漸引申出形容詞義項“未開化的,缺乏教養的,粗俗的”,如“粗鄙、卑鄙”等,所以該字帶給人一種貶義的色彩認識。在求美心理的影響下,在翻譯英語中的“bi”音節時,譯者一般不會使用“鄙”,而往往會采用與之同音的“比”“畢”等。可見,如果在翻譯的過程中出現了若干同音備選譯字時,那些在心理上會造成反感的漢字,就必然會被首先淘汰。漢語中不少流傳至今的音譯詞,大致都經過了這樣一個汰選過程。
【巧克力】
(1)蔗糖粉,九六0公分;巧克力粉,二四0公分。(周纘善《小工藝》)
“巧克力”源自英語“chocolate”,該食品早在19世紀初便傳入中國,當時馬禮遜在《廣東省土話字匯》中將其音譯為“知古辣”,當然,這可能是受到當地方音的影響,但是這三個字的組合很難和巧克力香甜可口的味道聯系在一起,尤其是“辣”甚至還會帶給人誤解。與之類似的是“chocolate”的其他譯名,諸如“炒扣來”“勺勾臘”“豬古辣”等,都無法帶給人一種美好的想象,同時也難以引起人的食欲。而“巧”字在漢語中多具有褒義性,如“靈巧、乖巧”等,用作外來食物的譯字較具有美感,更易于被漢民族所接受。與之類似的如“可可”(cocoa的音譯),從字面上就要比其他音譯形式“茍茍、寇寇、高告”具有美感,從發音上來說也較為響亮,用來音譯飲食類外源詞也是較為貼切的。
【安琪兒】
(2)葉只說了個我的安琪兒,便擁住沙妮亞不放。(陳辟邪《海外繽紛錄》第二十二回)
“安琪兒”即天使,源于英語“angel”。此詞在《國語辭典》中的釋義為“人形有翼,常系男性少年,亦作美麗者之通稱”。單從譯音角度來看,音節“-gel”譯為“其、奇”等同音字也未嘗不可,但卻不能生動地描繪出天使的形象。“琪”《玉篇·玉部》釋為“玉屬”,《漢語大詞典》作“美玉”解,它在后世經常作為語素出現在“琪花、琪草、琪樹”這樣的組合中。以“琪樹”為例,它最早指的是“仙境中的玉樹”,此時“琪”仍是本義“美玉”,但在后代,“琪樹”引申出了“亭亭玉立的美人”這樣的比喻義,如溫庭筠《女冠子》:“雪胸鸞鏡里,琪樹鳳樓前。”可見,“琪”的語義已經發生了變化,具有一種“美好”的意味。再如后來產生的“琪殿”即指華美的宮殿,如祝允明《宮觀》詩:“琪殿臨高臺,時聞落瑤磬”,“琪琚”可以比喻美妙的言辭等,這都反映出了同樣的表義傾向。在今天,“琪”多用于女性名稱中,從中也能看出它隱含的“美好”之義。因而,在對譯“angel”的過程中,“琪”這種字形上的“言外之意”能與源詞緊密相合,也更符合中國人的求美心理。
【雪絲黛】
“雪絲黛”即姐妹,英語“sister”的音譯形式,此詞在張德彝《歐美環游記》中已經出現。“黛”《說文》釋為“畫眉也”,看到這個詞就很易聯想到女子的一彎黛眉,頗具美感,“雪”亦具有純潔無暇的特性,可以說,二者用在女子的命名上再合適不過。所以,雖然從語音的角度來說,“雪絲黛”并不見得完全忠于源詞,但卻比較符合中國人的求美心理。事實上,求美心理的突出表現就是體現在人名翻譯上,例如民國中期美國女作家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其姓名如直接音譯則為“珀爾·賽登斯特里克·布克”,但她的父親是長期居住在中國的傳教士,于是按中文習慣,取美國姓氏中的首字“賽”為中姓,名字則直接意譯為“珍珠”。“賽珍珠”這個譯名不同于以往以單純音譯為主的外國人名,但卻傳達了“比珍珠還要珍貴、光彩熠熠”的信息,而且“珍珠”用于女性名稱也有“珠圓玉潤”的美感。再如近代第一部翻譯小說,由清人蔣其章于1875年翻譯出版的《昕夕閑談》(譯自英國小說家愛德華·喬治·布韋爾·利頓創作于1841年的長篇小說Night and Morning),其男主人公最終與三個戀人中的第一個“Merville”夫人訂婚,這個法語名字被作者譯作“美費兒”。如果從記音的角度來說,它并不是最貼近原詞的,但從這個譯名中仿佛能感受到女性柔美、嬌弱的一面,所以是符合中國人的求美心理的。同樣,男主人公Morton被譯作“康吉”,很明顯也是受到了漢民族審美心理的影響。如果從歷時發展的角度來看,類似于“美費兒”這種譯法今天在港臺地區較為普遍,尤其是臺灣地區更傾向于選擇女性度較高的字[3]。例如,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夫人“Michelle”,大陸地區譯作“米歇爾”,臺灣地區則使用更加女性化的“蜜雪兒”,從字面來看,后者無疑更具柔美的感覺。再如上述二人的女兒“切爾西(Chelsea)”,臺灣地區譯作“雀兒喜”,大致也體現了同樣的規律。
(二)求雅心理
在中國,自古就以“禮儀之邦”聞名,因而漢民族一直崇尚高雅文明,避免粗俗。有關“雅”的命題提出得很早,它常和“俗”作為一對矛盾而出現在人們的論述中。孔子早在先秦時期便提出:“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這其實就是“求雅”心理在文學藝術中的一種朦朧體現。再如曹丕《典論·論文》:“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這里的“雅”主要指的是文辭上的清雅、脫俗。直至近代嚴復《天演論·譯例言》中對于翻譯仍堅持“信達雅”的標準。可以說,從古至今,中國人崇尚美感雅致的心理也一直影響著造詞活動,對于外來詞的翻譯也不例外。這一方面體現為用字的“典雅”,一些較為粗俗,能帶給人反感的字眼盡量通過諧音的方式將其雅化,另一方面,為了追求文雅的效果,對一些不便言明的事物往往采取回避或委婉的方式。
【夏娃】
(3)吾等之始祖亞當、夏娃,即系作工之人。(馬林譯李玉書述《英國立憲沿革紀略》)
“夏娃”是人名,是英語“Eve”的音譯形式,此詞最早見于19世紀60年代,如張德彝《航海述奇》中便有“夏娃”。在當時還有人將其譯作“厄襪”。比較而言,“襪”與“娃”語音相同(對于無聲調語言而言,二者的音調不起辨義作用),但從用字角度來說,“娃”更加雅致,別具意味。在中國古代就流傳的“精衛填海”的傳說,其中“精衛”在《山海經》中被描述為:“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可見“娃”出現在女性名稱中由來已久。再如《漢書·揚雄傳上》:“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其中娵、娃連用,顏師古注:“娵、娃皆美女也。”再如金元好問《芳華怨》詩:“娃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裊裊春風前。”這里的“娃”顯然不是指“小孩”,而是指“美貌女子”。從這些用例可以看出,“娃”自上古時期便可表“美女”,并且該用法在后世一直得到了承用,直到今天還有“嬌娃”的用例。所以,從翻譯的角度來說,“娃”不僅對應了音節“-ve”,也直接體現了女性美貌的特點,而且“娃”顯然要比“襪”雅致許多。同時,“厄”在漢語中常表“困苦、災難”,往往與“厄運、厄難”搭配,所以僅從字面上來說,就會帶給人一種不好的聯想。由此可見,“夏娃”一詞取代“厄襪”這是符合漢民族“求雅”心理的。
與之類似的還有英語“olive”,它亦從“阿利襪”的最初譯名逐漸轉換為了“橄欖”,后一譯名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香檳酒】
(4)他心上一急,一個不當心,一只馬蹄袖又翻倒了一杯香檳酒。(李伯元《官場現形記》第七回)
“香檳酒”源于英語“champagne”。它約在清代中期傳入中國,最早曾被譯作“三邊酒”,道光時期《香山縣志》的《輿地》篇中曾提過來自西洋、佛朗西諸國的酒,其中之一即為“三邊酒”。此外,它還被譯作“三鞭酒”,道光六年編著的《皇朝經世文編》中有過這樣的記載:“……果行又極多制造三鞭酒、菩提酒、啤酒……”而且在清末民初的多部英漢詞典中“champagne”均被譯作“三鞭酒”,可見以上兩個譯名在當時比較通行。如果從記音角度來說,二者與源語都比較貼近,但從字面來看,尤其是“三鞭酒”絕對稱不上是“雅”。事實上,晚清時期的小說中曾出現了“三鞭酒”,例如《宦海鐘》第十二回:“這個種子秘方,似乎比那些龜鞭再造丸、三鞭酒要驗些呢,有錢無子的須要試試。”可見,上例中的“三鞭酒”其實是指由三種雄性動物的生殖器泡制的強身酒,所以它是一個偏正式詞語,和音譯詞“三鞭酒”是兩個不一樣的詞,只是恰好形式相同而已。但是,可能是受到了漢語固有詞的影響,“三鞭酒”容易造成“壯陽酒”的誤解,而且本身也與“champagne”帶給人那種高雅、洋氣的感覺不相符,這可能也是它無法留存下來的原因。相對來說,“香檳酒”出現的時間并不早,不過在清末民初的眾多小說,如《海上花列傳》、《孽海花》、《官場現形記》等作品中已經普遍采取了“香檳酒”的譯法。從字面來看,“香”突顯了酒味醇香撲鼻的特點,而且要比“三鞭酒”來得雅致,所以更符合中國人的審美心理。當然,棄“三鞭酒”而不用還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主要是因為它名不符實,容易產生誤導。
再如“咖啡”,它產生于吳方言區,最早出現在上海美華書館出版的《造飯洋書》中,當時被音譯為“磕肥”。“肥”在普通話中指脂肪較多,通常用來形容動物,若形容人的話,往往帶有貶義或者蔑視的色彩,例如“腦滿腸肥、食言而肥”,都是偏于貶義。所以,如果把“肥”用于飲品名稱中,可能給人一種喝了之后會變肥,變得臃腫之類不好的聯想,給人一種不甚雅觀的印象。而其他音譯詞,無論是“加非、 啡”還是“咖啡”,整體來說都比較中性,所以更適合作為“coffee”的譯名。值得一提的是,日語中“coffee”(コーヒー)是用漢字“珈琲”來表示的,據考察,“珈琲”是由日本江戶時代的蘭學家宇田川榕庵所使用的[4],這兩個字在漢語中古已有之,從王,表義均與“珠玉”相關,日語譯法注意使用了好字眼,但是這種形式并沒有取代漢語的“咖啡”(中國某些地區也出現了該形式,如武漢、上海等地一些咖啡館的招牌用字),可見這是兩種不同的取向。漢語的“咖啡”從口,更強調它的“入口”特性,而日語則強調它的美好一面。
此外,此期一些西洋樂器的名稱也體現了“求雅心理”,如“piano”被譯作“批雅娜”,“violin”被譯成“梵婀玲”,“flute”譯為“弗柳德”等,這或許與西洋音樂本就被當時國人視為高雅音樂有關,因而在用字上也要向“雅”靠攏。
(三)求吉心理
這種審美心理從本質上來說源于漢民族的“趨利避害”心理。由于中國長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對“福、祿、壽、喜”的追求亙古未變,這種思想在語言中也有所體現,人們盡量摒棄對人身有害的兇惡的字眼,而去選取蘊含“吉利、喜慶”色彩的詞語來表達對吉祥福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海洛因】【鴉片】
(5)最毒無如海洛因,嗎啡雖烈遜三分。高居鴉片紅丸上,北地人多白面稱。(葉仲鈞《上海鱗爪竹枝詞》)
二者都屬于毒品,前者源于英語“heroin”,后者譯自“opium”。毒品在近代中國是一種很特殊的存在,早在明代,鴉片就已經輸入中國,到了清道光年間,英國為了扭轉貿易逆差,開始通過走私毒品而獲取暴利,當時的清政府也逐漸認識到了鴉煙流毒之害,為了查禁和抵制毒品輸入,任命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廣東虎門集中銷毀鴉片。“虎門銷煙”成為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在此之后,有識之士紛紛對鴉片的危害進行了口誅筆伐。“heroin”是“鴉片”的高度提純物,它們的危害性在近代作品中屢有論及,如資產階級革命家朱執信在《嗎啡之毒》中提到:“吸鴉片者,面目灰敗,精神率萎,眾所周知。而打嗎啡針者,抑又加甚……喜羅英之毒,又甚于嗎啡、鵠肩。”[5]由此能清楚地看出毒品對人們身體所帶來的巨大危害。這樣的“毒害”本應是為人厭棄,唯恐避之不及的,但是從它們最初的譯名中卻很難看到這個特點。“opium”曾被譯作“雅片”,如作于道光九年的《東槎紀略》中有過這樣的論述:“賭館、娼閭、檳榔、雅片,日寢食而死生之。”“雅片”譯名留存時間較長,直至光緒二十年的《盛世危言》中仍有用例。而“海洛因”在上世紀初曾被譯作“喜羅英”或“喜羅因”并廣為流傳。這樣的譯名與毒品帶給中國社會的損害嚴重不符。試想,對于一個首次接觸“雅片”或“喜羅英”的人來說,僅靠字面理解,他很可能會產生與詞義背道而馳的聯想,這也不符合中國人“趨利避害”的文化心理。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同樣產生于晚清的“鴉片”,其使用頻率遠超“雅片”,并逐漸替代了后者;“海洛因”的出現時間較晚,大概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才出現,但是由于避免了“喜羅因”帶給人的誤解,所以也逐漸取而代之并一直沿用至今。
【來復槍】
(6)本公司在英國白明哈門地方開設,專造各種槍,即鳥槍、來復槍、手槍等。(傅蘭雅輯《格致匯編第二冊》)
“來復槍”是一種膛內刻有螺旋形槽線的步槍,源于英語“rifle”,來復槍引入中國的時間較晚,大約在19世紀末才出現,最早它曾被譯作“來福槍”,這在1899年鄺其照《華英字典集成》中有所體現,1908年顏惠慶《英華大辭典》中仍保留此譯名。僅從記音的角度來看,“來福”“來復”除了音調上稍有差異,其他并無不同,但從文化心理來看,“槍”本身屬于殺傷性武器,尤其是經歷了鴉片戰爭中“洋槍洋炮”的荼毒,人們對于“槍”有一種本能的“避害”心理,試想,這樣一種武器怎么還會“來福”呢?這個名稱很顯然與中國人的“求吉”心理相抵觸。而“來復槍”的名稱比較偏中性,不會給人帶來不好的聯想,1916年赫美玲《官話》就使用了這個譯名,并且一直保留至今。
我們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例子,魯迅《南腔北調集》中提到了“高而富球”:“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其實golf在當時已有“高爾夫球”的譯法,之所以用“高而富”來命名,是因為作者有意為之。從例句也可以看出,作者特意選取一些吉利的字眼,如“高”“富”,但實際卻暗含諷刺,那些富人好吃懶做,寧可花大把銀子去打只有富人能享用的“高而富球”,也不會自覺運動的形象躍然紙上。試想一下,該句如果用“高爾夫球”,勢必達不到同樣的反諷效果。
三.結語
從以上三個方面可以看出,漢民族的審美心理特點對于音譯外來詞的在選字及定形上的制約和影響,可以說,在音譯的過程中,人們總會不時受到民族思維的影響,在翻譯的過程中融合了漢民族的好惡心理,這是一個隱藏的動態的過程,而最終定型化的音譯詞就仿佛是鏡子一般,它折射出的便是漢語思維最形象化的體現。
參考文獻
[1]刁晏斌.試論清末民初語言的研究[J].《勵耘學刊(語言卷)》,2008(2).
[2]刁晏斌.現代漢語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3]劉蘭民.試論影響漢語造詞的因素[J].《語言文字應用》,2005(1).
[4]馬西尼.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的漢語外來詞研究[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
[5]潘文國.漢語音譯詞中的“義溢出”現象[A].載《社會語言學論文集》,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2.
[6]王偲,張燁.從“silk”一詞的生成及演變看“絲綢之路”的現實意義[J].《文化學刊》,2016(9).
[7]張岱年.中國思維偏向[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注 釋
[1]刁晏斌:《試論清末民初語言的研究》,《勵耘學刊(語言卷)》,2008(2).
[2]葛本儀:《漢語詞匯形成的基礎形式》,《山東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
[3]刁晏斌,鄒貞:《基于計算的海峽兩岸女性譯名性別義溢出情況對比研究》,《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年第2期。
[4]轉引自搜狐網《咖啡愛好者冷知識》,網址為:http://www.sohu.com/a/149942157_409217。
[5]朱執信:《朱執信集》,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60頁。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百年漢語發展演變數據平臺建設與研究”(項目號:13&ZD133)的階段性成果;2018年大連民族大學中央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項目號:20180305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介紹:張燁,博士,大連民族大學文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漢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