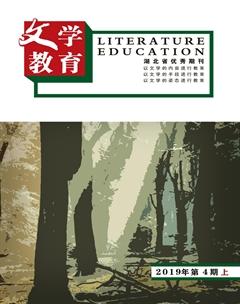悲涼的幸福
馬志倫
宋代大文學(xué)家蘇東坡說(shuō)過(guò):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本來(lái)人生在世,悲歡離合總是免不了的。然而盡管理論上是如此說(shuō),作為感情動(dòng)物的人,真正遇到了悲歡離合,特別是悲苦和離別,不是用理論能夠化解得了的。生活中的甜酸苦辣不是那么容易忘得了,更有一種悲涼的幸福那將是刻骨銘心,永志難忘。
這一年上海的夏天,天氣是如此的炎熱,35℃以上的天氣超過(guò)以往任何一個(gè)夏天。但是對(duì)于我,這一年的夏天是如此的悲涼,父親被查出了癌癥,而且確診為是癌中之王的胰腺癌。本以為科技昌明的今天,對(duì)付兇魔一般的癌癥,人類已有了克敵制勝的辦法(我從報(bào)刊上的廣告中了解到),不過(guò)醫(yī)生的一席話徹底泯滅了我天真的幻想。我沒(méi)有學(xué)過(guò)醫(yī)學(xué),但對(duì)祖國(guó)的文字終究是認(rèn)識(shí)的,從厚厚的醫(yī)學(xué)書(shū)籍中,我明白了這種疾病目前只是進(jìn)展到查出和確診這一步,治愈幾無(wú)可能。悲涼慢慢地涌入了我的心頭:我無(wú)能為力了。
我仍然寄存一線希望——當(dāng)父親被推進(jìn)手術(shù)室時(shí)。聽(tīng)人說(shuō)從手術(shù)時(shí)間的長(zhǎng)短中就可以知道手術(shù)是否成功,午后的病區(qū)長(zhǎng)廊寥無(wú)一人,煢煢孑立的我呆呆地望著長(zhǎng)廊的盡頭——那是手術(shù)間的玻璃門。父親并沒(méi)有如所說(shuō)的需要時(shí)間就從手術(shù)室出來(lái)了,身上插滿了各種管子,他被護(hù)送進(jìn)了重病房。
“你快回去吧,明天還要上課……”想不到父親睜開(kāi)眼認(rèn)出我的第一時(shí)間內(nèi)竟如此說(shuō),百感交集之中無(wú)語(yǔ)凝咽。我的教師工作本是普通,我也是平平凡凡地做好本職工作,然而父親卻對(duì)此看得那么重,關(guān)懷我甚于他的生命。在人世中,能被關(guān)懷就是一種幸福,只是這種幸福在我心中摻雜了悲涼。
接下來(lái)的日子是每天下班后的跑醫(yī)院。夏天已經(jīng)過(guò)去,秋陽(yáng)依舊火辣,有誰(shuí)能理解我去醫(yī)院路上的那種幸福感覺(jué)!平時(shí)對(duì)醫(yī)院敬而遠(yuǎn)之畏怯如虎的我,現(xiàn)在卻覺(jué)得是如此的親近,因?yàn)檫@里有我最親愛(ài)的人在祈盼著我——父親嘴上從沒(méi)有這樣說(shuō)。“父親,你要快快地好起來(lái)!”我的心聲只有我自己聽(tīng)得見(jiàn)。我看到了父親從重病房移到了一般病房,看到了父親從病榻上立起來(lái),看到了父親坐在病床前吃著晚餐——如水一般的米粥,那禿禿的頭頂上始終殘留的幾根稀發(fā),如同生命一般的頑強(qiáng),這是那個(gè)曾經(jīng)生氣勃勃引領(lǐng)我走進(jìn)這個(gè)世界的父親嗎?看著他如往日一般地露出笑容,剎那間我在懷疑醫(yī)生是否診斷錯(cuò)了。
然而科學(xué)是不容懷疑的。出院?jiǎn)紊系慕Y(jié)論一欄里分明寫(xiě)著“××癌”。
一切恍如隔世。父親又回到了他熟悉的老屋,他睡的床,他坐的躺椅,依舊做著他喜歡做的剪報(bào),和他所愛(ài)的人一同圍著一起吃飯(大多數(shù)的時(shí)候是看著愛(ài)著他的人)。或許他真的以為他會(huì)好起來(lái)的,抑或他已經(jīng)知道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縷時(shí)光,如果父親已經(jīng)了然,那是一種悲涼的幸福,如果父親依然不覺(jué),那是一種幸福的悲涼。
父親終于還是走了,“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現(xiàn)在每當(dāng)我佇立在他的墓前,望著他照片上的笑貌,又會(huì)時(shí)時(shí)感覺(jué)著那悲涼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