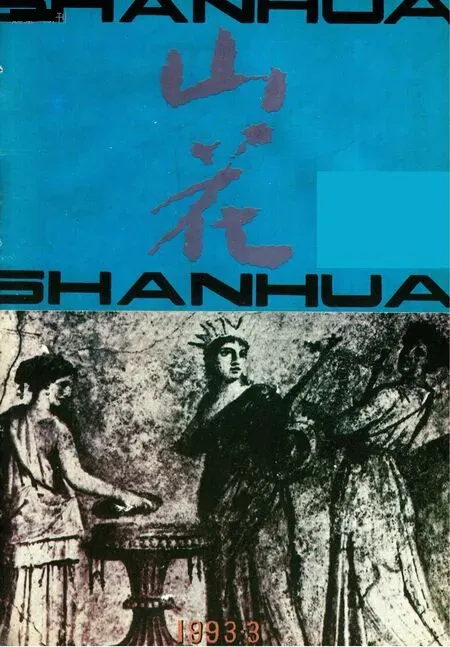你到底想要什么
一個男人(我不認識)拿著打火機在玩兒,打火熄滅,打火熄滅,樂此不疲。突然打火機出現了問題,在他手上燒成了一團火,這是打火機爆炸前的先兆。
男人并沒有扔掉打火機,幾秒鐘以后打火機在他手里爆炸了,滿天飄散著黑色的灰燼。我說的是打火機的灰燼,玩兒打火機的男人并沒有被炸死,他僅僅是被炸黑了。他一臉焦黑地被一群男人裹挾著朝前走去。說“裹挾”也許并不準確,他很可能是自愿加入他們的隊伍的。
這是一群待挑選的男人。至于挑選出來干嘛我也不大清楚。我只知道他們在待挑選前已經是被挑選過的了,也就是說不是隨便哪個男人都可以加入這支隊伍的。至于是誰挑選的他們,挑選的標準又是什么我同樣不大清楚。
這些被挑選出來的男人們沉默地朝前走著。也許他們被挑出來的目的就是為了“朝前走”。至于去哪兒無關緊要,哪個方向是“前”也全憑你個人的理解。
我似乎有一些理由認為這些男人是挑選出來給女人當“男伴”的。他們很快就被挑光了(你不必驚訝他們在行走過程中就被挑走),只剩下那個玩兒火自焚的男人一個人孤獨地走著。這很可能跟他燒焦了的面部有關,當然這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我走到他旁邊牽起了他的手(這是否表示我選中了他?)
他朝我露出了感激的笑容,當然那笑容在外人看來與嘲諷無異。
別誤會,我并不愛他,我只是執意要跟這個我不愛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別問我為什么,我他媽的怎么知道。
更加令人驚喜的事情發生了:另一個男人(我同樣不認識)朝我們走了過來,他在另一側牽起了玩兒火男人的手并向我微笑示意。我愉快地決定和這兩個男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我將和我的這兩個朋友共度余生,以“友誼”之名。
那么我們該不該做愛呢?我想那個玩兒打火機把自己燒壞的男人我是一定要跟他做的,于情于理我都應該。至于后來的那個男人我還需要再考慮考慮。
這個夢能否證明我是一個極富同情心的人呢?完全不能,在現實生活中我是一個毫無同情心的人。這個夢只能證明夢證明不了任何東西。當然了,你也可以選擇相信夢里的我才是真實的。
我覺得每個夢都像是藝術品,沒法兒如實復制而只能用“記一漏百”的文字去記錄實在是太遺憾了。
我認為最具藝術品特質的夢應該是惡夢。
我經常做在懸崖峭壁上行走的惡夢,而且一走就是好幾個小時(我指的是夢里的時間)。如果是在現實中有恐高癥的我肯定早就被嚇死了,但是在夢里我健步如飛義無反顧,感覺十分驚喜與開心。我可能已經瘋了。
我還經常做從很高的樓上跳下來的惡夢,我指的是主動跳而不是失足,這的確是我在現實當中考慮得最多的一種死法。在夢里我總是下降得十分平靜與悠然,以至于有一次我還在空中說了一句“我愛你”。遺憾的是我忘了是對誰說的。
更遺憾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從來就沒有如此平靜和悠然過,我總是神情緊張神經兮兮的。當然,你同樣可以認為夢里的我才是真實的。
我已經徹底醒了,看了一眼還在熟睡著的老公。
我老公王強長得很帥。所謂的“帥”也就是人們公認的標準——長睫毛,大眼睛,高鼻梁。
我認為男人長成這樣十分可笑。
我認為男人應該長得丑一點兒,像一只“狼”,至少像一只“狼狗”。如果你不小心長成了一只“泰迪”,應該為此覺得羞愧。
不光長相,王強的身材也堪稱完美——一米八的身高,一百四十斤的體重,八塊腹肌。這得益于他每天下了班兒都會在單位的健身房練上一個多小時。
他這么做完全是多此一舉甚至適得其反,我喜歡瘦得只剩下骨頭的男人。
不光長相和身材,王強的性格甚至也堪稱完美——沒有脾氣,對我極盡甜言蜜語溫柔體貼之能事。而我恰恰喜歡對我呼來喝去頤指氣使的。
一只蚊子落在了王強的長睫毛上,它伸了伸腿,疑惑地看著眼前黑色的“蘆葦叢”,把針扎進了王強的眼皮。我看著它吸飽了王強的血安全地飛走后才踹醒了王強。
“趕緊起來啊,都幾點了”我大聲說道。
“老婆,抱會兒。”他睜開了眼睛,把我摟了過去。
“把你的手拿開,勒死我了。”
“老婆,今天我休息咱們出去玩兒吧?我都好幾個禮拜沒休大禮拜了。”王強在我們縣公安局工作,去年剛提了副局長,沒有大禮拜是很正常的事情。
“去哪兒?”我從他的懷里掙脫出來
“我想想。要不去玉子山吧,離得還近,開車一個小時就能到。”
“那帶上爸媽一塊兒去吧,他們給咱們看孩子挺累的。”
“好啊!”
我說的爸媽是我的公公婆婆,我生完二胎兩個月就回學校上班兒了,我公公婆婆搬了過來跟我和王強一起住幫忙照看兩個孩子,準備等第二個孩子上幼兒園之后再回去。這意味著我需要跟公婆再在同一個屋檐下相處三年。
“我有個哥們兒是玉子山景區的負責人,可以給咱們免票。”王強翻了個身,看了我一眼。
“你這是腐敗,我要舉報你。”
“我這只是‘微腐敗。我又不貪污受賄,不就免個門票嗎?”
“‘微腐敗也是腐敗。你別得罪我,得罪我我就舉報你把你送進監獄。”
“那你當老師校外辦班兒算不算腐敗?你也別得罪我。”
“好啊,那咱們互相舉報吧,監獄里見。”
“呵呵。”
“說實話我還真挺想進監獄的,至少換一種活法,不像現在這么沒意思。”
“你覺得現在很沒意思嗎?”王強再次摟住了我。
“我想一會兒把吸頂燈擦擦,太臟了。”我從他懷里掙脫出來,“這個破吸頂燈跟百葉窗一樣,得一行一行地擦。”
“那你當時為什么非要買這么一個像百葉窗一樣的吸頂燈呢?”
“為了一行一行擦它們。”
“好吧。”
“我怎么覺得桌子上那摞書歪了,會不會倒?”
“不會吧?我沒覺得它們歪啊。”
“哦。”
“讓我再抱會兒你,你老躲什么?”
“我沒躲,摟著太熱了,我得起來了。”我從床上坐了起來。
我出了臥室門進了廚房,婆婆正在廚房忙活。她每天早晨都堅持起來給我們做早飯,說外面吃的不干凈。
“媽,做什么呢?”我一臉諂媚地走了過去。
“面條。”
“真香。”
“我做什么你都說香。”
“我爸呢?”
“去早市買菜去了。”
“哦。”
“今天休息你怎么起這么早?”
“起來伺候您寶貝兒子唄。”
“得了吧,我就看見過我兒子伺候你。”
“呵呵,您就向著您兒子吧,您就能看得見我使喚他,從來看不見他使喚我。”
“幫我遞一下蠔油。”
“媽我昨天夢見一個男人把自己給點著了。”
“誰?”
“我不認識。”
“夢見死人是好事兒,你今天要發財。”
“問題是他沒死。”
“那他后來怎么樣了?”
“忘了,媽我去洗臉刷牙了啊。”
我洗完臉刷完牙去大女兒的臥室把她叫了起來。她今年八歲,上小學一年級。去年我生完二寶之后就讓她自己一個人睡了。
她被我叫醒之后立刻跑到了爺爺奶奶的臥室去逗二寶。二寶是個男孩兒,一歲零五個月,公公婆婆怕二寶影響我和他兒子休息一直讓二寶跟著他們睡。
“姜彤你別逗弟弟了!趕緊洗臉刷牙練琴去!”我大聲斥責她。
“我不!”
我在縣一中教音樂,還在校外辦了一個鋼琴輔導班。我每天早上都要逼迫女兒練一個小時的琴。等兒子再大一點兒我也要逼迫兒子。
“別玩兒弟弟了!趕緊洗臉刷牙去練琴!”我更加大聲地斥責她。
“我不!”她大哭起來。
“你把嘴給我閉上!再哭我打死你!”我歇斯底里地喊道。
“至于嗎?至于嗎?”王強從臥室里出來了,“不就練個破琴嗎?還要打死我們?過來閨女,爸爸抱。”女兒朝王強走了過去,王強一把把她摟進了懷里。
“媽的她動不動就哭動不動就哭!一個女孩子這么軟弱怎么行!再哭我打死她!”我繼續發泄道。
“女孩子愛哭怎么了?女孩子愛哭很正常。”王強說。
“做人應該把眼淚咽到肚子里,尤其是女人。”
“她還是女孩兒。”
“總有一天會變成女人。”
“變成女人也不至于把眼淚咽到肚子里吧?”
“至于,現在是一個競爭的社會。人必須要對自己狠一點兒,尤其是女人。”
“她才多大?你就讓她對自己狠一點兒?”
“她現在應該趕緊去練琴!要不然我打死她!”
“行了行了,不就練個破琴嗎,還要把我們打死?”
“破琴?你說破琴?這個房子是哪兒來的?你的車又是哪兒來的?”
“是我老婆掙的,我老婆最有本事行了吧?”
“所以她也得好好練。”
“那也不至于動不動就要把她打死啊?”
“我爸媽從小就是這么教育我的。”
“唉,難怪。”
“她長大就知道我是為她好了!”
“那我要是萬一沒長大就死了呢?”女兒問。
“死了就死了!你的琴就白練了!”我說。
女兒再次大哭起來。
“唉,練琴就練琴,你老嚇唬她干什么!”王強說。
“我就嚇唬她了!”我大聲嚷嚷道。
“嚷什么嚷什么?有什么話不能好好說。”婆婆端著面條從廚房出來了。
“您兒子欺負我!”
“我兒子只有可能被你欺負!”
“您就護著您兒子吧!”
“去拿筷子!大早上的你們夫妻倆吵什么吵?”
“讓您兒子去拿!”
門開了,公公買菜回來了。我去廚房拿了筷子,一家人圍桌吃飯。
“我今天在早市碰見老丁了,他假裝沒看見我。”公公退休前是我們縣的副縣長,對別人看沒看見他特別敏感。
“那你想怎么樣?難不成你買個菜還要別人夾道歡迎你?”婆婆說。
“那倒不至于。”公公說。
“小倩說你們看孩子辛苦了,今天想帶你們出去玩兒。”王強說。
“你們倆帶著彤彤去吧。我跟你爸在家看小森。你們好不容易休個大禮拜,出去好好玩玩兒。”婆婆說
“是啊,我們帶著小森出去也不方便。你們去玩兒吧。”公公說。
“一起去,一起去。”我說,“爸媽給我們看小森每天還得接送彤彤上下學辛苦了,我今天就是想帶爸媽出去玩兒的,爸媽不去我就不去了。咱們去玉子山,中午我請。”
“是啊,小倩是特意想帶你們出去玩兒的。一起去吧。”王強說。
“那好吧,一起去。”婆婆說。
“太好嘍!太好嘍!爺爺奶奶也去嘍!”女兒歡呼起來。
“跟爸媽去沒那么開心是吧?”我瞪了她一眼,她低下了頭。
“那我一會兒去樓下挖兩條蚯蚓釣魚用。”公公在轉移話題。
“爸,您看您供的這個觀音菩薩上面是不是有一層水珠?”我看著博古架上的觀音菩薩說,“這兒是不是太潮了?”。
“真的哎,我還真沒注意,”公公說,“觀音菩薩顯靈了。”
吃完飯,女兒去客廳練琴了,婆婆去廚房刷碗,公公去樓下挖蚯蚓,我去衛生間刷洗卸下來的吸頂燈罩,孩子她爸在臥室里打游戲。
一個小時之后我們出發了。孩子她爸開車,我坐副駕駛,公公婆婆和女兒坐在后排,兒子在公公懷里抱著。
我伸手打開了車里的播放器,放起了肖邦的《第一鋼琴協奏曲》。
“故作高雅。”王強打了一下方向盤說。
“你不要胡說八道,”公公說,“小倩就是學音樂的。你覺得是高雅,其實那就是小倩的常態。”
“我就是故作高雅。”我看著車窗前面的路說。
車開了有十分鐘,大家一直沉默,我換了首亞納切克的曲子。說實話我還是只能接受肖邦的“抒情”,無法接受亞納切克的“反抒情”。接受不了我也要聽,以示自己的“高雅”。
我從包里拿出了手機刷起了朋友圈。
我的閨蜜翟井剛剛發了一條朋友圈。我一直都覺得我的這個閨蜜腦子不太正常。她經常在朋友圈里發她自己寫的莫名其妙的詩。比如剛才這首:
早晨
我睜開眼睛掀起被子,
去了趟廁所。
再次回到床上,
蓋上被子,閉上眼睛。
“你這寫的叫什么啊?這也叫詩?”我發微信問她。
“為什么不叫?”
“這東西是什么意思啊?”
“沒什么意思。”
“那你為什么要寫它?總是要表達什么意思吧?”
“我為什么非要表達什么意思?”
“反正你寫的這種詩我讀不懂。”
“這有什么讀不懂的,我就是說我醒了,上了趟廁所,又回到了床上。這么淺顯的意思你讀不懂嗎?”
“我是說我不知道你這首詩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太深奧了。”
“沒有什么深意,就是字面意思,我醒了,上了趟廁所,又回到了床上。現象就是現象而已,背后沒有深意,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平面,沒有深度。”
“那這詩也太淺顯了吧?”
“你剛才說它深奧,現在又說它淺顯。你到底想說什么?”
“我想說你是個神經病。”
“謝謝夸獎。”
“你跟你男朋友怎么樣了?”我問。
“哪一個?”
“上一次的那個。”
“上一次的哪一個?”
“靠!”
“不好意思,我實在是忘了上次帶誰去見你了。”
“姓王,好像是叫王鵬。”
“王鵬是誰?”
“靠!”
“算了,不重要。我上個月剛剛跟我的上一個男友‘手槍散了,上周我給他介紹了一個新女友——小雅”
“小雅是誰?”
“電子女友。放在手機里面的。你也可以認為她是一個‘電子妓女,可以‘網上做愛之類的。”
“靠,這也行?”
“這有什么不行的?‘手槍說‘小雅非常完美,十分性感。‘手槍已經深深地愛上了‘小雅,對‘小雅愛不釋手欲罷不能了。作為回報,‘手槍也送了我一個虛擬男友,是他花了一萬比特幣買的,叫‘無痕。”
“靠!你們現在都跟‘模擬人類談戀愛了?”
“是啊,反正以后人類都要跟‘模擬人類談戀愛,人類的同類實在是太麻煩了,不適合談戀愛。”
“靠。”
“你不覺得人類很麻煩嗎?跟人類談戀愛總是會有各種各樣的麻煩。虛擬戀人不會帶給你任何麻煩,不用你給他做早飯,不用讓你每天陪著他,如果他有這種無理要求把程序關了就可以了。當你需要他陪伴的時候可以再把程序打開,他會不計前嫌地跟你做愛。”
“它可能已經把你拒絕它的事情忘了。”
“不會忘的,它只是懶得跟該死的人類計較。”
“哦,這樣啊。”
“而且現實中的人類總是有各種各樣的毛病,相對于現實中的不盡人意,我們可以通過改變程序把虛擬戀人任意設定成我們喜歡的類型。總之‘虛擬戀人堪稱完美,我們的生活將會越來越完美。我的‘無痕就被我設定成了‘冰柜型,輕易不會搭理我,只有在我罵他的時候他才會還嘴。”
“但是‘虛擬人類也沒有感情啊,沒有感情的戀愛能算是真的戀愛嗎?”
“我覺得我們人類所謂的‘情感事實上只是‘快感的一種,是可以量化的。我們猜想人類以后可以通過服用藥物來獲得‘情感,就像通過服用‘春藥之類的來獲得‘快感一樣。我們可以通過服用藥物來獲得任何我們想要的情感。”
“以后的人類還需要情感嗎?”
“情感當然不是什么必需之物,不想要的話,可以服用去除情感的藥物。”
“呵呵。”
“你現在干嘛呢?出來逛街啊。”我跟翟井幾乎每周都要一起出去吃飯逛街。
“現在不行,我們一家六口出去玩兒,我現在在車上。”
“哦,那改天。”
“你今天下午有空嗎?我下午回來約你。”
“好的,下午約。”
我放下了手機。
“給誰發微信呢?”王強問
“翟井。”
“我一直就覺得你認識的這個翟井不靠譜。”
“靠不靠譜關你屁事兒!有本事你把她抓起來。”
“呵呵,還真沒準兒她哪天犯事兒落到我手里。你告訴她別吸毒別賣淫。”
“憑什么啊!我還想吸還想賣呢!”
“咳咳”坐在后座的公公咳嗽了兩聲。
我低下頭繼續玩兒手機,每個人都繼續沉默。
婆婆在朋友圈轉發了三篇來自一個叫“完美女人”的公眾號文章:《如何做一個精致優雅的女人》《這才是女人該活成的樣子》《到頭來男人都娶了這樣的女人》。我立刻給婆婆點了贊。
一個小時以后我們一家六口終于到達了玉子山景區門口,王強的哥們兒出來迎接我們并給我們免了票。
我們一家六口進了山,四個大人輪流抱著兒子,半個小時之后我們來到了歪桃峰景區。
“真美啊!”王強伸了個懶腰,“云彩都在腳下面。”
“是啊,”我說,“確實很美。”
但是那又怎么樣呢,我想。
從歪桃峰下來我們繼續步行半個小時來到了龍潭瀑布。
景色更美。
瀑布飛流直下,空氣是透明的,潭水清澈見底。
但是那又怎么樣呢,我想。
山泉水看上去很干凈,有不少游客捧起泉水來直接喝,女兒也要喝被我呵斥住了。
“你找死嗎?”我大聲說。
王強站在瀑布前吃起了火腿腸,女兒在岸邊兒壘沙堡,公公在岸邊兒釣魚,婆婆抱著兒子坐在石頭上指給他看潭里的魚。我在潭邊兒傻站著發呆。
公公每釣起一只魚又把它們放回河里。
“您這不是白釣了嗎?”我問。
“不白釣,魚已經死了。”
這就是他釣魚的目的。
女兒壘的沙堡很漂亮,有高高的屋頂,還有窗戶。河里過來一排浪,沙堡立刻消失于無形。女兒哭了。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我說。
從龍潭瀑布景區下來我們又去了“清涼界”景區和“駱駝峰”景區,景色都差不多。
兩個小時之后我們下了山,回到了景區收費口。
我們在收費口附近的一個農家院吃了午飯。要了六個菜:“鐵鍋柴雞”“干燒魚”“醬爆鴨片”“孜然羊肉”“清炒筍絲”“黃瓜拌豆皮”。都很好吃。
但是又能怎么樣呢?我想。
“小倩,你評‘高職有信兒了嗎?”婆婆問我。
“哦,評下來了,前天通知我的。”
“工資能漲多少啊?”
“七八百吧。”
“太好了。”
但是那又怎么樣呢?我想。
我們一家人沉默地吃完了午飯,結賬離開。我掏的錢。
我們開車往回趕,一個小時之后回到了縣城。我在車上跟翟井約好了逛街,先下了車。
我們在縣里最高級的商場“多瑙河大廈”見了面。商場的名字起得挺嚇人,其實只有三層,里面賣的東西也都是一些山寨貨,專門賺我跟翟井這種土鱉的錢。
我們倆轉了一圈兒,像每次一樣提溜著一堆大包小包出來了。
翟井買了三雙鞋兩件衣服。我買了兩雙鞋三件衣服。
“好開心啊!”翟井說。
“是啊。”我說。
但是那又怎么樣呢?我想。
“我們去‘金路易喝咖啡吧?”翟井說。
“好啊。”這是我們每次逛完街必去的地兒。
“我還是得減減肥,”翟井邊喝咖啡邊說,“我好喜歡剛才那條九分褲啊,但是我穿起來顯得好胖。”
“但你穿那條七分褲就很好看。九分褲顯胖七分褲不顯胖。”
“是啊,那條七分褲我拿了,你說配什么衣服啊?”翟井問。
“我記得你有一件紅藍花的長款襯衣跟那條七分褲很搭。”我覺得這兩件東西配在一起能把人丑死。
“哦,那我回去就試試。”
從“金路易咖啡”出來我們又去了旁邊的“春榮會館”做按摩。這也是我們每次逛街的必修課。
“我覺得真沒意思。” 我做著背部按摩對躺在旁邊兒床上也做著背部按摩的翟井說。
“什么沒意思?做按摩?”翟井說。
“都沒意思,吃飯、逛街、買衣服、喝咖啡、做按摩、活著。”
“多有意思啊!”翟井伸了個懶腰,“做按摩多舒服啊!太他媽舒服了!”
“是舒服,但是那又怎么樣呢?”
“呵呵,你還想怎么樣?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女的給你按摩滿足不了你啊,要不我帶你去找鴨吧。”
“我對找鴨不感興趣,我覺得自己只能去做雞了。”
“好主意。”
“然后被王強抓獲。”
“哈哈,太刺激了。去做吧。”
我們從美容院出來已經晚上六點了,王強來了電話,讓我去“福鑫酒店”,參加他們局里幾個同事的聚餐。他們幾個每周都要聚一次,輪流做東已成慣例,有時候帶老婆有時候不帶。王強已經兩個月沒帶我去過了,不知道這周是抽哪門子瘋。
王強在“福鑫酒店”的大廳里等著我,我挽起王強的胳膊進了包間。
今天是治安科的老劉請,點了一大桌子的菜。最突出的是一道烤乳豬。烤熟的乳豬睜著眼睛,十分瘆人。
“你們倆不至于吧?”老劉說,“都老夫老妻了,還挽著胳膊?”
“我們就挽了怎么樣嘛?”王強說。
“秀恩愛,死得快!”老劉說。
“早死早托生。”王強說。
我們倆在空座上坐了下來,飯局正式開始。
“嫂子,我敬你一杯。”刑偵科的小鄭朝我端起了酒杯。
“不行,我一會兒得開車送王強。我以茶代酒。”我喝了口茶
“王局,我敬你。”小鄭把酒杯轉向了王強。
“狗屁王局,叫強哥。”王強端起酒杯干了。
“強哥?”治安科的老邢說,“聽上去像黑社會老大。”
“你們跟黑社會有區別嗎?”我看著王強問。
王不強說話。
半個小時之后,每個人都打完了一圈兒,大家都有些高了。
“下個雙休日咱們幾個自駕游去壩上草原玩兒吧。”監所科的老楊說。
“還是去海邊兒吧,”老楊媳婦說,“去草原跟去海邊兒的距離差不多。”
“去海邊干什么?看你露點啊?”老楊說。
“是啊,我新買的比基尼,還沒機會穿。咱們縣連游泳館都沒有。”老楊媳婦說。
“穿給老楊看。”王強說。
“我才不想看。”老楊說。
“還是草原好,去草原吧。”檔案科的老蔣說。
“我喜歡海。”老蔣媳婦說。
桌上熱鬧了起來,女人們一致想去海邊兒,男人們一致想去草原。女人們都比較喜歡浪漫想吹吹海風什么的,男人們普遍喜歡吃想去草原吃烤全羊。
最終還是我們女人妥協了,決定下個雙休日陪男人們去草原。
“嫂子你身材真好,平時健身嗎?”坐在我旁邊的網監科的小林媳婦問我。
“偶爾。”
“在哪里健啊?”
“‘春天俱樂部。”
“哦,我知道,二趟街的那個。你都做什么項目啊?”
“就做瑜伽。”
“哦,聽說瑜伽特別能夠減肥。你看我這肉長的,我也想練瑜伽。”
“可以啊。瑜伽的動作不難學,但堅持下來挺難的,特別疼,所有的筋都需要拉開,全身的經絡都會被打通,想不瘦都難。”
“太好了!我太想減肥了,你看我這一身的肉。”
“唉,你們女的聚在一塊兒沒別的話題,就是減肥減肥減肥。”她老公小林說。
“還不是因為你們男人挑肥撿瘦?”我說。
“我可沒挑肥撿瘦,你看她都胖成什么了!”小林說。
“有本事你把我休了!”小林媳婦對小林說。
“嫂子我真的太想瘦下來了!”小林媳婦轉向我說,“嫂子我能跟你一起去練瑜伽嗎?咱們倆還有伴兒。”
“這個……”我遲疑了一下。王強在桌子底下踹了我一腳。
“沒問題,我下次去叫上你。”我朝她端起了茶杯,“等你瘦下來把小林休了”
“太好了嫂子!就這么定了!”她端起酒杯干了。
“對了老周,上周跳樓的那個案子怎么樣了?”王強問案審科的老周。
“靠,下周結案算了,沒什么可查的。”老周說。
“就查不出一點兒原因?”王強問。
“沒原因,”老周說,“夫妻倆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工,在工地上干活,她留了一封遺書,說是沒有愛情,然后就跳了。她老說平時他們夫妻倆關系很好啊,從沒紅過臉吵過架,跳之前她還給她老公做了一頓她老公愛吃的紅燒帶魚。他老公十分想不明白她為什么跳,沒有任何原因啊。”
“‘沒有愛情難道不是原因嗎?理由還不夠充分嗎?”老周媳婦說。
“‘沒有愛情算什么原因?沒有愛情就要跳樓嗎?我也沒有愛情,我也要跳樓嗎?”老周說。
“你趕緊跳。”老周媳婦說。
“老王,以后有這樣的任務你再也別派我去了。”老周對王強說,“我是第一次看見跳樓的死人,當時就吐了。”
“以后這種任務就都交給你了。”王強說。
“太恐怖了太恐怖了,”老周說,“我要是自殺肯定不用這種死法。”
“那你想怎么死?”我問老周。
“吃藥之類的吧。”老周說。
“跳樓這種死法只是看上去比較恐怖事實上是沒有痛苦的,”我說,“吃藥這種死法看上去比較溫和但實際上非常痛苦。你要么選擇‘恐怖但無痛苦要么選擇‘溫和但痛苦。”
“我選擇‘溫和但痛苦。”老周說。
“我選擇‘恐怖但無痛苦。”我說。
“為什么?”老周問我。
“都已經死了,哪兒還有什么恐怖?”我說
“但是你怎么解釋人有的時候會選擇‘上吊這種‘既恐怖又痛苦的死法呢?”
“可能是想感受一下窒息的快感吧。窒息是有快感的,你們當警察的連這個都不知道嗎?”我開始胡說八道起來,“人在上吊窒息的時候會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強烈快感。人在做愛的時候也會有這種窒息的快感。只不過做愛時的這種快感比起上吊來不知要弱了多少倍。這也就是為什么有很多人在做愛時會在腦袋上套上塑料袋兒。”
“靠,真的嗎?”老周問我,“今天晚上我就往腦袋上套個塑料袋兒。”
“我是不會讓你把塑料袋兒再摘下來的。”老周媳婦說。
酒局一直進行到夜里十一點多,大家作鳥獸散。
我開著車帶著喝高了的王強行駛在空無一人的馬路上。
“她有強迫癥。”我說。
“誰?”王強問。
“跳樓的那個女的。”
“強迫癥?是抑郁癥吧?”
“是強迫癥導致的抑郁癥。得了抑郁癥之后原來的強迫癥并不會消失。”我說。
“強迫癥不是潔癖洗手之類的嗎?她怎么會是強迫癥?”
“強迫癥不僅僅是潔癖洗手之類的,你把強迫癥理解得太表面化了。”
“強迫癥不就是小題大做覺得這個世界隨時隨地充滿了危險嗎?”王強問。
“我真的不確定強迫癥是不是‘小題大做。事情有可能恰恰相反:強迫癥患者的緊張很可能是因為他們看見了世界的真相,他們的緊張才是合情合理的。正常人的‘不小題大做很可能僅僅是麻木愚鈍看不見真相。”
“照你這么說跳樓的那個女的是個看見真相的聰明人,我們都是看不見真相的傻子嘍?”
“你有什么證據證明不是呢?”
“呵呵,那還是看不見真相好,眼不見心不煩。”
“能不能看見是一個問題,‘看見好還是‘看不見好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可能‘能不能看見這個問題更重要。”
“那你為什么覺得那女的有強迫癥呢?”王強問。
“每一個想要‘愛情的人都是強迫癥患者。”
“為什么?”
“強迫癥患者最大的特點就是追求完美,她們不能容忍這個世界有一絲一毫的不完美,而這個世界最大的不完美就是沒有‘意義。‘沒有意義就是這個世界的真相,盡管這個世界看上去充滿了虛假的‘意義。‘愛情雖然不是‘意義,但是它可以假扮成‘意義安撫人類。有了‘愛情我們會瞬間覺得世界充滿了‘意義。強迫癥患者無法容忍這個世界的不完美無法容忍‘意義的缺失,所以她們無法容忍沒有‘愛情。”
“你有強迫癥嗎?”王強問。
“十分嚴重。”
“呵呵,你有什么可‘強迫的?你的生活堪稱完美啊,金錢、事業、愛情,各個方面。”
“可能就是因為太完美了吧。”
“我們多久沒做過了?”
“一年了吧。”
“你愛我嗎?”
“很愛。”我加大了油門兒,伴隨著王強的尖叫聲往高架橋下沖去。
作者簡介:
王芝騰,1981年生,河北師范大學文藝理論碩士,現為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