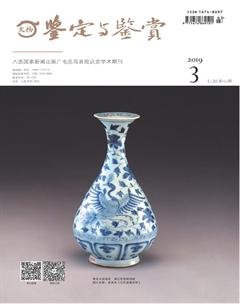中國古代耳飾分類及發展歷程研究
于海燕 王雨嫻 雷威



摘 要:中國古代耳飾作為首飾,首先起到人體美化的功能,表現為妝點妝扮、自我炫示、吸引異性的作用。但在古代,追求美是統治階級或極權階級的特權,所以中國古代耳飾也具有表現社會地位、顯示財富及身份的重要功能。而耳飾有損于身體,作為一種特殊的首飾門類,在中國古代首飾發展歷程中,其興衰及種類的發展是首飾中起伏最大也是最具有特色的。文章從材料材質、加工工藝、地域文化及時代背景等多層次交融重疊中探討耳飾款式及文化的發展與動因。
關鍵詞:中國;穿耳;耳飾;女性;政權
中國耳飾的歷史久遠,種類豐富,主要有玦、耳珰、瑱(充耳)、耳環、耳墜、丁香、耳鉗七大門類。在我國新石器時代的墓葬中,大量出土過質料不同、形狀各異的耳飾。由于新石器時代盛行玉石文化,該時期的耳飾也多與玉石有關,且男女均有佩戴。歷史步入周代后,隨著禮學的發展,中國古人注重保持身體的全形,“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需要穿耳佩戴的耳飾在中原漢族地區呈現衰退現象,耳飾的發展在漢族地區跌入谷底,這種狀況從周代一直延續至盛唐。到了宋、元、明、清時期,世俗地主階層逐漸發展,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導致世俗化的審美被上層社會認可,表現為追求世俗風趣、耽于修飾、注重感官享受的審美趨勢。同時,理學思想的發展成為禁錮女性、壓制女性的道德枷鎖,使男女之別極端化。耳飾作為女性的標志,被社會各階層推崇,女性穿耳之風空前流行。民國時期,穿耳佩戴的耳飾作為舊思想的遺毒,被接受西式教育的新女性抵制,中國各地也開始陸續發布廢止穿耳的禁令,穿耳耳飾越來越少,出現了夾鉗這種耳飾新品種。當今社會,耳飾仍然是女性追求美的重要裝飾品之一,而是否穿耳已經完全成為一種自主的選擇。由此可見,中國古代耳飾的發展與女性社會地位的變遷息息相關。本文以中國古代意識形態的演變為主線,從神權政治、貴族政治及士大夫政治三個階段闡述了從新石器時代至清代,耳飾意蘊、形制、材質、用途的承傳與變化。
1 神權政治——耳飾的繁榮
新石器時代,由于生產力低下,人們無法解釋自然現象,相信人的命運與自然現象緊密關聯,萌生對自然現象的崇拜,因而神權政治盛行。新石器時代,先民將飾品作為與天地通靈的象征,并且堅定地認為玉是可以使人溝通天地神靈的重要媒介之一[1]。因此,佩戴飾品在新石器時代的先民中十分盛行,且多為玉制飾品。新石器時代男女均有穿耳戴耳飾的習俗。此時期的耳飾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是耳珰,先在耳唇上穿大的圓洞,再將腰鼓狀耳飾插入,如江蘇常州圩墩村遺址中滑輪狀的耳珰、大連郭家村遺址中的扣狀陶耳珰和沈陽新樂遺址出土的煤精耳珰(圖1)。第二種是玦,環形帶有缺口的扁圓形玉飾,象征“天圓地方”。玉玦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分布范圍極廣,如遼寧阜新查海遺址、內蒙古興隆洼遺址、杭州河姆渡文化、太湖流域的崧澤文化(圖2)、四川的大溪文化以及東南沿海的史前文化中都有玉玦出土。第三種耳飾多以各種形狀的綠松石及玉制品為耳墜,造型為魚形、錐形、三角形和環形。在西安半坡遺址、遼寧阜新胡頭溝遺址、山東大汶口遺址、江蘇花廳遺址和四川大溪遺址中均有出土,但分布不如耳珰及玉玦普遍。
進入夏商時期,由于中央政權的建立,君王成為古代國家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對自然現象的崇拜逐漸轉化為對君王的崇拜,神權政治出現動搖及衰敗現象[2]。耳飾在夏商初期仍有一定的延續,如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龍形玉玦(圖3)、河北蔚縣夏商文化遺址出土的青銅耳環。商中晚期后,中原地區出土的耳飾較少,而西北少數民族地區仍有耳飾出土,多為金質耳飾,出現了環狀形制的耳飾——耳環,如內蒙古敖漢旗的周家墓葬出土的金耳環、陜西清澗溝寺墓出土的金耳環、北京平谷劉家河商墓出土的金耳環(圖4)等。綜觀此時出土的穿耳人物形象,主要是以神人及奴隸形象為主。神人巫師佩戴耳飾具有一定祭祀意義,而奴隸佩戴耳飾則帶有明顯的懲罰和地位卑賤的標志[3]。由此可見,夏商集權政治取代神權政治后,穿耳成為奴隸和刑罰的標志,因而出現全面衰退現象,尤其在中原漢族中已不再流行。
2 貴族政治——耳飾的衰敗
貴族是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中享有政治、經濟特權的階層,貴族的出現標志著貴族政治的盛行[4]。中國古代的貴族真正出現于周代,到了漢代達到鼎盛,指具有世襲爵位和領地的各級封建主,主要是皇室的宗族子弟和功臣。中國古代貴族一般都追求文化教養,嚴于自律,珍惜榮譽,且具有知性與道德的自主性。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強調以德為先,提倡“以禮制欲”,以個體人格和生命的自由為重,提出“全德全形”為女性美的最高境界。其中“全形”便是指在形體上保特完整,反對雕飾[4],認為穿耳是會破壞身體的“全形”,從而失去了天然美。同時,穿耳帶環被認為“乃賤者之事”,是“蠻夷所為”“不孝”的表現[4]。因此,自周朝開始,經歷漢唐盛世,直至五代,耳飾在漢族人的生活中是極其沒落的。出土的這一時期漢族人物形象資料中,佩戴耳飾的人物形象是非常罕見的。即使有,也多為下層奴仆或少數民族。
在這個禮制至上的貴族政治階段,為了滿足人們對美的追求,同時不違反禮制,周代出現了一種很特別的耳飾,稱為“充耳”,又叫做“瑱”。它是戴冠或者插簪時,以絲線垂在頭兩側,長度正好垂在耳際,以塞住耳朵的玉飾,男女均可佩戴。充耳除了起到裝飾的功能,還具有禮儀的象征,表示人們不該聽的事情不要妄聽。充耳自周至秦漢、魏晉南北朝以及初唐,被上層社會的女性接受,已成為一種制度規定下來。到了明代,冠冕垂充耳仍然沿用,清代由于廢除了冠冕,充耳才退出了政治舞臺[5]。自周代至前唐,中原地區女性的耳飾出土較少,一些少數民族仍喜歡佩戴穿耳耳飾[6],如秦漢西南苗族和傣族佩戴的耳珰(圖5)、漢代匈奴的金絲耳環、南北朝的鮮卑民族的金耳環等。總體上,自秦漢至前唐,與神權有關的耳珰、耳玦逐漸消失,耳飾形制主要為充耳、耳墜和耳環,充耳多為玉石,耳環多為圓形金制,耳墜多為瑪瑙、綠松石、琉璃、玉石等串連而成(圖6)。
3 士大夫政治——耳飾的復蘇
中唐以后,科舉制度成為選拔新官員的途徑。大批來自中小地主階層和農民階層的知識分子通過參加考試參與和掌握各級政權,成為中國士大夫階層,導致原來的貴族政治被士大夫政治取代。士大夫政治在中唐提出,晚唐得到鞏固,宋、元、明、清時期盛行[4]。士大夫來自不同的階層,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眾多人數,其注重世俗生活體驗和官能感受追求的審美追求,也逐漸得到上層社會的認同,取代了過去單一的貴族審美[7]。對于女性的審美趨向柔弱而矯飾,追求世俗風趣,耽于修飾,追求繁縟以顯富貴。耳飾作為美的重要裝飾品重新被人們接受,并進一步發揚光大。
另一方面,科舉可以改變普通階層男人的命運,加上宋代開始推崇的程朱理學導致女性地位沒落,使男女之別走向極端化。程朱理學的興起,不僅在思想上對女性提出約束,如嚴酷的貞節觀;在身體上束縛也增強,如纏足、穿耳。此外,穿耳除了使男女極端化外,還對女性起到警戒的作用。由此可見,穿耳之所以從宋代開始在漢族女性中流行,與科舉及理學的興起導致的女性地位沒落有密切關系。穿耳耳飾自宋代復蘇流行后,再經過與遼、金、元等原本就佩戴耳飾的異族常年征戰、錯居與交流[8],及至明清,在漢族女性中出現了無人不穿耳、無人不戴飾的局面。而且,自宋至明清,各朝代的耳飾與歷史審美的趨勢緊密相連。
宋代女性耳飾整體風格趨向世俗化,形制更為繁縟,題材和圖案都帶有一定美好的寓意[7]。耳飾多為耳釘、耳環和耳墜,基本上以黃金為材質,如江西彭澤宋墓出土的S形金耳環,江蘇無錫宋墓出土的花卉、瓜果造型的金耳環,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葵花形金耳環(圖7)。遼金至元朝,都是以北方少數民族為主體的政權,因而男女都有穿耳佩戴耳環的習慣,造型和圖案上體現了北方少數民族生活的真實寫照[8],如遼寧建平遼墓出土的魚龍形金耳環、鳳形金耳環(圖8),契丹族獨有的U形耳環。除了金、銀材質外,還用玉制作耳飾,如飛天紋飾玉耳飾等。明代的耳飾大多崇尚輕巧,既用耳墜又用耳環,這一時期流行茄子形、葫蘆形和燈籠形的耳環[9]。還有一種珠飾,由一顆或多顆的串珠組成金耳環也很受歡迎,如江蘇揚州明墓中出土的穿珠金耳環。除耳環外,明代的耳墜在耳環的基礎上演變而來,一般上部為圓環,環下綴一組飾品,如明定陵出土的10件精美的耳墜(圖9)。明末清初,耳飾中出現了一種以丁香花為題材、十分小巧的耳飾,稱為“丁香兒”(圖10),十分流行。清代的耳飾制作精美,取材廣泛。無論是滿族還是漢族,戴耳墜的現象十分普遍。佩戴者一般無需取下耳環,只要換掉底下的墜飾即可[10]。墜飾的設計多為一些有趣的形狀,如鳳凰、核桃、葡萄、鳥籠、花朵等。皇宮妃嬪耳飾一般為珍貴的寶石、翡翠、玉石、珍珠、珊瑚等,再飾以金銀,精美絕倫,如清宮廷妃嬪點翠珊瑚米珠壽字耳墜(圖11)、金鑲珍珠翡翠耳環等。清皇宮的滿族女性還有一耳帶三件耳飾的習俗,并且稱環形穿耳洞的耳飾為“耳鉗”(圖12)。民間富裕人家的女性通常用銀、銅制造,外層鎏金,材料雖不如皇宮珍貴,但造型和裝飾手法有獨到之處,如江蘇泰州博物館收藏的花籃形耳飾。此外,明末的“丁香兒”仍是清代女性喜愛的耳飾。
4 結論
總體來看,中國古代耳飾的發展與女性地位是息息相關的。在神權政治下,神和人地位極端化,人的地位遠低于神的地位,所以人需要通過各種途徑展示對神的崇拜,包括傷害身體——穿耳佩戴具有祭祀意義的耳飾。在士大夫政治下,男性和女性的地位極端化,女性地位低微,只能通過繁縟的妝飾吸引男性。此時期,穿耳耳飾作為女性的標志,同時又是精美的裝飾品,被各階層女性接受和推崇。而在貴族政治下,講究禮制思想,對女子的束縛相對來說是比較薄弱的。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把女性的內在美稱為“德”,外在美稱為“色”,提出“重德輕色”,所以這種破壞身體穿耳佩戴的耳飾被擯棄。總之,耳飾首先作為首飾,最本質的功能是對人體的美化和裝飾。但由于社會階層的存在,這種裝飾功能成為統治階層的特權,受到不同朝代統治階層審美觀念的約束。因此,耳飾的發展及演化歷程,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統治階層文化的轉變和興衰。■
參考文獻
[1]葉舒憲.珥蛇與珥玉:玉耳飾起源的神話背景——四重證據法的玉文化發生研究[J].百色學院學報,2012(1):1-10.
[2]陳東杰,李芽.中國原始社會耳飾研究[J].中原文物,2012(2):48-53.
[3]王嶸旭.新石器時期玉玦的造型分類及在耳飾中的運用[J].藝術科技,2017(5):288.
[4]李芽.中國古代耳飾研究[D].上海:上海戲劇學院,2013.
[5]李芽.唐代耳飾研究[J].服飾導刊,2012(1):14-18.
[6]李芽.漢魏時期北方民族耳飾研究[J].南都學壇,2013(4):15-23.
[7]許靜.宋代女性頭飾設計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2013.
[8]黨郁.北方地區耳飾初論及相關問題的探討[D].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2010.
[9]李芽.明代耳飾款式研究[J].服飾導刊,2013(1):13-22.
[10]劉馥凝.清代后妃黃金首飾賞析[J].中國寶石,2002(2):132-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