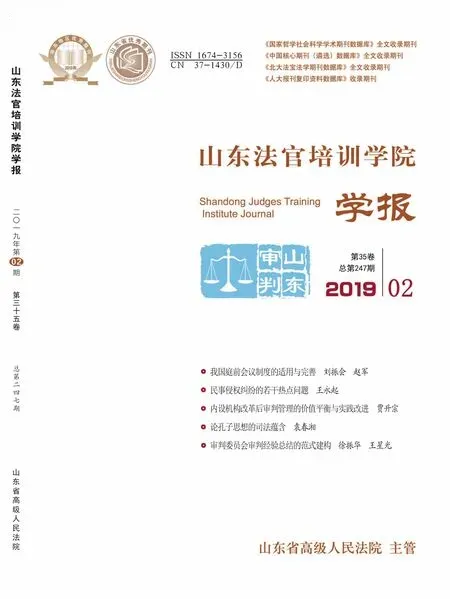事實類型化進路中類案裁判思維的發現和適用
——基于涉以房抵債民間借貸糾紛的樣本分析
王卉 陳蒙 王偉
當前,類案的司法實踐聚焦于類案檢索及其結果處理的程序性規范和常見類型案件的裁判規則總結,①前者如《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實施意見(試行)》、重慶市涪陵區人民法院《關于類案檢索參考的規定(試行)》,后者如北京市三中院關于類型化案件審判指引的研究成果、山東省高院開展類案證明標準研究。是為“類案類判”的外在規制。然而,對法律適用形成內在制約的是法律思維,同質的價值取向、共同的思維范式和技術路徑、知識共識②房文翠、陳雷:《法律適用的內在約束力研究》,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1年第4期。生發出法律統一適用的內在動力和意識自覺。裁判思維蘊含于案件審判。利用司法大數據資源進行類案檢索、比對和分析,在法律規范描述的標準要件事實基礎上,歸納審判實踐中復雜多樣類案事實及司法處斷,探究法官裁判的思維理路,在解構、建構、運用中,法官裁判價值觀、方法、技術交流漸達同質化、個案裁判思路明晰化,從而促進法律適用統一和法官隊伍專業化。本文以涉“以房抵債”民間借貸糾紛③本文所述“以房抵債”如無特殊說明,均指涉“以房抵債”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為樣本,演示類案比對分析的方法步驟,由此歸納同質化的裁判思維并應用于個案中。
一、方法展示:事實類型化主線下法官裁判思維總結的步驟
以促進法官職業思維形成為目的的類案比對分析多因待決案件事實未能找到明確昭示法律意義的規范依據而激發。在要件事實基礎上,歸納司法實踐中由不同裁判事實要素構成的類案事實,在相應事實類型的司法應對中發現法官裁判思維的特點,引導法官在待決類案中的裁判思路。
(一)簡析訴訟爭點——圈定法律規范——確定檢索要素
考察兩案或數案是否屬于“同案”,并不是從程序意義上講的,而是從不同案件中所爭議的問題即訴訟爭點角度而言的。④馮文生:《以房抵債流押禁止規則適用實例解析》,載https://item.btime.com/m_9d465675e63b43862,2018年6月19日訪問。訴訟爭點表述為案件事實能否歸入法律規范的要件事實中,⑤個案爭點可能是多層次的,因上一層次爭點中要件的認定需要依據其他法律規范,即法律適用是多層次的。因此,案件事實是明確訴訟爭點的起點,此亦通常將事實相類案件定義為“類案”的原因,同時,法律規范行為模式涵射的事實具有顯見的法律意義。綜上,應當結合當事人訴辯,大致圈定待決案件相關法律規范,并根據該法律規范要件事實確定檢索關鍵詞。但是:(1)法律規范行為模式多為相對抽象的類型化表述,而類案事實多樣;(2)當事人權利請求或抗辯主張所依據的事實和理由多為對生活事實的描述而未抽象表述為要件事實;(3)裁判文書多未進行生活事實向要件事實的明確歸入;(4)依據經驗和認知確定法律所調整的事項是可能的。因此,類案檢索標簽對事實要素的表述不應過于抽象。此外,由于以總結法官裁判思維為出發點,設定檢索的時間和法院級別等條件不必過于拘泥,以確保樣本的全面和代表性。
(二)分析事實特點——錨定標準事實——豐富事實類型
以法律規范要件事實為基礎,分析類案事實特點,進行事實的類型化建構。①有的要件事實是描述客觀的存在;有的則是主觀評價,但即使是主觀評價也需通過客觀的外在表現出來,類型化過程亦是主觀要件客觀化的過程。盡管以事實的生活化描述作為檢索條件,但在司法過程中,法律利用類型而非概念來描繪案件事實的特征,在努力塑造事件類型時,能夠為司法裁判尋找到適宜的評價標準,②張斌峰、陳西茜:《試論類型化思維及其法律適用價值》,載《政法論壇》2017年第3期。因此,對檢索出的類案進行分析時,應以要件事實作為基礎類別并比對類案樣本中出現的其他能夠影響法律評價的事實情節,對類案事實進行歸納和分類。首先,對樣本案件事實特點進行分析,包括直接歸入要件事實、間接證實要件事實的事實、其他事實。通過數據統計,排除偶發性的、無用的事實要素,固定典型、有裁判價值的事實要素,即以實證歸納而非理論演繹的方法確定“案件事實的價值判斷是否符合法律規則的價值預設”。③黃澤敏:《案件事實的歸屬論證》,載《法學研究》2017年第5期。其次,據法律規范構建標準事實類型,并將樣本案件事實與標準類型事實進行要素比對,以具有裁判價值的事實要素構建符合樣本司法實踐的其他事實類型。此過程實際是在樣本事實、裁判說理和法律規范三者之間往復的基礎上,對要件事實厘定、擴大或限縮的結果。在此建構過程的層面上,包括標準類型的所有事實類型所涵射的事實區分于生活事實、法律事實、要件事實等事實概念,可稱為“裁判相關事實”。④法律事實來源于能夠證明的要件事實,最終涵射于法律,是做出裁判的依據。參見李俊曄:《論要件審判“三段式”思維》,載《法律適用》2017年第23期。但本文研究目的下,事實不應局限于要件事實范疇,應擴展為對裁判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的事實。
(三)分析裁判要素——整合裁判思維——區分類型適用
事實問題及法律問題以不可分解的方式糾結纏繞在一起。⑤陳金釗主編:《司法方法與和諧社會的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頁。歸納裁判思維的過程與事實類型構建同步進行,是一個不能分裂的思維和操作過程。事實類型化過程最直接的產出是裁判規則,即形成類型事實——法律后果的準法律規范,但類案裁判統一性受質疑和成文法背景下,適用前案裁判規則欠缺實質合理性和形式合法性。而從裁判的主觀活動層面,法官并非以創設裁判規則而獲得裁判結論,而是以思維直接導出裁判結果。法官的價值追求、邏輯思維、解釋法律、論證結論的能力直接決定類案法律適用的過程和結果。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司法改革背景下加強人民法院法律統一適用機制建設的調查研究》,載《人民司法·應用》2018年第13期。思維之運用亦不似規則適用受條框制約,更關鍵的是抽象的價值、方法反而更具穩定性、更易同質化。因此,類型事實——裁判思維的研究現實意義明顯。在具體的裁判文書中看不到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之間存在何種關聯,⑦傅郁林:《民事裁判思維與方法——一宗涉及外國法查明的判決解析》,載《政法論壇》2017年第5期。因此,應對各事實類型對應樣本案例的當事人訴辯、認定事實、裁判理由、裁判結果等要素進行提煉;與此同時,在法律方法指引下,運用移情和換位進入司法者的思維世界,并比對自身同等情形下的裁判思路,方能與司法者建立有效溝通,最終整合歸納類案裁判思維:運用整體性和層次性思維,將樣本案例作為整體,分析法官裁判思維整體表現;從理念、思路和方法等層層剝開法官裁判思維的內核。區分事實類型,探究不同類型下裁判思維的具體適用,從而為待決案件的裁判提供可操作性指引。
二、樣本解析:以房抵債類案事實類型構建及裁判思路比對
對以房抵債行為性質的理論界定難以涵蓋豐富的案件事實,且民事主體總是嘗試突破法律規范行為模式。因此,跳出理論窠臼,利用前述方法將該類糾紛事實類型化并總結法官裁判思維具有相當的實踐價值。
(一)以房抵債樣本檢索及基本情況分析
以房抵債糾紛中,一方或雙方以房抵債的主張是否符合《物權法》第186條、擔保法第40條作為爭點之一。《物權法》第186條要件事實為“債務履行期屆滿前;抵押權人和抵押人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抵押財產歸債權人所有”,但檢索時以“以房抵債”這種相對生活化的事實表述即可。基于此,樣本檢索以“民間借貸糾紛”案由——“判決書”為選擇項,在“本院認為”中以“以房抵債”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進行檢索;為體現類案裁判的最新思路,將生效時間確定為2018年,截至6月13日,符合上述檢索條件的生效判決書共計106份,其中,高院1份、中院35份、基層法院70份;一審72份、二審32份、再審2份。
(二)樣本裁判相關事實要素分布統計和裁判相關性分析
從當事人訴辯看,樣本案例中關于以房抵債行為效力認定的法律規范基礎除前述《物權法》第186條、《擔保法》第40條——效力限制性規定,還有權利實現條件和程序規定即效力認可的直接法律規定——《物權法》第195條。①該法律規范要件事實多出現在擔保合同糾紛、實現擔保物權特別程序等案件中,樣本中數量極少。上述法律規范要件事實直接指向如下要素:達成以房抵債合意;達成合意時間;合意的具體內容主要是抵債方式的約定。通過數據分析提煉出其他裁判相關事實要素:房屋性質和權屬狀況、當事人庭審中對以房抵債合意的認可等。
1.關于以房抵債合意形式。在樣本中,當事人簽訂《住房抵債協議》(或以房抵債協議書、以房抵付借款協議書等)的有42件;簽訂(包括與第三人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或房屋買賣協議)的有19件;在借款協議中約定將房屋抵押(包括約定到期不能履行債務轉移房屋所有權)的有7件;通過《投資協議》、口頭約定、承諾書、收條等其他方式實現的20件;無協議或未達成合意的18件。可見,以房抵債合意形式多樣,在進行事實歸入時應結合當事人行為目的和法律規范之價值目標對合意形式進行實質審查,判斷是否屬于以房抵債協議。
2.關于合意達成時間及以房抵債履行方式的約定。樣本中,有72件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后達成合意,有8件在借款協議中同時約定。從合意內容看,有75件約定以房產轉讓償還欠款,有26件約定將抵押的房產作價一定數額抵償給債權人,有5件約定“用房產證抵押,到期不履行債務歸債權人所有”。履行方式具體約定盡管不同,從法律評價上可分為轉移房屋所有權和折價償還借款兩類。
3.其他裁判相關事實。樣本中,各方均認可以房抵債協議的有79件,各方就是否存在合意有爭議的有23件。從房屋性質和權屬狀況看,因房屋性質影響以房抵債協議效力的有16件,涉及土地性質為宅基地、房屋為小產權房;因房屋不符合預售條件、未實際交付、房屋被查封等致使協議無效或不能履行的有21件。從裁判說理看,房屋性質、權屬、交付等事實成為裁判相關事實要素,主要因其“影響要件事實認定”和“成為價值衡量因子”。
(三)以房抵債事實類型構建及各類型案件裁判思路比對
據《物權法》第186條等基礎法律規范并結合上述厘定的裁判相關事實要素,對樣本中出現的裁判相關事實進行提煉,可構建以下事實類型:完全歸入《物權法》第186條等法律規范要件事實的標準事實類型、實踐中存在由裁判相關事實要素組合構成的其他非標準類型(見表1)。

表1:以房抵債事實類型構建
在樣本各事實類型案件中選取典型案例,全面、深入分析典型案例的裁判文書,沿著當事人訴辯、事實認定、裁判理由、裁判結果的路線,探究、重現法官在個案裁判中的思考,架構起每個事實類型和思維之間的橋梁——盡管對各類型案例分析最直接的產出是裁判規則,但規則作為一種結論性命題無法為思維的發現提供充足供給,且規則并非思維發現的必經之路,思維可從案例裁判要素的分析中直接獲得。架構的過程不僅應對某事實類型案例進行橫向分析,更應著眼以宏觀和比較的視角發現案件裁判要素的異同(見表2)。

表2:以房抵債事實類型對應樣本案例裁判分析

類型 對應表1序號 案件 訴訟請求 答辯意見 認定事實 裁判理由 裁判結果其他類型(非標準類型)Ⅱ-3牛某與李某、許某民間借貸糾紛案(2018)魯1728民 初83號償還借款,在事實與理由中提出存在以房抵債合意的事實未答辯借款到期后,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兩份,約定李某將閣樓和車庫分別以15萬元、15萬元的價格出售給原告牛某。原告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兩份實際是以房抵債的協議,抵頂借款30萬元該房屋買賣合同的效力不屬于法院審查的范圍償還借款Ⅱ-4王某、周某民間借貸糾紛案(2018)浙 02民終146號原借貸關系終止,雙方建立了房屋買賣關系雙方借款關系合法有效,房屋買賣合同未簽訂債務履行期屆滿后,雙方簽訂《房屋抵押欠款轉讓協議》約定以房抵債方式變更原有的借貸關系。簽訂協議時尚未取得涉案房產所有權,房屋轉讓折抵欠款協議條件尚未成就因債務已屆清償期,而債務人未按約履行房產交付義務,以房抵債協議未實際履行,原債務關系亦未消滅歸還借款本息Ⅱ-5杜某與劉某、李某民間借貸糾紛案(2018)皖12民終526號償還借款及利息并非以房抵債,只是購買房屋的意思表示劉某用四套樓房折抵欠杜某的借款,簽訂房屋買賣協議未實際收到四套房屋以房抵債的協議未實際履行繼續履行還款義務Ⅱ-6侯某與吳某民間借貸糾紛案(2017) 蘇0302民初2748號償還借款,不接受以房抵債以房抵債,不欠借款債務到期不能還款,吳某將二套小產權房抵給侯某,并將房票、購房發票交給侯某房子系小產權房,無法辦理房證,且原告亦表示不接受以房抵債債務人以房抵債的主張不成立Ⅱ-7薛某與趙某民間借貸糾紛案(2017)蘇 03民終1596號不是借款人,不應償還借款 借款事實屬實借款到期后,薛某、趙某及凌某達成約定,以凌某所建房屋抵償債務,因用抵債的房屋為小產權房,無法辦理產權登記手續不產生物權變動的效果,債務人主張涉案債務以房抵償完畢的主張不成立繼續償還借款,對于以房抵債協議,可另行予以解決
對案例分析可見,標準事實類型下盡管當事人訴辯不同,但均直接以違反“流押禁止”規則認定以房抵債協議無效;非標準事實類型下不同事實類型案件的裁判中,大多未直接認定以房抵債協議效力、理由亦多樣化。比對所有事實類型案件,不論事實要素相似抑或明顯相異,裁判理由和結果均有異有同。從比對中以房抵債類案裁判思維得以發現和歸納。
三、總結歸納:不同事實類型下法官裁判思維的辨析
對樣本案例的整體分析發現,以房抵債類案裁判思維契合民事裁判思維共性,亦蘊含著在對基礎法律關系——民間借貸法律關系獨特價值判斷基礎上的特點。故此,裁判思維可作為包括以房抵債類案在內的各類民事案件的思維指引,但應區分限定適用于樣本類案的個性之處。
(一)兩種進路:法官裁判之理念、思路、論證和方法的實踐表現
關于裁判思維,立于不同立場有不同界定:能動主義和克制主義之分;三段論法和證明責任法之分;涵射思維、類型思維和反省思維之分;推論模式和等置模式之分,等等。但上述界定僅涉及思維的某一方面或角度,而思維是多條線縱橫貫通的復雜主觀活動,主要是裁判理念、思路、論證、方法在一個思維過程中融洽運用。不論何種角度界定,主要可歸于形式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思維模式。
裁判理念上,形式主義多謙抑之姿、現實主義則顯積極之態。謙抑是司法“消極的美德”,裁判應尊重法律和立法原意;積極的裁判在個案審判中不囿于文義。裁判思路上,形式主義采推論模式:形式的法律邏輯——演繹三段論推論和類比推論;①類比推論是個案事實超出了準用規則可能的文義射程,但基于規則之后的政策、原則、目的,認為可以將個案事實涵射進來。參見陳林林:《裁判的進路與方法——司法論證理論導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117頁。由此看來,盡管邏輯思路上類比推論最終符合形式邏輯的外觀,但具體適用中有實質因素的考量。現實主義采等置模式:將事實一般化、將規范具體化,將事實與規范不斷拉攏、靠近。②鄭永流:《法律判斷形成的模式》,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裁判論證上,形式主義使用三段論法、證明責任法——證明責任方法不僅在程序上推進訴訟,實際上形成新的三段論,即“證明責任分配規則”為大前提,“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為小前提的方法;③胡學軍:《論證明責任作為民事裁判的基本方法——兼就“人狗貓大戰”案裁判與楊立新教授商榷》,載《政法論壇》2017年第3期。現實主義的論證方法是利益衡量法,即獲得案件事實后,結合個案事實,對案件所涉各種利益——各方當事人的具體利益和法律規范所涉之價值——進行審查和衡量,作出支持哪一方訴求和何種利益的實質判斷。裁判方法上,形式主義采請求權方法——處理以請求權關系為內容的實例應以請求權基礎(請求權規范基礎)為出發點和歷史方法;④參見王澤鑒:《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頁。現實主義則傾向受民法理論啟發。
司法者裁判案件大致沿循一類一般思維模式,因為思維總是有始有終,但未必是機械化的流水作業、線性直向發展,而是視事實與規范之間的不同關系,在這二者之間往返。⑤鄭永流:《法律判斷形成的模式》,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以房抵債類案裁判思維模式符合上述判斷,即整體上采一種一般思維模式,但根據事實類型有所區分。
(二)所有事實類型:裁判思維整體上秉持衡平之價值取向
從樣本類案整體分析,類案裁判說理的外觀多體現了形式主義的思維進路;對以房抵債協議效力認定及基礎法律關系處理的深層檢視則顯示對該類案件所涉債權人、抵押權人、債務人具體利益以及經濟秩序、社會誠信等社會利益的衡量,以此實現裁判形式合法性和實質正義。因此,總體上看法官裁判秉持相對一致的裁判價值——衡平:始終是在嚴格規則與自由裁量之間來回擺動,在據法司法和不據法司法之間不斷循環往復。①[美]羅斯科·龐德:《法律史解釋》,曹玉堂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衡平②此處衡平并非能夠量化的平均主義,而是根據案件具體情形達成一種協調。例如,根據案件事實,單獨運用嚴格規則主義的裁判進路亦為衡平,因為此時運用嚴格規則可達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表現為:對以房抵債類案的裁判達致兩種進路之平衡,在每一事實類型類案裁判上亦體現衡平基礎上的選擇;在類案整體及個案具體裁判中采用三段論論證,同時沿著據利益衡量找法適法的邏輯;事實類型相似的案件出現不同裁判思路或結果,如前述葉某與魏某、泗某、某房地產公司案和牛某與李某、許某案事實要素均有:約定以房屋作價抵頂債務,葉某案在債務履行期屆滿之前訂立協議而牛某案則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后訂立,牛某案距離“流押禁止”的標準要件事實更遠,但是法院認可葉某案中以房抵債效力但對牛某案則不予審查協議效力,其中體現一種適法技術的衡平。裁判思維模式的衡平運用并非完全依靠直覺,而是一定經驗、知識并經反思后作出法律判斷,由此,影響法律判斷的規范、社會、傳統等各種要素實現協調。
(三)標準事實類型:形式主義為主兼具現實主義的進路
在標準事實類型的樣本案例中,形式主義是主要裁判思維模式。因為標準事實類型是根據請求權基礎法律規范獲得,其事實要素與法律規范要件事實一致。在這一事實類型案件中法官裁判思維具體過程是:運用請求權方法分析當事人訴辯主張及相關證據初步得出案件事實高度符合標準事實類型的結論后,法官即形成謹慎之謙抑理念引導思維進展;繼續沿著請求權方法并輔歷史方法、運用證明規則及經驗法則等方法形成裁判事實,與之幾乎同步進行的是依據法律規范的文義和立法解釋;在裁判說理時運用三段論方法或者證明責任方法進行涵射型論證,得出裁判結論。簡言之,整個過程是在三段論邏輯框架下,以請求權方法為線展開。以樣本中符合標準事實類型的于某與苗某、徐某案為例,探析法官對以房抵債協議效力認定的思維:債務人苗某借款當日出具的借款協議中約定“借期為45天,以住宅樓一棟作為抵押。如借款到期不還,則該房屋無償歸于某所有”,苗某認可簽訂協議的事實,因此確定以房抵債協議效力認定的請求權基礎規范為《擔保法》第19條,本案事實“債務履行期屆滿之前、以房屋作為抵押借款到期不還則該房屋歸債權人(抵押權人)所有”與《擔保法》第19條的要件事實一致,應適用形式主義裁判思維;由于雙方當事人對借款及曾約定以房抵債的事實均認可,相關證據充分,前述認定事實進一步予以確認為裁判事實,同時明確《擔保法》第19條是對流押行為的禁止。裁判說理中運用三段論推理:大前提——《擔保法》第19條,小前提——裁判事實,結論——借款協議中關于以房抵債的約定違反法律的規定。
在某些情形下,案件事實完全符合某一法律規范之下標準事實類型,但嚴格適用形式主義將導致機械司法而引發道德和倫理風險——如瀘州張學英訴蔣倫芳遺產糾紛案,此時,采用形式主義裁判思維應增加一步:對裁判結果進行合理性、正當性檢視,如若不妥,則應恰當修正、調整思維模式,兼采乃至主采現實主義思維路徑。
上述思維對于標準事實類型的其他類型民事案件同樣適用。
(四)非標準事實類型:多種考量因素下形成混合型思維
審視樣本類案非標準事實類型案例的裁判,并未發現明顯的、區分性的標志性思維模式。即符合前文所述,裁判外觀顯示形式主義思路;內里則是形式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綜合運用,原因在于:法律形式主義是“在法制發展到較為成熟而未達至臻階段的認識”①胡銘、王霞:《法官裁判思維中的法律形式主義與法律現實主義》,載《浙江學刊》2015年第4期。與當下法治環境相近,且向公眾展示了依法審判。但當裁判事實要素無法恰當地歸入某一法律規范時或者即使能夠通過法律解釋歸入要件事實,但如簡單形式化裁判違背立法之本意或法官自身亦猶疑不決,則采積極思維、適用等置模式、探究規范目的、運用利益衡量、借助民法理論得出結論并進行論證。
前述可知,非標準事實類型類案裁判主要區分為以下情形:(1)案件相關事實要素能夠歸入其他法律規范——該法律規范能夠對請求權基礎法律規范形成補充,則一個裁判過程實際兩次采形式主義思維;(2)盡管并不符合標準事實類型,但裁判事實要素是認定要件事實的間接事實,實質上該類型與標準類型相同、是標準類型的具化,此時亦應以形式主義思維為主,例如,前述戚某與李某、金某案中法院認定《房屋轉讓協議》實為借款提供擔保,實際適用“流押禁止”規則認定債權人不享有直接取得房屋所有權的權利;(3)與要件事實比較發現缺少關鍵事實,或者在要件事實之外有影響裁判的關鍵要素,應積極的檢索法律規范和民法理論,考量不同裁判結果的社會效果及其與債法價值取向之關系——基于合同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中,保護債權是基本立足點,②司偉:《債務清償期屆滿后的以物抵債糾紛裁判若干疑難問題思考》,載《法律適用》2017年第17期。同時應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并兼顧債務人權利。在經衡量得出結論后,還應根據案件事實回到法律規范中尋找論證的根據。如前述王某、周某案,對債務履行期屆滿后雙方簽訂以房抵債協議的認定,法院認為“二人通過建立新的債權債務關系取代原來的借貸法律關系。但案涉兩份協議只是改變了原債務的履行方式,增加債權實現的途徑與可能而非對原有借貸關系的否定”,實際是參考債務清償期屆滿后以物抵債是“債之更改”抑或“新債清償”的民法學探討。
非標準事實類型的其他民事案件亦多用混合思維,但在立法目的、利益衡量的具體判斷上與樣本類案有所區分。
上述分析可知,裁判思維的形式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模式是對立統一的,因為實質判斷仍需立足于法律規則并尊重法律規則。
四、個案驗證:法官裁判思維在具體案件中的應變適用
類案裁判思維只有引導個案裁判正義方能實現類案研究目的。事實類型建構是建立在不完全歸納基礎上,待決案件事實可能無法完全歸入已建構的事實類型中,但裁判思維進路異曲同工。下面在劉某與趙某某民間借貸糾紛案中驗證法官裁判思維。
【案情簡介】
2014年9月17日,劉某作為買受人,趙某、張某作為出賣人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一份,約定將坐落于A區一套房屋以446200元出賣給劉某,同日,趙某、張某出具收到條一份,載明:“今收到現金肆拾肆萬陸仟貳佰元正。”涉案房屋現由趙某、張某占有使用。劉某訴稱要求趙某、張某協助其辦理涉案房屋的過戶手續。趙某、張某辯稱,該房屋買賣合同不是其真實意思表示,簽訂合同是為趙某某從劉某處借款提供擔保,且未收到購房款。趙某某述稱,其與劉某系朋友關系,系案外人王某與劉某借貸關系中擔保人,后因其向劉某借款8萬元,劉某要求其為上述擔保及借貸關系的提供擔保,遂將其父母趙某、張某名下的涉案房屋以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形式提供了擔保。
【案件解析】
本案的訴爭焦點問題是趙某、張某與劉某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是否為趙某某的債務提供的擔保。本案雖系因房屋買賣合同引起的糾紛,但實系民間借貸糾紛,據庭審雙方當事人認可的事實及查明的事實,本案的主要事實要素有:
要素1:借款未約定履行期限;
要素2:在借款同日,雙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
要素3:房屋買賣合同行為系為借款行為提供擔保;
要素4:涉案房屋未實際交付。
從上述事實看,該案符合以房抵債構成非典型擔保的事實類型,但與樣本案例戚某與李某、金某等民間借貸糾紛案事實要素并不完全相同,但可通過等置模式,將該案件事實要素靠近非典型擔保的事實要素,以此作出裁決結果。
從裁判理念、思路上看,《擔保法》第40條確定的行為模式要求有,一是雙方之間有抵押約定;二是債務履行期屆滿抵押權人未受清償時;三是抵押物的所有權轉移為債權人所有。該案中,房屋買賣合同系為債務擔保而存在,因未約定明確的債務履行期限,其不符合《擔保法》規范中確定的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只有在劉某應要求趙某某履行,趙某某無力償還時才能要求實現,現劉某直接主張涉案房屋的所有權,有悖于《擔保法》第40條的規定。另,涉案房屋系趙某、張某的唯一住宅,若將房屋所有權轉移,趙某、張某將無處居住,且趙某、張某年邁,若強行執行,對老年人的權益將有所損害,亦應考量裁判結果的社會效果,即在利益衡量中應先保障基本生存權益。從裁判論證方法上看,運用三段論邏輯,查明的事實符合《擔保法》第40條中關于禁止流押規定構成要件,故不應支持劉某的訴訟請求。證明責任法則是查明小前提以適用三段論的方法之一。本案中,庭審期間,劉某就支付房款的方式前后陳述矛盾,且未提交有關證據予以證實購買房款實際支付的金額及支付方式等,故無法確認該房屋買賣合同簽訂系趙某、張某真實意思表示。從裁判思路上看,如果劉某的請求權系將涉案房屋折價、變賣等實現擔保物權,在不進行利益衡量的情形下,可能得出不同的裁判結果。但劉某訴請協助辦理房屋過戶,則根據查明的事實,一是房屋買賣關系不成立;二是劉某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違反法律的效力性強制行規定;三是經利益衡量,則最終將駁回劉某的訴訟請求。
上述驗證案例裁判中整體上采衡平思維,在形式主義和現實主義邏輯、方法的融貫運用中,亦展現出對不同事實要素的靈活處理。
結 語
從事實切入探究裁判形成是合乎司法立場的邏輯進路。從案件事實到裁判思維的關鍵連接點仍是法律規范,規范是思維歸納的出發點和歸宿,思維的過程中法律被解釋、規范所涵射的事實類型得以明確,由此司法者在汲取類案裁判智慧的同時,對裁判方法進行反思和完善。因此,以思維為研究對象是促進法律統一適用的更根本和深層次的路徑選擇。由于立法對不同法律關系規范的目的和價值取向不同,因此,民事法官裁判思維的養成還應結合待決案件審理開展全面實證研究。盡管樣本限定以房抵債事實于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之中,但是突破案由的制約對事實進行類型化界定能夠拓寬思維研究的廣度,亦未超越類案研究之范疇;裁判思維的研究還應根據民事案件流程擴展到立案、庭前證據交換、庭審等階段,對審判各環節提供全面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