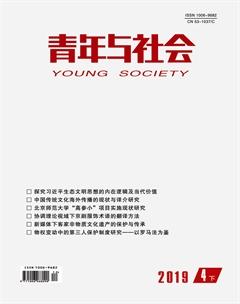論述改革開放后農民主體的演變歷程
摘 要:改革開放后,在國家現代化和城鎮化的影響下,農民主體的演變歷程也就表示為:從傳統農民到第一代農民工再到新生代農民工。而在每一次演變中,農民主體表現出不同的心酸與喜悅,對此國家也出臺相應的對策來解決農民主體所面臨的困境。同時,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民市民化將是農民未來的發展趨勢,而這一過程將是漫長且具有挑戰性的。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期待農民市民化的實現以及國家的富強。
關鍵詞:改革開放后;農民主體;農民工;農民市民化
改革開放后,隨著國家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一大批農民從傳統農業中轉移和分離出來,同時也與傳統農民表現出很大不同特點。因嚴格的戶籍制度,他們仍然是農民身份。而在這個過程中,農民主體也相應發生演變:傳統農民→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
雖然這三種農民類型可能還會并存一段時期,但新生代農民工將是研究“三農”問題專家日后關注的重點對象。故對改革開放后農民主體的演變歷程進行論述,在歷史梳理中把握時代命脈,發現新的時代特征從而推測未來農民主體走向,為城鄉的協調發展作出一種參考價值。
一、第一代農民工:走出鄉土,又回到故鄉
20世紀80年代初,在農村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從集體經營體制中解放出來從而自由生產。緊接著鄉鎮企業的興起,有一批農民開始“離土不離鄉”,鄉村社會正在流動。90年代隨著糧食統購統銷的改革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推行,“市場社會”悄然興起,鄉村進入“大流動”時代,大批農民涌入城市“闖市場”。這就形成“民工潮”現象,第一代農民工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因此,在國家現代化和市場化影響下,農民的“鄉土本色”逐漸消失,村莊與外部世界開始有聯系。若傳統農民是靠種地謀生,與泥土分不開,正如費孝通所說的“直接靠農業謀生的人是粘著在土地上的”,“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而第一代農民工就表現為走出鄉土,進城務工,在城鄉之間來回遷移。當農民從進城務工中獲得比在村種田更高的收益時,這種來回遷移也就形成常態。而對農民大規模涌入城市這種現象進行原因分析,我們還可以體會到農民的心酸與喜悅。首先,與城市建設一片欣欣向榮相比,農村大多顯得落寞與衰敗。其次,加上傳統農業低收入高成本,這種利益權衡是農民進城最大的動力。還有,當種地還要交稅時,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卻仍然只混個溫飽,這不得不使人感到“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陰影時刻籠罩在農民心中。而反觀進城務工:一是擁有較高的收入,雖然工作不穩定;二是擁有較多的就業機會,只要肯吃苦就有事做;三是潮流趨勢,進城務工有面子。這也就形成一種人口遷移推拉理論,即鄉村在向外推,城市在向內拉,農民自然就吸引到城市來。
然而,第一代農民工進城后,他們生存狀況怎么樣?第一,身份歧視,因臟貧窮受教育低,受到城市居民不待見;第二,嚴重的異鄉漂泊感,雖身在城市卻永遠是異鄉人;第三,生存艱辛,在城市辛苦勞作住很差的房。對此,詩人左河水在《鷓鴣天·農民建筑工》中寫道:“萬道磚墻砌楚幸,幾多惆悵度黃昏。異鄉校外兒八歲,留守田間父六旬。城鎮化,筑功勛,險臟不懼懼求薪。醫療社保無承保,緣是鄉籍農戶身。”這首詞生動形象地道出了那個時代農民工在城市勞動、生活的辛酸。當他們大量涌入城市后,對鄉村造成極大影響:整個村落只留下老人、兒童和少量農業兼副業的勞動力,村莊顯得空蕩蕩的,這樣鄉村就成為“空巢社會”。從而導致農田荒蕪、留守兒童教育、老人養老等鄉村問題大量出現。
對此,當第一代農民工走出鄉土,不管如何艱苦奮斗,由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這條鴻溝橫亙在面前,農民工很難被城市所容納,他們微薄的收入也很難在城市里進行消費。因此,雖然被城市繁華所吸引,他們卻永遠是異鄉人。于是他們逐漸明白:“城市,只是自己討生活的地方,不能指望它們給你留下真正的生存空間。他們變得本分、安分、守成了,他們認同自己的命運,不再抱怨。”如果賺有大量錢財時,他們會選擇回村莊蓋房子,因為那才是他們的家。梁鴻曾對第一代農民工進行大量采訪,其中一位農民工的回答很有代表性:“在這兒(指城市)奔波這些年,也夠了。你看著,只要是做生意的,都在老家弄有房子,主要咱這打工還不是穩定工作,說走就走了。對西安(打工的城市)沒感情,一回去就心里美……住到城市有啥用意?沒有三朋四友,空氣也不好。它請我住在這兒我也不住這兒”,“(進城掙錢)就想著在家蓋個房子弄得美美哩,將來回家住。”然而第一代農民工在家鄉蓋起新房子,自己沒有享受幾天就外出打工,如“村莊里的新房越來越多,一把把鎖無一例外地生著銹。”等自己老了回到故鄉,突然發現房子也衰敗了,這是一種怎樣矛盾的心情。
面對上述農民工生活艱苦以及農村衰敗等問題,從2006年起,國家開始實行農稅免收和新農村建設,國家與農民的關系開始“從索取型關系轉變為普惠型和扶持型的關系。”同時國家對“三農”進行大力扶持和出臺各種優惠政策,但鄉村形成“空巢社會”、身份歧視、農民工待遇等這些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總之,第一代農民工的主要特征:走出鄉土,又回到故鄉。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的興起,新的時期又出現新的問題。
二、新生代農民工:進不去的城,不想回的鄉
“新生代農民工”指的是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新一代農民工,2010年1月31日首次在中央一號文件中被正式提出,從此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逐漸受到國家與相關研究者重視。
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7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8625萬人,而新生代農民工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為50.5%,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而老一代農民工僅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49.5%。因此,2017年新生代農民工占比首次過半,隨著老一輩的農民工即第一代農民工逐漸老去,新生代農民工毫無疑問會成為新的農民主體登上歷史舞臺。
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輩農民工不僅僅只是年齡上區別,其實更本質的區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表現出新的時代特點:(1)基本不懂農業生產,純粹從事二三產業,即主要從事工業、服務業。僅據2009年統計,上一代農民工除外出從業之外,還從事了農業生產活動的比例為29.5%;而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僅為10%。換句話說,在2009年,有90%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一天的農業生產活動。如果說上一輩農民工還“亦工亦農”的話,新生代農民工就真的“名存實亡”,成為不種地的農民。(2)文化素質整體較高。也據2009年數據分析,從平均受教育年限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8年,而上一代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8.8年。隨著國家九年義務教育的全面普及和普通高等院校的不斷擴招,農民工的學歷自然會越來越高。(3)對鄉村缺少認同感。自從改革開放后,農村就表現出“缺乏分層與缺失記憶”的情景,即鄉村精英大量流失,鄉村傳統習俗被遺忘,村民之間的聯系變弱,這就導致村民對村莊的認同感逐漸消失。隨著新生代農民工成長成才,那種“鯉魚躍龍門”的心情更急迫,鄉村精英更是流失嚴重,新一代農民工對農村的認同感更是嚴重缺失。一位典型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絕對不會在村里,也不想在縣城,肯定也不會在北京。極有的可能是,將來結婚,把孩子留給家里的父母,兩個人繼續在不同的城市打工。”由此可見,新生代農民工寧愿在城市間到處漂泊,也不愿回到農村。(4)對“農民”身份的排斥。他們見過父輩農民的辛苦和所受到的社會歧視,因此,他們對“農民”身份特別敏感,不愿被叫成“農民”。如有人表示:“它確實有一種歧視。‘農民從來不是個好詞。咱們小時候,爹媽讓上學,不就是想讓你脫離農村,不當農民嗎?為啥,農民可憐,過不上好日子,農民被歧視……現在,農民進城的多了,農民和城市直接相遇,那差別就出來了。……農村負擔大,農村人不講衛生、不講個人權利,其實都是對應大家心里對‘農民的負面判斷。”(5)渴望城市生活。城市生活條件便利,有更多就業機會,并且自己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等與城市居民毫無差別,同時對鄉村是越來越陌生的狀態,由于這些原因綜合作用勢必導致新生代農民工渴望進入城市,渴望城市生活。如詩人左河水在《鷓鴣天·打工妹》這首詞中生動形象地描述道:“村妹不甘種稻麻,滿懷志智闖天涯。繡衣出口顯身手,四海街頭飄彩霞。歐美澳,亞非拉,品牌名起客商夸。時時領創推新品,歲歲登臺戴大花。”
然而,對第一代農民工而言,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雖然有過掙扎,但最后還是安于本分,老了還是回到故鄉。而新生代農民工強烈渴望改變自己的命運,對農村是排斥的,對農民身份是抗議的。同時,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與自己的低收入、嚴格的戶籍制度、冷漠的社會歧視等種種無形有形的門檻不斷粉碎著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夢。于是,他們便處于一個尷尬的境地,渴望進入城市又被城市制度性排斥在外,戶籍在農村卻對農村缺少認同,這樣他們處于“雙重邊緣化”困境,即進不去的城,不想回的鄉。一位新生代農民工對此深有體會,說道:“干農民的活,你干不了;往高的,你也干不了。我們這種人,是吊在半空上的,上不去,機會很少;下不來,不愿放下身段。”這種“吊在半空上的,上不去,下不來”的感受,可見新生代農民工內心痛苦的掙扎。
面對上述新生代農民工出現的困難,國家也制定相關政策,使新生代農民工既進去了城又可回到故鄉。如2014年7月30日,國務院正式公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逐漸解放戶籍桎梏、取消二元戶籍制,這對農民工定居城市創造條件。同時,國家進行新城鎮化建設,即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和諧發展。如2014年3月份,《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正式發布。還有“三農”問題和鄉村建設一直是國家關注的重點,故國家在2015年5月27日發布了《美麗鄉村建設指南》,把鄉村建設思想提到一個新的時代高度,努力把鄉村建設成為更美麗更適人宜居的地方。
總之,隨著國家的戶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鎮化的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似乎是個必然趨勢,但目前新生代農民工“進不去的城,不想回的鄉”的困境還將持續一段時期。
三、未來的走向:農民市民化
城鎮化,一般指隨著國家現代化發展,其社會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型社會向第二、第三產業為主的現代城市型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也即農村人口逐漸轉換為城鎮人口的過程。而對改革開放后農民主體的演變歷程進行梳理,農民的市民化將是未來不可阻擋的趨勢。
根據2011年國家統計局統計,全國大陸總人口為134735萬人,其中城鎮人口為69079萬人,占總人口比重首次超過50%,達到51.3%。而2017年統計,全國大陸總人口139008萬人,比上年末增加737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8134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即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是逐年上升的。另一方面,與城鎮化快速發展相比,農村正在迅速衰亡。如“2002年前,中國有360萬個自然村,到2012年,已銳減為270萬個,十年里有90萬個村落消失了,平均每天有240個自然村消亡,而這其中就包含眾多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的古村落”。還有對國家三大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行統計,得出如下表所示:
第三產業 46.7 47.8 50.2 51.6 51.6
一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發展主要靠第二、第三產業支撐,雖然農業是基礎,但農業所占份額卻是最低的。對上表的數據進行分析,第一、第二產業比重有下降趨勢,第三產業是穩定持續上升。對此,中國未來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將會越來越少,農業生產趨向飽和,更多勞動人口從事于第二、第三產業。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后,國民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中國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也說明中國逐漸從農業大國中走出來。
由于國家城鎮化迅速推進,農村的大量衰亡,務農人數大量減少,農民的市民化將是一種必然趨勢。對此,國家鼓勵農民市民化并對它表示極大的重視,如2016年8月5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財政政策的通知》,其中強調道:“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首要任務,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途徑,是擴內需、調結構的重要抓手。”其實,國家還強調:“要進一步調整戶口遷移政策,統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到2020年,基本建立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有效支撐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依法保障公民權利,以人為本、科學高效、規范有序的新型戶籍制度,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如果戶籍制度改革成功,這將對城市化發展、農民的市民化有極大推進作用;同時,打破了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附著農民身上的身份標簽也將逐漸消失,關于農民的社會歧視也將會減少。
總之,在國家、城市、鄉村等相互博弈下,農民的市民化是未來必然的走向。而農民這個概念將還原為本來的職業稱謂,不再形成一種身份象征,而未來的農民將會很少,即從事現代化農業生產并與其它行業并存不再具有特殊性。
四、結語
傳統中國以農業立國,詩詞中“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這個“百姓”更多指農民。而鄉村社會常被視為底層社會,農民是生活在社會底層,“三農”問題也一直被視為國家難點問題。如梁鴻在調查自己家鄉時便感嘆道:“從什么時候起,鄉村成了民族的累贅,成了改革、發展與現代化追求的負擔?從什么時候起,鄉村成為底層、邊緣、病癥的代名詞?”還有新生代農民工“進不去的城,不想回的鄉”的困境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這將對社會穩定是一個極大的隱患。如果鄉村不是現代化追求的負擔,那么在這個社會轉型期,鄉村如何振興,農民工問題如何解決,城鄉如何協調化發展,這將是最近一段時期國家研究的重點。
對改革開放后農民主體演變歷程進行論述,從中可以體會到農民的心酸與喜悅,從傳統農民到第一代農民工再到新生代農民工,表明隨著國家經濟發展,農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其自我定位也將隨之改變,而落后的戶籍制度必然要被淘汰,農民這個階層也將如“鄉紳階層”一樣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日后農民的概念將回歸本意,即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其人數也將不再構成龐大的社會階層。
回顧歷史,“因為農民的勤勞和智慧,中國創造了燦爛的中華農業文明;因為農民的支持和參與,中國開辟了獨具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因為農民的付出和犧牲,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因為農民的勇敢和創造,中國開啟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進程。”因此,展望未來,期待農民市民化的實現和他們的發展進步,也期待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1] 陸益龍.后鄉土中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2]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三聯書店,2013.
[3] 李昌平.一位鄉黨委書記含淚訴說[J].鄉鎮論壇,2010(10):16.
[4] 左河水.鷓鴣天·農民建筑工[J].中華詩詞,2015(3):33.
[5] 梁鴻.中國在梁莊[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6] 梁鴻.出梁莊記[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3.
[7] 國家統計局.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DB/OL].中國政府網,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
[8] 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結構和特點[DB/OL].中國政府網,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103/t20110310_16148.html.
[9] 賀雪峰.新鄉土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調查筆記[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10] 左河水.鷓鴣天·打工妹[J].中華詩詞,2015(4):33.
[11] 張春華.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與中國鄉村社會建設[J].求索,2011(9):73.
[12] 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DB/OL].中國政府網http://www.stats.gov.cn/statsinfo/auto2074/201310/t20131031_450700.html.
[13] 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DB/OL].中國政府網,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14] 王先明.中國鄉村建設思想的百年演進(論綱)[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1):24.
[15] 國務院.國務院關于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財政政策的通知[DB/OL].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8/05/content_5097845.htm.
[16] 國務院.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DB/OL].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7/30/content_8944.htm.
[17] 韓長賦.正確認識和解決當今中國農民問題[J].農機科技推廣,2014(02):7.
作者簡介:劉琰(1993- ),男,三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