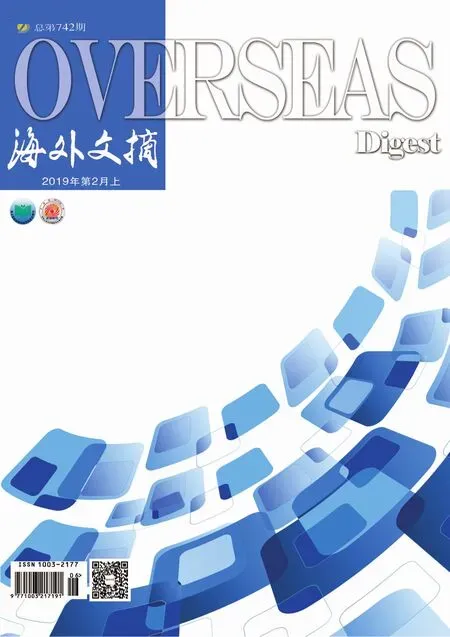場(chǎng)景和框架理論對(duì)小說(shuō)翻譯的啟示
宋秦松
(西安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 德語(yǔ)學(xué)院,陜西西安 710128)
0 引言
Fillmore提出的場(chǎng)景框架理論,作為語(yǔ)言學(xué)中的重要理論之一,盡管對(duì)翻譯學(xué)的發(fā)展及翻譯理論的形成沒(méi)有起到?jīng)Q定性作用,但隨著近年來(lái)眾多學(xué)者對(duì)翻譯過(guò)程的深入研究,以及從更廣闊的視角對(duì)翻譯過(guò)程進(jìn)行詮釋和探索,場(chǎng)景框架理論成為探究翻譯過(guò)程的一個(gè)新的出發(fā)點(diǎn),它不僅對(duì)于理解翻譯行為、指導(dǎo)翻譯實(shí)踐具有重要的意義,還對(duì)于培養(yǎng)優(yōu)秀譯員具有借鑒意義,使譯者更好的理解自己在翻譯過(guò)程中的“雙重”的作用,即:—方面扮演“原文接受者”,另一方面扮演“譯文產(chǎn)出者”的角色。
本文首先詳細(xì)闡述Fillmore場(chǎng)景框架理論中框架、場(chǎng)景等核心概念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得出三種的翻譯行為模型,來(lái)詳細(xì)分析翻譯過(guò)程中各個(gè)要素之間的聯(lián)系,并以《伯爾中短篇小說(shuō)選》個(gè)別句段翻譯為例,簡(jiǎn)要分析場(chǎng)景框架理論對(duì)小說(shuō)翻譯的啟示。
1 場(chǎng)景框架理論
在Fillmore的場(chǎng)景框架理論中, Frame這一術(shù)語(yǔ)所代表的是“任何與現(xiàn)場(chǎng)情景相關(guān)的語(yǔ)言學(xué)選擇的體系,其中最簡(jiǎn)單的即是詞的集合,但同樣包括語(yǔ)法規(guī)則或語(yǔ)言學(xué)范疇的選擇(choices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Scene這一術(shù)語(yǔ)不僅包括可視場(chǎng)景(visual scenes),還包括我們熟悉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dòng)(interpersonal transactions)、標(biāo)準(zhǔn)劇情(standard scenarios)、熟悉的布局、結(jié)構(gòu)、經(jīng)歷、身體印象(body image)等等,更籠統(tǒng)的說(shuō),任何類型的連貫部分,不管是大的還是小的都可以稱之為場(chǎng)景,如人類信仰、行為、經(jīng)歷或想象,等等。


圖1 宏觀框架對(duì)應(yīng)單一宏觀場(chǎng)景

圖2 宏觀框架對(duì)應(yīng)多個(gè)宏觀場(chǎng)景

圖3 宏觀框架對(duì)應(yīng)多個(gè)微觀場(chǎng)景
Fillmore的場(chǎng)景框架理論為語(yǔ)義學(xué)研究尤其是在描寫(xiě)動(dòng)詞語(yǔ)義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此外,它在篇章語(yǔ)言學(xué)領(lǐng)域,包括篇章分析和篇章理解方面也具有指導(dǎo)作用,而這兩者又是翻譯過(gu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此說(shuō)來(lái),場(chǎng)景框架理論對(duì)于翻譯過(guò)程研究的重要性也自然不言而喻。
2 場(chǎng)景框架理論視角下的翻譯過(guò)程
2.1 宏觀框架對(duì)應(yīng)單一宏觀場(chǎng)景
此前,大多數(shù)人都認(rèn)為,翻譯就是把一種語(yǔ)言轉(zhuǎn)換為另外一種語(yǔ)言的過(guò)程。然而事實(shí)并非如此,翻譯是一個(gè)復(fù)雜的過(guò)程,其中譯者既要承擔(dān)“原文接受者”的角色——需要理解原文語(yǔ)言文字背后所表達(dá)的內(nèi)容;還要擔(dān)任“譯文產(chǎn)出者”的角色——將原文作者表達(dá)的內(nèi)容用目的語(yǔ)表達(dá)出來(lái)。翻譯也并非多個(gè)詞或句子的機(jī)械相加,它的單位是整篇文章,詞和句子作為內(nèi)部要素它們之間相互聯(lián)系,相互影響,譯者掌握了它們的聯(lián)系之后,方可進(jìn)行翻譯,Hannerem和Snell-Hornby提出的翻譯模型,就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過(guò)程(Hannerem/Snell-Hornby 1986, S.192)。
圖1中A-Frame指的是原作,是Produzent(原作作者)將Scene(場(chǎng)景)通過(guò)語(yǔ)言文字進(jìn)行解碼后的結(jié)果。在譯者接受原文的過(guò)程中,原文的語(yǔ)言框架會(huì)激活譯者頭腦中已有的場(chǎng)景。場(chǎng)景被激活后,換句話說(shuō),也就是譯者理解原文之后,他選擇合適的ZFrame(目的語(yǔ)框架)將所激活的場(chǎng)景表達(dá)出來(lái),此過(guò)程就是創(chuàng)作譯文的過(guò)程。從這個(gè)圖1中不難發(fā)現(xiàn),譯者在翻譯過(guò)程中并非只起到兩種語(yǔ)言之間的轉(zhuǎn)換作用,而是要將源語(yǔ)框架背后暗含的場(chǎng)景用目的語(yǔ)言框架表達(dá)出來(lái),即扮演著“場(chǎng)景接受者”和“場(chǎng)景表達(dá)者”的雙重角色。
然而,這個(gè)翻譯模型的缺陷在于,它將原作和譯文場(chǎng)景混為一談,將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shí)頭腦里的場(chǎng)景與譯者翻譯時(shí)頭腦里的場(chǎng)景、讀者閱讀譯文時(shí)頭腦里的場(chǎng)景等同起來(lái)。事實(shí)上,場(chǎng)景具有主觀性,每個(gè)人頭腦中的場(chǎng)景不盡相同;其次,每篇文章都是由很多細(xì)小元素構(gòu)成的(例如:?jiǎn)卧~、短語(yǔ)、句子等),而這些細(xì)小元素也會(huì)觸發(fā)頭腦中的場(chǎng)景,那么,原文觸和譯文觸發(fā)的場(chǎng)景就不盡相同了。
2.2 宏觀框架對(duì)應(yīng)多個(gè)宏觀場(chǎng)景
之前所述,F(xiàn)illmore認(rèn)為,譯者在接受原文時(shí),頭腦中會(huì)構(gòu)建出一個(gè)與源語(yǔ)言框架相應(yīng)的場(chǎng)景,該場(chǎng)景與譯者的個(gè)人經(jīng)歷和頭腦中形成的范例知識(shí)相關(guān)。Vermeer和Witte據(jù)此又提出了新的翻譯模型,該翻譯模型中涉及三個(gè)參與者——原文作者、譯者和讀者,由于主觀原因,三者頭腦中產(chǎn)生的場(chǎng)景是不同的,所以源語(yǔ)言框架和目標(biāo)語(yǔ)言框架背后至少暗含著三種場(chǎng)景,如圖2。
如圖2所示,原文作者帶著某種交際目的將某場(chǎng)景用源語(yǔ)言框架表現(xiàn)出來(lái),譯者作為接受者將源語(yǔ)言框架在頭腦中擴(kuò)展為一個(gè)場(chǎng)景,然后又將這個(gè)場(chǎng)景用目的語(yǔ)言框架表達(dá)出來(lái),最后讀者接受到目的語(yǔ)言框架后,頭腦中會(huì)激活自己的場(chǎng)景。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翻譯并非單純是一個(gè)“場(chǎng)景的接受”和“框架的創(chuàng)作”來(lái)回轉(zhuǎn)化的過(guò)程,“場(chǎng)景”和“框架”存在著不對(duì)等關(guān)系,當(dāng)某一場(chǎng)景通過(guò)語(yǔ)言框架被表達(dá)出來(lái)時(shí),場(chǎng)景不可避免地被縮小了,它只能凸顯場(chǎng)景的某一方面,其他方面未加指明;當(dāng)接受語(yǔ)言框架時(shí),過(guò)程剛好相反,語(yǔ)言框架通過(guò)語(yǔ)言使用者的主觀認(rèn)識(shí)、范例知識(shí)得到了拓展,最終形成了頭腦中的場(chǎng)景。總的來(lái)說(shuō),翻譯就是語(yǔ)言框架放大成場(chǎng)景,場(chǎng)景縮小成為語(yǔ)言框架的過(guò)程,作者、譯者和讀者背后的場(chǎng)景是截然不同的,語(yǔ)言框架激活出的場(chǎng)景與語(yǔ)言使用者所處的文化、個(gè)人經(jīng)歷和頭腦中形成的范例知識(shí)息息相關(guān)。
譯者在接受源語(yǔ)言框架時(shí),要盡量遵循客觀的原則,避免頭腦中形成過(guò)于主觀的場(chǎng)景,要借助自己的源語(yǔ)言文化能力盡可能貼近原文作者想要表達(dá)的場(chǎng)景;并利用自己目標(biāo)語(yǔ)言能力將原文場(chǎng)景表現(xiàn)出來(lái)。此外,目標(biāo)語(yǔ)言框架不僅與譯者頭腦中形成的場(chǎng)景有關(guān),還與翻譯目的有關(guān),根據(jù)翻譯委托者的需要,譯者可以選擇追求原文和譯文的相近,也可以選擇原文和譯文的“等值”。
2.3 宏觀框架對(duì)應(yīng)多個(gè)微觀場(chǎng)景
根據(jù)篇章語(yǔ)言學(xué)來(lái)看,一篇文章是一個(gè)宏觀的語(yǔ)言框架,它是由許多不同層面的微觀語(yǔ)言框架構(gòu)成的,這些不同層面的微觀語(yǔ)言框架會(huì)激活不同層面的微觀場(chǎng)景,這些微觀場(chǎng)景間雖沒(méi)有嚴(yán)格的等級(jí)或線性關(guān)系,但它們之間相互聯(lián)系,相互補(bǔ)充、作用,最終形成一個(gè)有機(jī)整體。此外,由于語(yǔ)言使用者在將場(chǎng)景轉(zhuǎn)化為語(yǔ)言框架時(shí),會(huì)不可避免的將場(chǎng)景縮小,因?yàn)檎Z(yǔ)言的選擇往往伴隨著視角的選擇,一篇文章的微觀框架(單詞、詞組和句子)的選擇體現(xiàn)出語(yǔ)言使用者所采取的視角,例如:kaufen,verkaufen,kosten 這三個(gè)動(dòng)詞,每個(gè)詞都可以激活商業(yè)活動(dòng)場(chǎng)景,但它們所表達(dá)的視角又是截然不同的,每選定一個(gè)詞,必然意味著場(chǎng)景某一方面的凸顯和其他方面的缺失。這樣一來(lái),翻譯并不僅僅是將源語(yǔ)言宏觀框架轉(zhuǎn)化為目的語(yǔ)宏觀框架的過(guò)程,而是要將源語(yǔ)言微觀框架背后的場(chǎng)景用目的語(yǔ)微觀框架表達(dá)出來(lái),同時(shí)還要保證兩者視角一致,功能對(duì)等,目的語(yǔ)微觀框架最終要形成一個(gè)有機(jī)的整體。
既然微觀框架如此重要,微觀框架與翻譯之間的關(guān)系究竟是怎樣的?對(duì)此語(yǔ)言學(xué)家Rickheit和Strohner就對(duì)此進(jìn)行了探究。他們發(fā)現(xiàn):人們?cè)诮邮芑騽?chuàng)作文章時(shí),語(yǔ)言符號(hào)會(huì)在被重新加工、解讀,這個(gè)過(guò)程包括語(yǔ)義和句法加工,語(yǔ)義加工涉及四個(gè)層面,包括話語(yǔ)模式、命題、概念體和詞意加工,與它們對(duì)應(yīng)的四個(gè)層面的句法加工分別是話語(yǔ)、句子、詞組和詞匯加工,具體表現(xiàn)如圖3。
圖3顯示,一個(gè)宏觀場(chǎng)景由許多不同層面的微觀場(chǎng)景構(gòu)成,不同的微觀場(chǎng)景之間相互聯(lián)系、相互影響共同組成一個(gè)宏觀場(chǎng)景,在接受原文過(guò)程中,譯者頭腦對(duì)微觀語(yǔ)言框架進(jìn)行加工,在思維上將句子抽象成為命題,將詞組抽象成為概念體,將詞匯抽象成為詞義,命題、概念體和詞義在頭腦激活場(chǎng)景,經(jīng)歷一個(gè)放大的過(guò)程;在創(chuàng)作譯文過(guò)程中,過(guò)程恰好相反,譯者在思維上對(duì)場(chǎng)景進(jìn)行加工,將其概括成為命題、概念體和詞義場(chǎng)景,最終以句子、詞組和詞匯的形式表達(dá)出來(lái)。此外,單個(gè)命題并非可以直接加工為句子,這個(gè)加工過(guò)程需要考慮作者的交際目的、文章主題和語(yǔ)境,換句話說(shuō),小的加工單位從屬于大的加工單位,概念體從屬于命題,命題從屬于話語(yǔ)模式,話語(yǔ)模式從屬于當(dāng)前所在的語(yǔ)用和文化背景。
例一:
“Ich kann nicht Schule putzen;ich bin immer schon aufgefallen wegen schlechten Schuhputzens.”
原譯:“我不會(huì)擦皮鞋;我一向因?yàn)槠ば恋貌涣粒么蠹覀?cè)目相看。”
改譯:“我不會(huì)擦皮鞋;我一向因?yàn)槠ば恋萌绱酥畨模灾劣诖蠹覍?duì)我刮目相看。”
原譯使用了“側(cè)目相看”這個(gè)詞,顯然與源語(yǔ)言框架——“auffallen”是一一對(duì)應(yīng)的關(guān)系,兩者含義十分貼近,原譯嚴(yán)格遵守了原文的字面含義。然而,引得大家“側(cè)目相看”卻會(huì)引發(fā)異議,其一,讀者可理解為,因?yàn)槠ば恋貌涣粒源蠹覍?duì)皮鞋側(cè)目相看。其二,可理解為,我擦得不亮,大家對(duì)我側(cè)目相看。聯(lián)系文章上下文,很明顯文章想表達(dá)的是第二層含義,而相較于“側(cè)目相看”,“刮目相看”更能體現(xiàn)出“我”對(duì)擦皮鞋的不擅長(zhǎng)。所以,改譯雖然沒(méi)有嚴(yán)格遵守源語(yǔ)言框架,但是它所給出的信息卻更加透明,有助于讀者構(gòu)建場(chǎng)景。
例二:

原譯:“這沒(méi)多大關(guān)系。我們反正要追加一定的百分比零頭。”
改譯:“這沒(méi)多大關(guān)系。我們考慮到了一定百分比的誤差。”
在這個(gè)例子中,原譯出現(xiàn)的問(wèn)題和上面例子相同,即直接將源語(yǔ)言框架轉(zhuǎn)化為目標(biāo)語(yǔ)言框架,而沒(méi)有將源語(yǔ)言框架背后的場(chǎng)景,通過(guò)目標(biāo)語(yǔ)言框架合適的表達(dá)出來(lái),這樣容易讓讀者不知所云,不能很好的構(gòu)建出其所要表達(dá)的真實(shí)場(chǎng)景。
例三:
“[...]und da waren Türen mit Emailleschild chen:VI a und VI b.”
譯文:兩扇門(mén)之間都掛著搪瓷小牌,上面寫(xiě)著“一年級(jí)甲班”和“一年級(jí)乙班”。
在這個(gè)例子中,譯者將羅馬數(shù)字VI譯為“一”將a,b分別譯為“甲”,“乙”反倒不能看作紕漏,而是充分的考慮了源語(yǔ)言文化和目的語(yǔ)言文化之后得出的
3 舉例說(shuō)明場(chǎng)景框架理論對(duì)翻譯的啟示
成果,即:將源語(yǔ)言框架背后代表的場(chǎng)景通過(guò)目的語(yǔ)言框架恰當(dāng)?shù)乇磉_(dá)了出來(lái)。
《伯爾中短篇小說(shuō)選》中值得細(xì)細(xì)推敲的句段翻譯還有很多,由于篇幅原因,文章在此就不進(jìn)行一一贅述,通過(guò)以上三個(gè)實(shí)例筆者主要想要說(shuō)明,翻譯并非是一個(gè)簡(jiǎn)單的語(yǔ)言框架轉(zhuǎn)換的過(guò)程,譯者在進(jìn)行翻譯時(shí),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源語(yǔ)言能力,盡量理解并構(gòu)建出其背后暗含的場(chǎng)景,然后利用自己的目的語(yǔ)言優(yōu)勢(shì),將其場(chǎng)景恰當(dāng)?shù)谋磉_(dá)出來(lái)。
4 結(jié)語(yǔ)
Fillmore提出的場(chǎng)景框架理論和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的翻譯模型對(duì)分析小說(shuō)翻譯存在的問(wèn)題,為解決譯者翻譯途中遇到的困難提供了新的視角和途徑。譯者在翻譯過(guò)程中要擺脫源語(yǔ)言框架的干擾,避免因?yàn)樽非笤凑Z(yǔ)言和目標(biāo)語(yǔ)言框架的一致性而忽略了雙方場(chǎng)景的一致性,從而造成讀者“不知所云”的現(xiàn)象,在目標(biāo)語(yǔ)言框架下尋找和源語(yǔ)言場(chǎng)景最佳關(guān)聯(lián)的詞和句式,將翻譯看成一種新的創(chuàng)作,才是一個(gè)好的譯者應(yīng)當(dāng)具備的素質(zh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