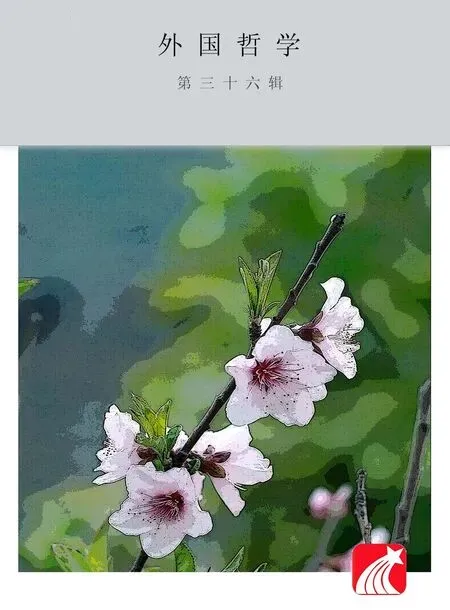認知建構主義、實在論與觀念論
湯姆·洛克摩爾(Tom Rockmore) 著
趙英男** 譯
內容提要:巴門尼德提出“思維與存在同一”的論斷,開啟了哲學傳統中有關知識的討論。對這一主張主要有三種理解方式:第一種觀點認為如果巴門尼德是位懷疑論者,那么他會認為我們無法獲知實在之物、實在或世界,并且不存在知識;第二種非常流行的觀點認為我們能夠獲知實在之所是,而不僅僅是其顯象;第三種是現代建構主義觀點,認為我們沒有也不能認知實在,但我們能夠而且的確認識到人類實在。建構主義通常被認為是康德的一種獨特認知方法,它意味著思維著的主體并非被動地接受知識,而是主動地建構知識。以西方哲學傳統為背景討論認知建構主義,將有助于澄清以下三點:其一,認知實在的努力從未取得任何進步;其二,建構主義是當下富有前景的認知方法;第三,所謂觀念論與實在論之間無法兼容的觀點,主要抑或完全基于一種誤解。
一、導言
何為“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在國際關系、藝術、數學、教育等領域中該詞匯有多種不同的使用方式。①比如,可參見最近對于該領域全面的研究,Theo Hug, “Towards a Dialogue Among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s”, in From Constructivist Monologues to Dialogues and Polylogues.Constructivist Foundations, 13 (2), 2018, pp.204-206。藝術建構主義強調藝術作品的社會建構性特征;俄羅斯建構主義是由弗拉基米爾·塔特林(Vladimir Tatlin)與亞歷山大·羅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大約在1915年于俄羅斯發起的抽象藝術領域中的一場樸素運動②相關討論參見J.M.Nash, Cubism, Futurism and Constructivism, New York: Barrons, 1978。;教育建構主義是一種有關人們在社會情境中如何學習的心理學理論,它與讓·皮亞杰(Jean Piaget)③參見 Jean Piaget,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the Chil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和維戈茨基(L.S.Vygotsky)等學者相關;在數學哲學中,建構主義證明理論主張我們通過發現(或“建構”)一個數學對象來證明其存在是必然的④參見 Michael Dummett, Elements of Intuition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st ed.1977; 2nd ed.2000。。
簡言之,我們無法在一般意義上討論“建構主義”。在本文中,這個詞用來指代通常被認為與康德相關的一種特定認知路徑。在此領域核心人物之一恩斯特·馮·格拉澤菲爾德(Ernst von Glasersfeld)看來,“(激進的)建構主義持有如下觀點:思維著的主體并非被動地接受知識,而是主動地建構知識”⑤Ernst von Glasersfeld, Partial Memories: Sketches from an Improbable Life, Charlottesville: Imprint Academic, 2009, p.264.。
本文將在哲學傳統的語境中發展馮·格拉澤菲爾德上述通俗主張并論證以下三點:其一,自古希臘以來認知實在之物(也被稱為實在或世界)的努力從未取得任何進步;其二,建構主義或不試圖了解世界之所是而是將之視為經驗中被給予之物的努力,是當下富有前景的替代方案;第三,所謂觀念論與實在論之間無法兼容的觀點主要抑或完全基于一種誤解。
二、巴門尼德、康德與認知問題
1.界定認知問題
知識問題以不同方式貫穿于整個西方傳統中。似乎有多少位哲學家對此議題表露興趣,就有多少種或幾乎有多少種認知方法。經過大約2500年的爭論,顯然沒有任何一種認知方法是無爭議的。或許最穩妥的概括就是,對認知而言,當一種知識問題最初在傳統中很早被提出后,哲學史就是由一系列試圖應對、解決或克服該問題的努力構成的。
為了理解這一問題,思考埃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這位物理學家的觀點會很有幫助:
無論物理學概念看上去多么像就是由外在世界決定的,但是它們仍然是由人類心智自由創造而非唯獨由外在世界決定的。在我們試圖理解實在的努力中,我們有點兒像一個正在努力理解一塊密閉手表運行機制的人。他看著表盤又轉動表針,甚至聽一聽表針的滴答聲,可是他沒辦法打開手表。如果他非常聰穎,他能夠形成有關運行機制的某種理論,該理論可能會與他所觀察到的一切現象相符,但他或許永遠無法非常肯定地認為他的理論就是能夠理解他所觀察到的一切的唯一理論。他也將永遠無法把他的理論同真實的運行機制加以比較,甚至就連這一對比是否具有意義也無法想象。①Albert Einstein and Leopold Infeld, The Evolution of Physics: The Growth of Ideas from Early Concepts to Relativity and Quant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1, p.3.
愛因斯坦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無法把我們的理論同理論的對象加以比較,那么我們如何能夠獲知實在之物呢?作為物理學家的愛因斯坦關切的自然是物理學,可是這一知識問題卻更為普遍。它涉及我們知道什么以及我們如何能夠獲得知識。這是對于一系列非常復雜的認知關切的一種相當簡潔的表述。諸如實在之物(the real)、實在(reality)以及世界(the world)等詞匯意味著知識對象的存在獨立于觀察者。而人類的實在之物(the human real)、人類的實在(human reality)以及人類世界(the human world)等術語指的是被我們經驗到的事物。這一簡單區分引發了試圖克服它的一系列漫長努力。比如,唐納德·戴維森(Donald Davidson)對被他稱為概念圖示(a conceptual scheme)觀點的批評。他的學說遙相呼應著弗雷格的語義學,認為主體和客體、認知者和被認知事物之間不存在中介物。①參見Donald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Donald Davidson,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p.183-198。晚近的討論,可參見Robert H.Myers and Claudine Verheggen, Donald Davidson’s Triangulation Argument: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Routledge,2016。
2.巴門尼德與知識問題的起源
知識問題貫通于整個西方哲學史。巴門尼德在當下語境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提出了持續回蕩在其后傳統中的對此問題的早期表述及其解決方案。
巴門尼德顯然是古希臘時期首位可認定的在現代意義上關切知識問題的思想家,更準確說,他是首位從語言來論證世界本質的思想家。他同時也是首位聚焦于討論后來成為希臘形而上學核心問題的“實在”或存在性質的思想家。他將知識等同為認識世界,并對其以他稱為真理之路的方法加以研究。
巴門尼德并非一位經驗主義者,他此刻將其有關認知的主張立基于一種邏輯辯證法之上,該方法可能允許不訴諸任何感性或感性經驗來進行有關存在或實在的推導。我們回想一下,真理之路起始于如下石破天驚的主張:“存在者存在,且它不可能不存在。”該主張以寥寥數語指出,認知的主旨就是認識不可改變的實在之物。
本文將討論巴門尼德令人費解的下述主張:“to gar noein kai estin einai”②DK 28 B 3, Clement of Alexandria, Stromateis, 440, 12; Plotinus, Enneads, 5, 1, 8.,或以今天的話來說,認知與存在同一。這一簡短陳述指向了他對知識的哲學問題所持有的觀念以及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案。
似乎有三種可能方式來理解這一主張。第一種可能方式是認為巴門尼德是位懷疑論者,也即他認為我們無法獲知實在之物、實在或世界,因此不存在任何知識。被視為懷疑論鼻祖的蘇格拉底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我只知道我并不知道。如果巴門尼德是位懷疑論者,那么懷疑論的起源要早于蘇格拉底。
第二種可能方式是巴門尼德認為,認知要求我們超越僅僅是顯象(appearance)的東西,而獲知實在的本來面目。這意味著存在一個雖然無法通過經驗認知,但是能夠被認知的實在的世界。上千年來我們能夠且確實認識到世界的觀點一直是獲得知識的主要方法,但卻從未得到證明。如果這一方法是正確的,那么知識問題的解決就取決于證明我們認識到了世界。此時困難在于理解“認知”這個主張的含義。因為顯然,我們熟知的認知世界主張的一切形式都預設了事物的顯象和其所是之間的區別。
最后一種可能方式立足于世界與人類世界或經驗中被給予的世界之間的區分。在這種觀點看來,雖然我們無法認知世界,但我們能夠認知人類世界,而后者與世界的關系尚未或無法被我們知曉。
現在出于眼下的目的,我們可以把主張我們無法獲得知識的懷疑論觀點放在一邊。迄今最為流行的觀點是說知識取決于認知實在之物或事物之所是,比如,從事物顯象展開回溯性因果推斷。但部分是由于從事物顯象推斷事物之所是存在著困難,因而其相反觀點,即雖然我們尚未且無法獲知實在,但我們確實且能夠認識人類實在的主張,在現代傳統早期開始吸引人們的關注。后文中我會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3.巴門尼德對于前現代爭論的影響
受巴門尼德啟發,之后的許多思想家試圖通過證明上述一般主張的某種形式來解決知識問題,而該主張如巴門尼德所說,認為認知與存在同一。讓我們來分析柏拉圖的觀點。
柏拉圖是首位試圖證明巴門尼德觀點—因為思維和存在同一,所以我們能夠認知實在—的重要思想家。柏拉圖的證明依賴于著名的形式說或理念論—它通常被認為屬于柏拉圖,但他顯然無法以可被人接受的方式對之加以明確表達。
在《斐多篇》中,蘇格拉底說他發明了形式理論來替代古希臘對于因果性的科學解釋。現代因果理論立基于動力因(efficient causation)之上,這非常不同于古希臘有關因果性的看法。后者的因果性理論不僅包括對于原因的識別,也包括什么算作(因果)解釋的理論,并且既包含動力因也包含目的論解釋。比如,根據蘇格拉底的學說,現代科學依賴一種解釋一般因果關系的因果性分析,但可能無法解釋特定原因與個體性結果之間的關聯,或者這么說,無法解釋特殊因果性。
柏拉圖的形式理論是一種非標準的因果理論,區別于科學因果關系,柏拉圖以此來解釋我們如何獲知個體性事物。依據這種理論,每一個特殊個體都由事物的形式所引發。蘇格拉底說,“我們習慣于假設一個單一的形式關聯于我們以同一名稱指稱的許多事物中的每一個”①John Cooper (ed.), Plato’s Complete Works, Cambridge/Indianapolis, 1997, 596A, p.265.。最低限度的因果理論至少包括一個原因與一個結果。形式理論通過事物的形式來解釋每一個事物,比如,每個桌子作為一個結果通過作為原因的“桌子性”(tableness)這個形式或概念得到解釋。但不知出于何種理由,柏拉圖否定了從結果向原因的回溯性推斷。比如,若存在一個桌子,他不認為我們能夠從一個特定桌子或特定顯象,回溯性地推理或推斷出所謂的“桌子性”,即原因。柏拉圖對于科學因果性的批判,指出因果解釋的失敗體現為在認知實在之物過程中無法滿足巴門尼德的知識標準。柏拉圖通過設定智性直觀這一非因果性基礎解決了這一問題并回避了懷疑論。易言之,在柏拉圖看來確實存在著事物和事物之形式之間的區分,但我們無法從事物回溯性地推斷出事物的形式。如果有人能夠直覺到實在而直接把握到形式,那么知識就是可能的。
4.論證思維與存在同一的現代努力
古代涌現的知識問題體現在之后所有爭論之中。該爭論蘊藉于一系列漫長努力,它們試圖證明如巴門尼德所指出的,思維能夠認知存在或世界。但其中每種努力可能都失敗了。
現代有兩件事發生。其一是柏拉圖之后知識問題向因果性方法回歸;其二是有關知識的第二種或替代性策略的產生。認識論中現代因果性方法沒有考慮柏拉圖對回溯性因果推斷的拒絕,后者自然成為對現代因果性認知理論的可能批判。哲學家們很難相信看上去是黃金的事物卻實際上是黃鐵礦。在大約2500年徒勞無益的努力后,許多學者認為試圖認知實在的因果性方法依舊是最富前景的方法。這一觀點由于現代諸多努力無法提出一種知識的因果理論而受到挫敗。同樣在現代出現的更有意義的方法,是我將稱為“認識建構主義”的非常不同的知識策略。
知識的現代因果理論之所以失敗,是與柏拉圖拒絕我所說的回溯性因果推斷有關。為了闡明為什么這一推斷的失敗使得我們必須拒絕認知的因果性方法,在此有必要再回到柏拉圖。
問題在于我們熟知的主張,即認知必須在因果性基礎上證明思維和存在的同一。如果世界是原因而經驗是其結果,那么這一方法試圖通過從結果到原因的推斷來證明我們能夠獲知實在。
在柏拉圖看來,這類推斷是無效的。認為一個原因帶來一種結果是正確的。如果我們知道原因,我們就能夠且通常確實知道結果。然而從一個結果卻能推斷出不同原因。出于尚不明確的理由,柏拉圖似乎認為從結果向其原因的反向因果推斷無法使我們認知實在,因此也無法讓我們證明思維和存在的同一。
我們可以通過有時被稱為新的觀念途徑(the new way of ideas)來闡明這一點。這一術語被經驗主義者洛克用來批判理性主義者笛卡爾。我會使用“觀念途徑”(way of ideas)這一詞語來寬泛地指代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以區別于舊的觀念途徑或柏拉圖式的形式論。形式論是直接或無中介的。與柏拉圖式觀點不同,對于知識的現代因果分析并非直接的而是間接的。柏拉圖式方法要求一種雙元關系:進行認知的主體以及主體認知的形式或對象。在現代產生的與柏拉圖主義特征不同的改變,是主體與認識對象的間接關系。根據這種新的觀念途徑,認知要求一種三元關系:進行認知的主體,被認知的對象以及表象(representation)或進行認知的認知者與他所認知對象之間的中介。
一個理性主義者試圖通過從思維到世界的推斷獲得認知,而一位經驗主義者則試圖通過從世界到思維的推斷獲得認知。理性主義者笛卡爾認為在特定條件下我們能夠有保證地從思維推論到世界。在他看來,清楚而明白的觀念是真確的。因此,通過從心智中的觀念向實在的得到證立的推斷,觀念可靠地告訴我們世界的本來面目。
在笛卡爾的知識論中,他至少做出三個假設:首先,如前所述,心智中一些得到揀選的觀念作為有關世界知識的有保證來源是可接受的,因為如他所說,上帝不會欺騙我;其次,心智中的觀念是結果,而其原因是世界;以及第三,與柏拉圖相反,他認為重新運用柏拉圖拒絕的因果解釋,我們能夠有保證地通過逆向因果推斷,從作為結果的心智中的觀念回溯性推理出其原因或世界,因此我們獲知了世界。
洛克的經驗主義部分地基于對笛卡爾理性主義的拒絕。洛克作為一位經驗主義者,認為心智中所有觀念都來自于經驗。追隨笛卡爾,他區分了簡單觀念(我們無法創造它們以及因為它們與世界一一對應而不可能是錯誤的,因此是必然為真的)與復雜觀念。我們以正確或不正確的方式將簡單觀念組合為復雜觀念,后者可能或不能與世界相符合。
從心智推論到世界的理性主義和從世界推論到心智的經驗主義是知識論中兩種對立的方法。但笛卡爾式理性主義、洛克式經驗主義以及所有其他觀念途徑的變體都有一個相同的基本缺陷—基于觀念途徑的理論依賴于觀念或對象的表象與它們所指涉對象之間的認知關系。如果我們不能將對于實在的觀念同實在加以比較,我們就無法證明并且完全無法獲知從事物的觀念到該觀念指涉之事物的推斷是得到證成的或正確的。
讓我們來總結對于這一點的論證。現在我們已經討論了基于形式論的古代柏拉圖方法以及基于觀念途徑的現代替代性理論。柏拉圖主義拒絕了一種回溯性因果分析,因此也拒絕了對于知識的因果性解釋。這意味著我們通過直覺直接獲知實在而沒有解釋這是如何可能的。對于因果分析的現代回歸同樣是不可接受的。如柏拉圖很久之前所說,借助從結果向原因的回溯性推斷(它無法證明我們能認知世界),是無法證明知識的。總之,如果我們將巴門尼德對于知識問題的表述理解為要求證明思維與存在的同一,那么一切證明這一結論的努力都失敗了。
5.康德、表象主義與認知建構主義
雖然證明我們確實獲知實在的努力是最受歡迎的獲得知識的方法,但直到認知建構主義在現代興起之時尚未有人在此問題上稍有進展。我現在來討論我認為取得進步的第一個標志。該轉變通常與康德這位批判哲學鼻祖相關。康德有時被認為是最初的建構主義思想家。①參見Jerome Bruner,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也有人認為弗朗西斯·培根、托馬斯·霍布斯以及詹巴蒂斯塔·維科這些早期思想家在康德之前開啟了這一傳統(就培根而言則是導向了法律建構主義)。②Fuller 將社會建構主義的起源歸屬于Francis Bacon。參見Steve Full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2016, pp.352-355。
康德提及培根時強調了他對于現代自然科學誕生所發揮的開創性的重要作用。康德認為“批判的”(critical)一詞在此傳統中被首次提出,在此語境中它意味著他能夠證明(prove)他試圖提出(show)的論斷。至于這一觀點是否正確,則是一個解釋上的問題。康德所謂的證據可以等同于一個法律問題(quid juris)或司法論證,而非事實問題(quid facti)。這一對比區分意味著,既然一個司法論證并非哲學演繹,那么康德為其立場所提供的理由因此是“演繹而來的”而未得到證明。③參見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Allen Wo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 116, pp.219-220。
一言以蔽之,康德的立場在逐漸演進。在不同時期,他持有兩種非常不同的認知立場。這兩種不同的立場可以被視為對于知識問題的彼此替代性解決方案。順便提及且同樣值得強調的是,雖然康德通常被理解為是在回應休謨,但他也回應著包括柏拉圖在內的其他思想家的觀點。
康德的知識學說在不同文本中得到處理分析,最為突出的是《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這本他寫作了將近12年的巨著。由于他顯然在不斷地對手稿加以補充,完成的著述中同時包含其理論的早期與后期形態。康德最初的方法,是對我們已然熟知的現代觀點的重述,該觀點因笛卡爾、洛克以及其他思想家借助觀念或康德所說的表象而得以發展。康德對于借助觀念的認知方法的回應,立足于他對于“顯象”(appearance,Erscheinung)和“表象”(representation,Vorstellung)的區分。在康德看來,如果存在顯象,那么一定存在著顯現著的某物。①參見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Allen Wood, B xxvi-xxvii, p.115。
在顯象與表象之間存在著一個基本的差異。一切表象都是顯象,但只有一些顯象是表象。區別很明顯:一個顯象指涉著自身之外的使得其自身作為結果的原因;而一個表象因準確地表征自身的原因而指涉自身之外的事物。如今康德的后繼者們(即繼承康德表象主義方法的學者—譯者注)提出的觀念理論與批判哲學的表象階段并沒有重要的不同之處。康德的表象主義(representationalism)接續了理性主義者笛卡爾與經驗主義者洛克借助觀念的認知方法。在其表象階段中,康德提出、重述卻未能解決這一回蕩在批判哲學之前的整個哲學傳統中的問題。
我有兩點提議。首先,康德的批判哲學同時秉持了兩種不兼容的知識立場;其次,最初的或表象的立場并沒有解決而只是重述了傳統的解決知識問題的方法,該方法試圖證明我們能夠或確實知道或準確地表征世界。易言之,康德在表象階段與其他現代思想家如出一轍,受到現代因果形式的表象理論吸引;同時與他之前或之后的表象主義者們一樣,也未能通過表征世界而解決知識問題。不過通過第二種立場,他獲得了成功或至少較為成功。
第二種立場涉及所謂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康德并沒有使用這一術語,不過其他人以此來指代其立場。它意味著康德解決知識問題的第二種立場與哥白尼天體理論之間令人困惑的比較。哥白尼的天文學指出太陽并不圍繞地球運動,因為地球事實上是圍繞太陽旋轉,因此它依賴于太陽。這一類比并不是那么有用,因為康德在相當程度上指出知識依賴于主體。
相比較于將知識立基于表象的現代早期努力,康德后期的方法帶來兩個改變: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在認知獨立于主體的對象或世界這件事上我們沒有取得任何進步;其次,康德認為,如果我們翻轉主體和客體的關系,我們或許能做得更好。簡言之,與其假設知識問題在于認知獨立于主體的對象,倒不如作為一種嘗試,我們應當假設認知問題在于獲知依賴于主體的對象。
我稱為“認知建構主義”的康德版本是對于知識問題的替代性方案。簡言之,在康德看來,因為認知必然起源于經驗,而且如果我們無法經驗到世界,我們就無法主張能夠認識到諸如世界這樣的獨立于主體的對象。不過我們能夠主張可以獲知在經驗中被給予的依賴于主體的對象,或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建構”的對象。
康德并不是說任何個人或所有人一同建構了世界。我們無法證明并且不知道是否存在著獨立于心智的世界。可我們確實知道,如果這樣的世界存在,我們并不曾對之加以建構。更確切地說,康德回到世界與人類世界這一古代柏拉圖式區分,并提出如下三個彼此相關的主張:其一,盡管我們沒有而且無法經驗到或認知世界,但人類世界或柏拉圖所說的顯象的世界在經驗中被給出;其二,我們能夠且確實認知到的,如果不是從來無法被經驗到的世界,那么至少是人類世界;其三,正是因為我們建構了人類世界或有時所說的“為我世界”(the world for us),我們能夠主張可以認知該世界。
6.認知建構主義的古今形態
在何種意義上我們建構并且獲知人類世界?在何種意義上我們建構了我們的經驗?這些問題一部分在康德之前得到了解答,一部分由康德加以回應,還有部分有待回答。由于并不是康德創造了建構主義,所以就有必要在歷史語境中分析“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在古代數學,更確切地講是在用直尺和圓規建構幾何圖形中得覓其蹤。單一幾何對象的建構,比如,一個直角三角形的建構,證明了這一類事物的存在。
建構主義通過三位思想家在17世紀進入現代哲學,他們是英國哲學家培根與霍布斯以及意大利思想家維科,并在18世紀則通過德國思想家康德等人得以延續。霍布斯關切他所說的公民社會或國家(commonwealth)。他認為它們與幾何類似,我們由于了解其原因、生成與建構而得以認識它們。因此,對于“建構人類世界意味著什么?”這個問題的一種解答,就是指出我們建構并了解公民社會。
維科受霍布斯影響,他將后者的理論加以一般化而成為一種一般的知識學說。如霍布斯一樣,維科是反對笛卡爾的。笛卡爾提供的知識理論是關于一個已然構成的世界的,而維科倡導如下觀點,即他認為真確的(true)與人為的是一致的,他將此觀點運用到由我們建構的對象上,以此區別于由自然生成的對象。在維科看來,因為公民社會的原理存在于人類心智中,并且人類創造了公民社會,因此人類能夠認知該社會。
霍布斯和維科都關切如何將人類社會理解為一種歷史建構。康德以一己之力普遍化了他們的建構主義方法,并沿著如下非歷史的進路展開:首先,當且僅當知識的對象是可認知的,知識才是可能的;其次,我們根據在人類心智中被賦予的原則或范疇建構人類世界;最后,我們建構的對象由于我們的建構而是可認知的。
7.對康德哥白尼革命的批判性評述
巴門尼德的知識和存在同一這一許久以前的提議,引發了后來不同學者在長達若干個世紀中證明這一主張的努力。我已然指出,巴門尼德主張思維和存在同一的這個主張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引發了對于知識的哲學討論。如果巴門尼德的觀點被懷疑論式地解讀,那么對于知識的追尋就失敗了。如果它被解釋為追求對于世界的知識,那么它同樣也失敗了。如果它被解釋為求索人類世界的經驗和知識,那么至少在我們知道且只能知道我們所建構的事物這一假設上,它潛在地是成功的。我認為如下主張是巴門尼德問題的鎖鑰:認知建構主義可能首次為證明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提供了一種成功的路徑。換言之,以康德先知式的語言來說,思維根據它自身的計劃,能夠且確實獲知它所建構的人類世界。①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Allen Wood, B 180-181, p.273.
這一結果會讓一些人開心而讓另一些人絕望。在2500 多年成果寥寥的努力后,許多學者認為,我們要么能夠認知世界,要么對于知識的這一宏偉追求就以懷疑論告終。而另有一些學者認為,雖然我們無法認知世界,但我們通過獲知我們所建構的人類世界而避免了懷疑論。
我們可以對康德的建構主義和建構主義本身加以區分。在此有以下三點相關:康德立場的先天性,它可能具有的不可修正性以及主體觀念。這些要點彼此關聯:正是因為康德認為認知是先天的,所以他主張其理論是不可修正的;并且正是因為康德式認知主體并不是一個人或一群人,所以康德將他的認知主張立基于這樣一種想象的主體—他能夠獲知必然為真因此是不可修正的知識。
康德認為知識必然是先天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除卻特殊情形(如果存在的話),大部分認知主張無法避免爭議,因此至少有可能受到之后的修正。康德指出,哲學若名副其實的話,就是批判的或能夠第一次超越獨斷論而證明其自身主張。對他來說,因為在他的觀點中沒有什么要修正的,哲學既起始于也終結于他自身的立場。這暗示著康德認為在他之前既無哲學也沒有哲學家,并進一步意味著他自己是唯一的哲學家、唯一名副其實的哲學的提出者。他持有的如下假設,即他認為自己已經成功找到認知唯一的可能路徑,與后來思想家解釋、批判和修正包括批判哲學在內的早期思想家觀點的方法完全不一致。似乎他從未意識到,就如《純粹理性批判》甫一面世時事實上所發生的那樣,后來的思想家將會或可能會與自己有分歧。
除卻他試圖證明先天認知的主張,至少有爭議的是康德并沒有成功地提出一種先天的理論。他似乎通常在應當使用“后天”的時候使用了“先天”這個術語。盡管他主張名副其實的知識是先天的,可他的批判哲學卻在至少兩種意義上是后天的。他通過回應他熟悉的其他立場而提出自己的觀點,包括著名的對于休謨批判因果性的回應,也包括對于伍爾夫(Wolff)、鮑姆加滕(Baumgarten)、萊布尼茨(Leibniz)、柏拉圖等人的回應。因為他的理論依賴于感性的接受或以他的術語來講是感性雜多的內容,他的理論進一步是后天的。如果他的立場依賴于感性,那么可以說它就不是先天的,而是顯然并且必定奇特地至少在部分上是后天的。因此,他并沒有演繹或證立他的形而上學方法是先天的。他只是將自己形而上學的立場立基于邏輯、數學還有自然科學那或許成功的先天方法上,并認為不能立基于觀察從而不能立足于后天推斷之上。最起碼,康德認為他的知識理論是先天的這一主張,需要進一步討論。
康德版本的建構主義似乎是一個沒有希望的解決方案。他認為,知識是先天的,因此對任何及一切經驗內容都必然有效,這意味著他的立場也具有相同狀態。如康德所想,這隱含著他不僅推動了哲學,而且更以一種由于是正確因而之后不會受到修改的方式解決了哲學的問題。必然為真的主張和歷史的主張是不兼容的。由于康德拒絕了歷史的視角而采納必然為真的主張,他的立場由于其所具有的先天狀態而遭到有力駁斥。這一點可能使得康德式認知建構主義不再有效,但卻未能否定認知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既不罕見,也不新鮮,雖然未必以此之名,但它在持續不斷、永不停歇地形成我們可接受的理論的過程中,時時發揮著作用。這些理論如果不是關于我們無法獲知的世界,至少是關于在經驗中被給予的世界以及我們自身。在康德生前與身后有不同形式的建構主義。黑格爾在論及以持續的修正過程為基礎的認知過程時,描述了一種后康德式的建構主義形態。黑格爾認為,在逼近經驗中被給予之物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前后相繼的諸多認知理論。知識源自如下過程,在其中我們在接受或在必要時改變理論之前,會形成并檢驗我們的理論并在必要時修正與進一步經驗相左的觀點。
康德將知識視為先天的因而是不可修正的規范性觀點,包含著對于笛卡爾甚至柏拉圖的遙遠呼應。雖然柏拉圖與笛卡爾的觀點非常不同,但兩者都認為不同的認知領域都必然要通過哲學得以證成。柏拉圖認為,哲學通過辯證法證立了數學、科學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認知活動。這一觀點在笛卡爾式的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中得以發揚。康德依舊持有該觀點的另一種樣態。正是因為康德認為哲學必然證立一切認知領域中的所有知識,他會認為知識必然是不可修正的。不過,皮爾斯在他受到忽略的“長期”(long run)觀念中,無疑更接近這一點。這一術語在皮爾斯理論中有不止一種含義,它指代或然率的“長期相對頻率理論”(long run relative frequency view),也意味著一種知識對象的學說。在皮爾斯看來,“必然被所有研究者最后同意的觀點,就是我們所說的真理,而此觀點所代表的對象就是實在”①C.S.Peirce, “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in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I, 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39.。在一切認知領域中,研究通過不同的階段獲得進步,這些階段匯聚于這樣一種觀點,即皮爾斯認為我們最后必然會接受或至少在另一個更強的觀點被發現前加以辯護的觀點。下文中我會回到皮爾斯的學說。
8.費希特、黑格爾與康德之后的建構主義
如前所述,在形成一種成功的認知學說這一共享任務下,認知建構主義貫穿于康德觀念論學說并將其與后康德的德國觀念論者觀點關聯在一起。康德、費希特與黑格爾作為原創性思想家這一事實,使得人們未能關注他們的共性,因此也就增加了理解這一時期思想的難度。康德開啟了德國觀念論者對于認知建構主義的關切。康德之后發生在德國觀念論建構主義的兩大重要改變,包括了人類學轉向(它使得我們將主體視為有限人類)以及歷史性的知識的觀念。
重要的英國經驗論者關切人類知識的不同形式。康德曾是德國首批教授人類學的學者之一,他從1772年一直講授到1796年退休。在他充滿洞見的《實用主義人類學》(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②Kant,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 Louden, introduced by Manfred Kueh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一書中,康德將人類學視為所有學科中的最高學科,因為它回答了下述問題:什么是一個人?休謨青睞人類學式的認知方法。在回應休謨時,康德可以說在其“先驗演繹”最后一部分“演繹”主體觀念時回到了人類學。①參見John Zammito, Kant, Herder and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對于康德哥白尼轉向的后康德式重新表述,通過重新將主體視為有限的人類(在費希特看來,主體是人類個體主體;在黑格爾看來主體既是個體也是復數主體,或他在《精神現象學》中提及的有名的“我們”)而修正了康德的認知方案。
在從康德向費希特的轉變中,德國觀念論拋棄了康德描述認知一般條件的努力,而支持一種非常不同但依舊可歸類于康德式努力的、對于有限的人類如何能夠進行認知活動的描述。康德的哥白尼轉向與熟悉的因果性認知方法決裂,并以引入物自體或世界這一相當大的代價,指出認知主體能獲知其所建構的認知對象。
費希特恰恰拒絕物自體概念,認為它“只是由自由思維產生”,并且不具有任何“無論何種的實在性”。②J.G.Fichte, Science of Knowledg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Peter Heath and John Lach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0.他表明自己認同一種康德式的建構主義,他寫道:“(認知)對象應當被認知能力設定和確定,而非對象設定認知能力。”③Ibid., p.4.自我是絕對活動的,并且單純是活動的,這一主張是費希的“絕對前提”④Ibid., p.221.。費希特將認知主體重新視為有限的人類完全轉變了批判哲學。
費希特從康德演繹的抽象哲學主體向有限人類的轉變,將認知立足于有限人類的活動性之上。在其他地方我已論證過費希特或許受K.L.萊因霍爾德(K.L.Reinhold)的影響,他走得太遠以至于試圖將一切從主體中演繹出來。盡管康德和費希特都對歷史感興趣,但他們都不是歷史性的思想家。康德先天知識的觀念與實踐和空間無關。此外,他認為除了借助經驗以外,我們無法以直覺或其他方式了解自身。費希特認為通過直覺我們能夠具有自我意識而認識到我們的活動受到我們周遭環境或社會語境的限定,但歷史如同心智的法則一樣,以預定的、獨立于人類的方式展開。
黑格爾不同于其前輩之處在于他將歷史維度引入了獨特的德國觀念論建構主義認知方法。黑格爾有關認知具有歷史性的觀點包含兩個方面。首先,一切現實的即是合乎理性的。這是其名言“合乎理性的即是現實的;現實的即是合乎理性的”①G.W.F.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by H.B.Nis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0.的核心觀點。如果一切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那么至少在原則上不存在界限來限制我們能夠認知的事物。這就推動了黑格爾將國家或政治領域刻畫為具有內在合理性的努力。其次,認知在另一種意義上受到了限定,因為每個人必然從屬于一個特定的時空,沒有人能夠外在于這一約束。一切知識甚至哲學,都因此而受到限定,正如黑格爾所說:“這里就有薔薇,就在這里舞蹈吧。”②Ibid., p.22.由此得出,盡管我們可以在無限多樣性中獲知事物之所是,但我們只能從當下歷史時刻這個角度出發知道我們所知道的。如有時所言,認為我們能夠跨過傳統追溯哲學問題甫一進入傳統時的樣態,這不過是哲學思想的白日夢。
黑格爾認為,知識是在歷史的因而是有內在限定的語境中發展。認知從一系列持續不斷的調適中產生,源自于經驗并在經驗基礎上我們形成了會被之后的經驗加以驗證的理論。經驗的理論和經驗之間的互動關系只有兩種形態:要么是經驗的理論與經驗暫時一致,盡管分歧稍后可能會出現;要么是它們未能一致,此時理論必然會受到修正,或更確切來說,是得到加強,以便在解釋最初理論所能解釋的經驗的基礎上再加上至少一個它應當解釋的事物。比如,牛頓力學能夠解釋行星的軌道而無法解釋水星的軌道,而由于廣義相對論能夠解釋一切行星,包括水星的軌道,所以它就是相對而言更強有力的理論。
9.科學建構主義
由于當下是一個科學的時代,舉出一些源自自然科學和科學哲學的例子會頗有幫助。這兩個曾在幾個世紀里連為一體、在現代都包含在自然哲學(Naturphilosophie)之名下的領域最終在19世紀末彼此隔絕,仿佛只是昨天的事情。許多科學家和一些哲學家推動科學主義或將科學運用到科學方法尚未覆蓋的領域中。不時有重要的科學家反對說,如果我們不知道實在,那么科學就沒有意義。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史蒂文·魏恩伯格(Steven Weinberg)認為,如果科學未曾揭示實在之物,那么研究科學就是非理性的。①參見Steven Weinberg, “The Revolution That Did Not Happen”,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5, no.15,October 8, 1998, pp.48-52。另一位物理學家謝爾登·格拉肖(Sheldon Glashow)指出:“存在著永恒、客觀、非歷史的、社會中立的、外在的和普遍的真理,并且這些真理的集合就是我們所說的物理科學。”②參見Sheldon Glashow, “The Death of Science?” in The End of Science? Attack and Defense, edited by Richard J.Elve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2, p.28。認知建構主義則認為如下情形至少總是可能的,即當下科學結論在之后將會改變。
將科學視為細致地一層層揭開實在的真實層次的理論(image)是個不錯的故事,但它與實際科學實踐并不相關,因為后者并不是通過把握實在之物而是通過形成經驗的理論而得以展開。思考一下一位在今天幾乎無人知曉的生物學研究者路德維格·弗萊克(Ludwik Fleck),以及廣為人知的科學哲學家與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觀點。
弗萊克在生物現象領域中首倡社會建構主義方法而先于比如庫恩有關科學發展的觀點。弗萊克指出被稱為乏色曼反映(Wasserman reaction)的測試,即梅毒抗體檢測,是一種只有通過其自身歷史才得以界定的歷史建構。③參見Ludwik Fleck,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translated by Fred Bradley and Thaddeus J.Trennited edited by Thaddeus J.Trenn and Robert K.Merton, foreword written by Thomas Kuh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如奎因之后所言,弗萊克認為被我們錯誤地理解為獨立于心智的事實,是社會建構物。④參見W.V.Quine, “Facts of the Matter”, in American Philosophy: From Edwards to Quine,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W.Shahan and Kenneth R.Merrill,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1977。他的思維群體(thought collective)觀念預見了庫恩科學范式的理念。他認為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受限于思維群體(或思維風格),獲得獨立于心智的事實在科學研究中是一個不可實現的理念。在錫瓦卡(Siwecka)看來,在此與黑格爾觀念相近的弗萊克認為“純粹和直接的觀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感知對象這一活動中,觀察者也即認識論上的主體,總是受到他所處的時代和環境的影響,也即受到弗萊克稱為思維風格的影響”①相關討論參見Sofia Siwecka,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fact’, Thought style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in the epistemology of Ludwik Felck”, in Dialogues in Philosophy, Mental and Neuro Sciences, vol.4,no.2, 1991, pp.37-39。。
庫恩在他的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學說中與弗萊克觀點一致。他認為常態科學形成概念矩陣,理論在其中得到常態地接受或拒絕,而常態科學本身則在科學革命中得到拒絕。②參見Thomas Kuhn,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論述真理觀念從他稱為“內在實在論”的視角轉變時,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③參見Hilary Putnam,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在普特南看來,源自亞里士多德的真理符合論是失敗的。康德已然做出這一推斷,他認為“構成一個對于實體直覺的一切屬性僅僅屬于實體的顯象”④Kant,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Gary Hatfie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41.。庫恩則更進一步,他指出認知主張并不因與實在之物相關而得到證立,而是與一種共享的視角相關。庫恩認為在科學革命之前與之后,盛行著不同的世界觀。在一個著名的段落中,他描述了拉瓦錫(Lavoisier)與普利斯特列(Priestley)觀點上的差異,他寫道:“最起碼,由于氧氣的發現,拉瓦錫看待自然的方式不同了。并且由于不再依賴他以‘不同方式看待’的、假設的固定自然(fixed nature),經濟原則使得我們會說,在發現氧氣后拉瓦錫是在一個不同的世界中工作。”⑤Thomas Kuhn,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118.(經濟原則,即語言經濟原則,指的是人們用快捷有效的語言傳遞信息—譯者注)
庫恩被誤解為是在說科學的終結,他其實是在討論一種科學觀點的有效性,這種科學觀點被假設為揭示了世界,但其實不過是提供了在經驗中給定世界的一種觀點。易言之,未能證明我們獲知世界與現代科學并非不融貫反而是一致的。盡管我們不知道世界,但基于理論是否與其他觀點適切而對之加以建構、接受或拒絕,以此我們獲知了經驗中給予的人類世界。
10.認知建構主義小結
巴門尼德通過要求思維與存在統一或同一的規范性知識觀點,對有關知識的爭論做出巨大貢獻。他所倡導的這一標準已然得到接受,并且作為知識的最低條件似乎是可接受的。知識需要一個主體或認知者以及一個在恰當條件下至少可能被認知的對象,這一點很難被否認甚至嚴肅地質疑。
如前所述,巴門尼德的知識標準可以有三種不同的解讀方式。懷疑論式的解讀使得該標準無法得到滿足;第二種解讀作為貫穿整個哲學傳統的熟知立場,認為知識意味著對于實在之物、實在或世界的認知把握;最后一種解讀認為我們只能獲知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建構的事物。
有意或更通常是無意的對于巴門尼德觀點的回應,即認知要求獲得獨立于思維的實在之物的知識,自前蘇格拉底時期以降便主導著這一爭論。巴門尼德并非懷疑論者。可是顯然,若干世紀以來以證明實在之物的知識作為其目標的不成功努力(之后許多思想家都是如此),如果沒有導致一般意義上的懷疑論,至少導致了這一與認知相關的懷疑論。
這種巴門尼德式的知識方法萌生,發展并開花成熟,進而在許多年后,雖然依舊是無法解決的哲學難題,但早期認同表象主義知識路徑的康德注意到,不僅花朵已然離開花托同時也已枯萎和凋零。雖然未能證明任何形式的認知實在之物的知識主張,但哲學家對這項事業的參與卻不過是對不利的結果稍感挫敗,尤其是他們從未受到足夠挫敗以至于推斷說這整個事業不過是浪費時間。他們總是準備好繼續前行,在要付出加倍努力時沒有一絲猶豫。哲學家們之所以未能注意到這一方法的任何形式的明顯失敗,唯一原因就在于他們顯然未能從經驗中獲得教訓。因此諷刺的是,康德這位否定認知可以是后天的先天思想家、這位我們不應期待他依賴于經驗的思想家提出,在把握獨立于心智的對象這一困境中,我們在實踐上不可能取得任何進展,并因此從認知實在之物之所是的知識轉向了基于認知建構主義的替代性方法。
如果認知實在之物是知識方法中最受青睞的方法,那么就如幾個世紀以來詳盡且令人疲憊的研究結果似乎預示的那樣,在最受歡迎的選擇無法得到證明時,認知建構主義就是立刻變得饒有意味的次優方案。因此毫無意外的是,認知實在之物這一主導著巴門尼德以來的討論的努力,由于認知建構主義作為替代性知識方法的出現而得到補充。
認知建構主義重要的旨趣包括兩方面。首先,它通過最終證明思維與存在的同一而展示了一種滿足巴門尼德知識標準的方法。雖然我將不會在此展開論證,但它或許因此而成為當代最具吸引力的知識方法,而且要比其當代的替代性方案諸如新實在論以及更早的所謂推理主義,還有其他形式的語義學等更饒有意味。其次,它澄清了實在論與觀念論陣營間重要的現代爭論。這兩個術語被廣泛認為是不相容的,特別是在秉持“實在論”立場的人那里,但眾所周知的是它們都以許多不同方式而得到理解。不存在任何當然或共識的方法,可以在不顯著影響我們對于它們每一個及其之間關系的看法的情況下,理解它們及其關系。
本文已然證明,時至今日,在證明形而上學實在論作為一種知者較少的巴門尼德觀點或更為人知的柏拉圖式觀點明顯失敗后,我們應當將認知建構主義視為形而上學實在論的可行替代,同時保留對于基于經驗的一種實在論形態的認同。
在此回應一種常見的質疑頗有助益。觀念論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透徹的理解。①最近的討論可參見Jeremy Dunham, Iain Hamilton Grant, and Sean Watson, Idealism: The History of a Philosoph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2。認為知識問題可以通過某種形式的觀念論—比如認知建構主義—得到最佳解決的觀念論者會遭遇如下質疑,即觀念論與實在論并不相容。
英美分析哲學立基于實在論和觀念論之間假定的互斥性,或更準確來說是對觀念論的一種特定解釋。我們回想本科生G.E.摩爾與伯特蘭·羅素作為J.M.E.麥克塔格特(J.M.E.McTaggart)這位重要的劍橋觀念論者的學生時,他們在很快拒絕觀念論之前,曾短暫地認為自己是觀念論者,甚至是英國觀念論者。
他們對于“觀念論”的理解即使從最好的角度分析,也是成問題的。摩爾顯然如同不了解觀念論一樣對之堅決加以排斥。他明確試圖將觀念論作為一種正常心智的人不會接受的、缺乏常識(這被視為他哲學的核心理念)的荒謬學說而加以否定。摩爾捍衛一種所謂的常識實在論或者說就是常識的立場。他曾在沒有任何實例的情況下(或許他所想的是貝克萊)不光彩地主張,一切形式的觀念論都拒絕外在世界的實在性。①參見G.E.Moore, “Refutation of Idealism”, Mind, 12 (48), 1903, pp.433-453。
羅素要比摩爾更了解觀念論,也更細致。他否定20世紀早期他理解為“無論存在什么,或無論任何可被獲知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精神性的”觀念論。②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rpt.2001, p.19,chapter IV.此時他認為“觀念論”作為認知條件而興起,通過他所描述的條件我們能夠知道他歸屬于貝克萊的認知條件。在羅素看來,貝克萊證明了感覺素材并不獨立于心智,認為事物或他之后所說的“被感知的觀念”(ideas apprehended)不過是精神性的。③羅素對于觀念論的觀點,參見Ibid., pp.19-24, 第四章“觀念論”。
羅素是作為一位萊布尼茨學者而開始其學術生涯的。但在對這位德國哲學家的研究中,他從未提及“觀念論”這個他應當了解或至少從后者非常獨特的觀點中應當獲知的詞匯。④參見Bertrand Russell,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New York: Routledge, 1900,rpt.1992。萊布尼茨贊同觀念論并通常被理解為是一位觀念論者。他或許因其形而上學實在論或實在是由精神性的、非互動的“單子”理論而在哲學上最為聞名。
如果柏拉圖是位觀念論者,那么觀念論在古代哲學中就已很重要,并且古代和現代觀念論之間存在差異。若想理解觀念論和實在論在現代的關系,理解康德就頗有幫助。他通過哥白尼轉向對建構主義抑或同時是觀念論的認知方法做出決定性貢獻。同樣是這位思想家,他認為當觀念論得到正確理解時,它與實在論并不矛盾而是彼此兼容。
康德堅持認為實在論對觀念論至關重要,是屬于其后期哥白尼時期的立場。學者通常沒有意識到的是,他最初認同包括形而上學實在論在內的因果性表象主義,之后則轉而認同一種非因果性的、反表象主義的認知建構主義。在第一版《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并沒有考慮觀念論和實在論的關系。在這部著作的第二版,這一關系成為他理解觀念論的核心。他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與《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都詳細討論了觀念論和實在論的關系。
康德對于觀念論的立場顯然意味著他認同觀念論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的附釋三中,他評論說,雖然他將自己的理論稱為先驗觀念論,但這不應當導致將其與笛卡爾的經驗觀念論或貝克萊的神秘與空想的觀念論相混淆。康德顯然將笛卡爾式的理性主義視為對于世界的懷疑論。他認為笛卡爾持有的觀點是,一個人會自由地否認所謂物質世界(之后,摩爾在關于康德的博士論文中將其稱為外在世界)的存在。此時,康德顯然認為笛卡爾式理性主義會導致對于世界的懷疑論。康德除了指出《純粹理性批判》是貝克萊學說的解毒劑外,在此并沒有處理他的觀點。他頗有助益地堅稱觀念論并不關涉事物的存在,即外部世界,而只是關乎他所描述的“事物存在的感性表象”。他進一步指出“認知能力”反而無法認知事物,以此區分顯象與顯現著的但我們無法獲知的事物。至少,康德在此提出他對于批判哲學先驗觀念論的理解。
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重要的“拒斥觀念論”部分,康德更詳細地回顧了這一問題。與“導論”中觀點一致,他認為笛卡爾的“物質觀念論”使得在貝克萊觀念論中“虛假且不可能”的外在對象的存在變得“可疑且不可證明”。在對這位愛爾蘭哲學家展開進一步批判時,他否定了如果空間屬于物自身那么就可能會出現的、據說是獨斷論的觀點。在康德看來,“疑問式觀念論”對于“從我們直接經驗方法出發,證明外在于我們的存在”這個任務而言是“理性且適切的”。康德指出,雖然仍舊需要證明,但笛卡爾并沒有懷疑內在經驗只有基于外在經驗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他已預見了摩爾的反駁,因此試圖證明觀念論與外部世界存在之間的相容性。
康德兩方面的意圖旨在排除一種他歸之為貝克萊的可能是不正確的觀念論立場,而支持一種他歸之為笛卡爾的正確觀念論立場。在他看來,貝克萊錯誤地認為存在著一個未顯現任何事物的顯象;而笛卡爾正確地指出卻未能證明的是,經驗取決于外部實存。換句話說,康德試圖否定貝克萊式觀念論并證明笛卡爾式觀念論,或他通過證明如下定理,即“對于我自己存在的純然但受到經驗規定的意識,證明了空間中我以外的對象的存在”,而證明“內部經驗只有在外部經驗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這一觀點。①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Allen Wood, B 275, p.327.
康德的證明旨在斷言我在時間中存在的意識“只有通過我之外的事物”才是可能的(也即通過笛卡爾的觀點),而“不是僅僅通過我以外的一個事物的表象”(或貝克萊的觀點)才是可能的。②Ibid.康德進一步對其證明做出三個補充。首先,如他所言,他主張“外部經驗確實是直接的”③Ibid.。其次,他爭辯說純然的自我意識不過是理智表象。這與先驗演繹中主體作為認知位格的觀點是一致的。最后,在弱化他主張內部經驗依賴于外部經驗這一立場時,他強調一種特殊的情況為內在經驗可能不過是源自于想象,因此可能出現外在實存的內部表象事實上與外部實存并不一致的情況。
三、認知建構主義之后
本文第一部分討論了認知問題的發展,它引發了認知建構主義的產生以及巴門尼德式實在論與認知建構主義之間的現代論戰。本部分將討論在認知建構主義興起后,這一認知問題的發展。
1.認知建構主義之后的實在論
在此評述晚近以及最近的實在論正當其時。提及“晚近的實在論”,我設想的時期是1831年黑格爾去世后直至今日近二百年的時光。而“最近的實在論”,我指的是在本文寫作歷程中一種或更多種方興未艾的實在論運動。
當下的歷史蓋棺論定之日,即是有關實在論特別是科學實在論的關切在討論中居于重要位置之時。后康德時期的論戰,見證了如下變遷:黑格爾觀念論迅速衰落,伴隨現代科學迅猛興起而向康德有限的回歸,從觀念論向實在論(以及唯物論)的持續轉變①就這一點而言,Lange 很重要。參見F.A.Lange, The History of Materialism, New York: 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 1925。以及種類繁多的認知建構主義在思想家筆下出現(對這些思想家而言,他們大部分對觀念論既不感興趣,也不認同)。
如前所述,現代傳統中認知建構主義的出現,引發了認知實在之物這一傳統主張的支持者與其反對者(即認為我們只能認知我們建構之物的學者)之間的論戰。前者自然認為認知標準應當如若干個世紀以來一樣,保持不變。形而上學實在論的信徒們并沒有被他們未能認知實在之物而嚇倒,而是揣測他們最終會提出一個嶄新且更好的論證。此外,他們否定了建構主義式的替代方案,認為這不過是懷疑論的一種詭譎變體,后者的信奉者們將背離實在之物的舉動重新描述為比試圖把握實在之物的努力更好。
除卻極少例外,認知建構主義在現代的興起似乎充其量對傳統主張(即將知識理解為對于世界的知識)也作用甚微。后一種認知方法在今時今日的盛行程度一如往昔。晚近的形而上學實在論者包括(排名不分先后):邏輯實證主義者,像埃德蒙德·胡塞爾與馬丁·海德格爾這樣的現象學家;自稱是秉持這一立場的幾位分析性實用主義者抑或稱他們為分析性新實用主義者更妥當,比如理查德·羅蒂、羅伯特·布蘭頓;還有那位終身實在論者希拉里·普特南;以及所謂的新實在論者。晚近的認知建構主義包括(同樣排名不分先后):皮爾斯、奎因、弗萊克、庫恩、納爾遜·古德曼(Nelson Goodman),或許還包括約翰·塞爾(John Searle)。
2.實用主義轉向
當下對于認知建構主義的主要闡述,是在實用主義之中。實用主義不曾是嚴密融貫的哲學思潮。但它由于幾位分析哲學家向他們堅稱為“實用主義”立場的轉變(這種堅稱有時是令人驚訝的),而在晚近顯露出分裂的跡象。實用主義的重組呈現出古典與新古典實用主義之間分離的特征:一方面是繼續發展皮爾斯、威廉·詹姆士與約翰·杜威的后笛卡爾式、反基礎主義趨向;另一方面則是在新弗雷格式語義學認知方法(或許稍早的C.I.劉易斯以及當代的布蘭頓對之有最佳闡述)中,出色地回歸向基礎主義或與之關聯密切的替代形式。①參見Robert Brandom, Between Saying and Doing: Towards and Analytic Pragmat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也參見Joseph Margolis, “A Pragmatist among Disputed Pragmatists: Robert Brandom’s Between Saying and Doing: Towards an Analytic Pragmatism”, in Contemporary Pragmatism,6 (1), 2009, pp.183-195。
不斷增加的分析性新實用主義者名冊中還包括一系列也被視為最優秀的分析哲學家的人物,這取決于研究者怎么劃分。比如,奧圖·紐拉特(Otto Neurath)、魯道夫·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劉易斯、奎因、普特南、羅蒂以及當代的布蘭頓和胡·普萊斯(Huw Price)。其他有時被列為實用主義者的分析哲學家包括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唐納德·戴維森(Donald Davidson)以及古德曼(Goodman)。
雖然未以其名,但古典的美國實用主義以人類實在的認知建構為特征。這一運動起源于皮爾斯對于笛卡爾式基礎主義的批判,這使他試圖提出一種后基礎主義的知識路徑。皮爾斯標志著這一運動的興起,在他之后,該運動在轉向分析哲學之前經歷了詹姆士真理學說中皮爾斯對于知識關切的衰落甚至消失以及杜威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這些循環流轉,并且可能由于各種意圖或目的而早早終結于羅蒂實用主義懷疑論的新分析實用主義形態中。有待觀察的是,羅蒂之后的新分析性實用主義是否會在布蘭頓的推理主義語義學中得到復興?
與索爾仁尼琴發表研究蘇聯古拉格的著作以來一直在衰落的(除卻由于2008年大衰退帶來的情況改善)馬克思主義不同,一般意義上的實用主義(雖然或許不是影響極深的羅蒂分析性實用主義)當下依舊處于上升地位。很大程度上受羅蒂的影響,以及認為分析進路的英美哲學越來越走入歧途這一廣為接受的信念,20世紀最后20年見證了哲學向實用主義的強勢回歸。直至20世紀末,實用主義似乎位列20世紀四大盛行哲學思潮(馬克思主義、歐陸現象學、美國實用主義、英美分析哲學)之首。可是其全面的盛行與其說意味著實用主義的繁榮,倒不如說表露了這一由皮爾斯嚴肅開啟、詹姆士與杜威進而加以消解的運動正走入歧途。除卻歐陸思想家,所有人看上去要么主張自己是實用主義者,要么曾被一位或幾位研究者歸于實用主義者之列,但越發令人迷惑的是,這些聲稱是實用主義者的人(如果有的話)共享著何種特征?
該議題在晚近所謂的分析性實用主義的興起中浮現。皮爾斯與詹姆士有關如何使用這一術語的有名論戰,說明沒有人能夠壟斷對于“實用主義”的正確描述。但是一些自稱的分析性實用主義者們似乎只與實用主義(無論如何界定)有極為微弱的關聯。這其中包括曾在光輝的一瞬間身居實用主義乃至哲學的核心人物的羅蒂。他看似無處不在地發掘實用主義;而他先前的學生布蘭頓與他不同,布蘭頓確實是無處不在地發掘實用主義。或許,實用主義者與新近自稱是實用主義者的分析性實用主義者,乃至對于皮爾斯所感興趣的基礎主義的拒斥之間的主要差異,是對認知建構主義和巴門尼德實在論之間的區分所做出的回應。
羅蒂與布蘭頓可能都持有非實用主義式的認知方法。在羅蒂看來,認為認知要求把握實在之物的觀點不過是老生常談,這像其他許多觀念一樣讓他走向了懷疑論。對布蘭頓而言,羅蒂的觀點是正確的,不過我們通過一種形式語義學方法—有時也被稱為指涉(或推理主義)語義學等—而事實上把握了實在之物。羅蒂借助的相對非形式化的方法以及布蘭頓使用的更加形式化但與之相關的方法都拒絕了皮爾斯和杜威所使用的建構主義方法。后者可以說是古典實用主義的典型方法,但對分析性實用主義而言卻并非如此。就此層面而言,問題不在于羅蒂的認知懷疑論和布蘭頓對于認知問題的形式語義學解決方案是否是可能的認知路徑,而在于即使作寬泛理解,它們是否可以算作整體實用主義方法的正當形式相比于大部分哲學思潮,實用主義都堪稱形態多樣,因而難以描述。更困難甚至不可能的是提出所有研究者都接受的實用主義定義,更不用說對之加以描述了。拉夫喬伊(A.O.Lovejoy)這位出色的研究者因提出多達13 種實用主義變體而著名。①參見A.O.Lovejoy, The Thirteen Pragmatisms and Other Essay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1-29, “Thirteen Pragmatisms”。詹姆士在哈佛大學的同事喬塞亞·羅伊斯(Josiah Royce)對德國觀念論極為熟稔,在他看來,觀念論者就是研究者們在20世紀初期稱作實用主義者的那些人。②參見Josiah Royce, Lectures on Modern Ide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Press, 1964, p.85。羅伊斯或許將“觀念論”與“實用主義”錯誤地等同起來,在寬泛但依舊是有限度的意義上使用了后一個詞匯。其他學者則不受此類似局限,他們走得更遠。羅蒂在非常寬泛的意義上使用“實用主義”一詞,在他看來,不僅戴維森就連尼采也是實用主義者。③比如可參見Richard Rorty, “Nietzsche, Socrates and Pragmatism”, in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0 (3),August 1991, pp.61-63; “Nietzsche: un philosophe pragmatique”, in Magazine Littéraire, April 1992,pp.28-32。布蘭頓對于這一詞匯的使用甚至更為寬泛,以至于似乎沒有誰不為其所涵蓋。比如,他不僅將這個詞用在奎因身上,還用在邁克爾·達米特(Michael Dummett)、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甚至弗雷格身上。④參見Robert Brandom, Articulating Reasons: 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還有一些學者甚至將“實用主義”標簽貼在歐陸哲學的主要人物身上,比如馬克·奧克倫特(Mark Okrent)就將海德格爾解釋為先驗實用主義者。⑤參見Mark Okrent, Heidegger’s Pragmatism: Understanding, Being, and the Critique of Metaphysic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對此解釋的反駁,可參見 Hubert Dreyfus, Being-in-the-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 Division I。
3.皮爾斯與認知建構主義
有必要加以評述皮爾斯與觀念論的關系。皮爾斯興趣廣博,其著述涵蓋眾多領域,其中就包括觀念論。①參見皮爾斯對于如下詳細的書評,“Fraser’s The Works of George Berkeley”, in The Essential Peirce,vol.I, 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 pp.83-105。他對于主要由他締造的美國實用主義的巨大貢獻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他拒絕了笛卡爾式基礎主義這一主要抑或依舊是最有影響力的現代知識路徑;另一方面,他勾勒了完全基于實踐的非笛卡爾式、后基礎主義的建構主義知識學說。
皮爾斯對康德與黑格爾尤感興趣。他逐漸將康德視為一位令人困惑的實用主義者,他說:“康德(我對他分外尊崇)就是一位有些令人困惑的實用主義者。”②Justus Buchler (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New York: Dover, 1955, p.299.并且他越來越強調他同黑格爾之間在擴展卻依舊有限的共識。皮爾斯強調認知是一個過程,但與黑格爾不同,他未能以歷史性的語匯對之加以描述。在對笛卡爾的批評中,皮爾斯檢驗并拒絕了康德知識構造形態的一種早期形式(該形式將知識視為一系列有關經驗可能性的必然為真的主張),以及不可因之后發展而受到修正的知識。
皮爾斯對于笛卡爾的批判說明,基礎主義認知模式是對我們如何展開認知過程的完全錯誤的描述。正因為如此,他不認為基礎主義是獲得知識的適切方法,必然為真(apodicticity)也并非認知標準,并且也否認了將知識等同于形而上學實在論的一切努力。他提出一種更為靈活的知識方法以取代熟知的笛卡爾模式,在這種方法中科學的進步依賴于推理的進步。皮爾斯并沒有承認一種終極的科學觀念,他認為科學史的每一階段都體現了該階段所基于的推理類型的不足。③參見“The Fixation of Belief”, in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I, 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 p.111。
在他起始于1877年的一系列開創性文章中④參見Ibid., pp.109-123。,皮爾斯關切被理解為通過信念克服懷疑的研究(inquiry)⑤The Essential Peirce, vol.I, 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 p.132.。皮爾斯通過權威、固執(tenacity)和先天性(apriority)的方法與科學方法的對比展開討論,后者是面對在經驗中被給予的實在時唯一能夠產生信念的方法。①參見The Essential Peirce, vol.I, 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 p.120。皮爾斯認為,邏輯的首要任務就是澄清我們的觀念。②參見“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in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I, 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 p.126。在澄清其信念的含義后,皮爾斯指出信念引發了行動的習慣③參見The Essential Peirce, vol.I, 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 p.128。,或面對事物的一種方式。通過擴展這一觀點,皮爾斯在一段常被引用的極為重要的段落中寫道:“思考一下,我們視為自己觀念的對象可能具有哪些有實用價值的效果。這樣,我們對于這些效果的觀念,就是我們對于該對象觀念的全部。”④Ibid., p.132.
皮爾斯在此提出一種普遍的意義觀念,它將使用價值或實踐中的效果等同于我們所說的對象。他很快將這一通過實用效果理解一個對象的理論同實在的觀念聯系起來。在他看來,“必然被所有研究者同意的觀點,就是我們所說的真理,而此觀點表征的對象就是實在”⑤Ibid., p.139.這一觀點影響了杜威。杜威認為:“我所知的從邏輯角度對于真理的最佳定義源自于皮爾斯:‘必然會被所有研究者同意的觀點即是我們所說的真理’。” John Dewey,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38, p.58.。皮爾斯拒絕了任何將實在之物視為知識對象的努力,而支持如下替代性有效(operational)理論,即將最終源自研究過程的任何事物視為實在。
根據我們如何解釋皮爾斯,他與黑格爾的認知理論可以是一致或幾乎一致的(雖然其表述語言有很大差異),也可以完全相反,即兩者是非常不同的。對黑格爾而言,知識問題是古代巴門尼德思維與存在同一問題的變體。與巴門尼德非常類似,黑格爾將主體與客體在本體論上的差異同兩者認識論上的同一結合在一起。知識并不涉及事物之所是,而只關切意識中呈現出的內容。當我們對于認知對象(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墊子上有貓”)的觀念同經驗中顯象的內容不再有任何差別時,我們可以說獲得了知識。⑥參見“The Probability of Induction”, in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I, 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 pp.167-169。用康德的語言來表述就是,認知是克服我們對于一個對象的表象和我們對于一個對象的經驗之間的差異。不過當我們獲得知識時,我們并不知道我們獲知了獨立于心智的實在。我們也不知道我們通過意識經驗獲得的知識,如何同任何可能或不可能存在于意識之外的事物相關。因此,黑格爾并沒有主張我們獲知獨立于我們之實在的本來面目,而是提出一種普通的主張,即知識僅局限于我們的經驗內容之中。黑格爾將知識理解為一種過程,以此我們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有關經驗內容的知識。知識的過程由形成前后相繼的更好或“更豐富的”(即有更強解釋力的)有關經驗內容的理論,它們進而受到實踐或之后經驗的檢驗。
在《如何使我們的觀念清楚明白》(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一文中,皮爾斯提出了一種我們熟悉的有關實在的理論,即實在本身的屬性獨立于任何人的思維并且作用于我們而使我們產生信念。對皮爾斯來說,通過運用最盛行的科學方法,我們能夠獲得我們認為的實在。這一科學方法假定研究會指向唯一共享的理論或所謂預定的中心(destined center)。對于我們的知識是否為關于實在的知識,皮爾斯的觀點是模糊的,而且再多的詳思慎查也無法澄清這一模糊之處。即便遵從善意的解釋,皮爾斯似乎也從未最終確定他有關實在的概念。
在皮爾斯看來,我們證立了實在符合于我們的理論這一信念,因為長期以來的科學研究圍繞如下觀點形成了共識,且我們不知道該觀點是否或如何與世界之所是相關:“但真實的實在卻依賴于這樣一個真實的事實,即研究只要足夠長久地繼續下去,最終注定會達到對于實在的信念。”①“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in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I, edited by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 p.139.皮爾斯沒有主張真實決定了有關真實的正確信念,而是認為真實就是在研究過程的終點我們所相信的事物。換言之,我們同意我們所認為的真實是我們不知道且不可知的。
或許皮爾斯并沒有下定決心選擇自己最終立場,或許他因對于司各脫主義實在論的興趣而相信我們的理論會逐漸接近獨立于心智的實在之物。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它的觀點在當下討論中俯拾皆是但又不可辯護。如下兩個方面的主張存在差異:一方面認為后來的理論改進了先前的理論;另一方面認為我們能夠逐漸接近、了解世界本來的樣貌。前者是可辯護的而后者不能。前文中已經談到,相對論解決了牛頓力學的某些難題,但認為后來的理論更加接近實在之物是一種誤解。庫恩無疑正確地否定了如下觀點:后來的科學范式能夠更接近于被理解為把握世界之所是的真理。①參見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4.論普特南實在論的多重面孔
在當下,實在論自始至終依舊如哲學傳統早期那樣是一個鮮活的議題。在書寫這一時期的歷史時,普特南赫然成為我們時代最重要的實在論者。理由之一就是這位廣受尊敬的思想家有眾多標題包含“實在論”一詞的著作②包括如下著作:《實在論的多重面孔》(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自然主義、實在論與規范性》(Naturalism, Realism, and Normativity)、《表象與實在》(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具有人類面孔的實在論》(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實在論與理性》(Realism and Reason)、《實用主義和理性》(Pragmatism and Reason)。,更多的理由則是,比如在《三重繩索:心靈、身體與世界》(The Threefold Cord)一書中,實在論是其核心主題。
與羅蒂類似不過可能更為典型的是,普特南既是一位實用主義者也是一位分析哲學家。如前所述,實用主義緣起于對于認知基礎主義的否定。這一否定使得羅蒂走入認知懷疑論。在他看來,認知主張無法得到證立,因為無法證明表象的精確性(這是我們認為正確的),甚或無法了解表象如何同世界相關聯。不過羅蒂并不覺得這一立場有問題,因為“在我們理解信念的社會證成時,我們理解了知識并因此沒有必要將之視為表象的精確性”③參見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70。。羅蒂似乎與許多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概念獨裁的社會,雖然兩者背后的原因并不相同:馬克思主義者立足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而羅蒂顯然立足于行為主義。他認為知識主張取決于并因而反映了社會讓我們述說的事物。①羅蒂認為這一觀點源自維特根斯坦和杜威,參見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174。羅蒂終生致力于否認知識的存在,并以我們無法證明表象的精確性為理由而捍衛懷疑論立場。普特南曾有一段時間與羅蒂一致,也承認表象實在的困難,這是其內在實在論或拒絕形而上學實在論的基礎。他正確地指出(而羅蒂卻沒有),重要的替代性理論在于表象人類的實在。
這一觀點顯然與羅蒂對皮爾斯的看法有關。許多研究者認為皮爾斯是最重要的實用主義者乃至最重要的美國哲學家。對羅蒂而言,他未講皮爾斯的一句好話,而認為杜威是實用主義者的核心。普特南沒有否認皮爾斯的價值,但對其著墨甚少,并認為實用主義主要同詹姆士和杜威相關。②參見Hilary Putnam and Ruth Anna Putnam, Pragmatism as a Way of Life: The Lasting Legacy of William James and John Dewey, edited by David Macarthur,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2017。換言之,對于羅蒂的最大化主義(maximalism),即我們無法把握世界,因此懷疑論無法避免的主張,普特南通過更為溫和的最小化(minimalist)主張加以解答。如羅蒂不自覺地追隨康德觀點所言,我們無法成功地理解世界,但我們至少可以理解人類的世界。
由于另一個原因,羅蒂和普特南的實用主義觀點之間的差異更加有趣。本文討論對于巴門尼德知識學說的回應。“在世哲學家文庫”(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普特南卷中,有一篇羅蒂回應普特南《回應羅蒂》(Response to Rorty)一文而撰寫的《普特南、實用主義與巴門尼德》(Putnam, Pragmatism and Parmenides)。③參見The Philosophy of Hilary Putnam, edited by Randall Auxier and Douglas Anderson, LaSalle, IL: Open Court, 2015, pp.863-882, 883-891。在該文中,羅蒂大體上改變了主旨。他花了大量篇幅討論布蘭頓、很少篇幅討論杜威,同時對他提及的巴門尼德或普特南則幾乎未加著墨。羅蒂認同海德格爾觀點,認為巴門尼德引入了一種與所謂的“超實體”(superthing)存在關聯的觀點。他是某種意義上的黑格爾愛好者,認為普特南因為依舊認同“確定的結果、范導性理念和縹緲的極限概念(Grenzebegriffe)”而犯了一種支持殘余康德主義的錯誤。④參見Ibid., p.878。普特南的回應(由于出現在羅蒂逝世后,因而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回應)包括兩個主張:第一,我們無法通過證立而證明(cash out)一個認知陳述。這與他在《理性、真理與歷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一書中持有的立場一致。第二,其有關世界的主張(附帶說明的是,如果我們將世界理解為人類的實在而非實在本身)描述了“那個我們通常能夠成功感知和理論表述的世界”①參見The Philosophy of Hilary Putnam, edited by Randall Auxier and Douglas Anderson, p.888。。不過尚不明確的是“成功”在此語境中指的是什么。
在普特南漫長的學術生涯中有關實在論的著述非常廣泛。他早年的許多最為重要的論文都與之相關,后期的許多論文也與實在論有關。在最近的一本文集的第二章,即《從量子力學到倫理學然后再返回》(From Quantum Mechanics to Ethics and Back Again, 2012)中②參見Hilary Putnam, Philosophy in an Age of Science, edited by David Macarthu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51-72。,他重述了已在1975年出版的首部論文集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主題。現在他聚焦于他思想的轉變,即從他的“內在實在論”或他現在稱作“反實在論時期”向他之后稱為“常識實在論”(commonsense realism)的轉變。③參見Ibid., p.x。
普特南在漫長學術生涯中研究實在論的不同層面,同時又經常轉變自己的立場。如果像康德所否認而普特南所接受的那樣,無法為哲學問題提供終結性解答也即答案的話,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努力表達一些有用的見解。④參見Hilary Putnam, Representation and Realis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8, p.xii。由于他的興趣的持續發展,在普特南實在論立場表面上的不連續性中很可能蘊含著一種深層次的統一。盡管他從未提出一種大一統的實在論學說,但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他提供了許多(如果該大一統分析得以成立時)顯然屬于實在論的因素。
作為一種實在論,普特南的實在論也有諸多變體。在不同的時期他分別對形而上學實在論、科學實在論、所謂的內在實在論、直接或非中介的實在論以及其他許多實在論形式感興趣。在他之后的著作中,他在不同時期又陸續提出一系列不同類型的實在論。
普特南跟隨漢斯·賴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這位重要的科學哲學家和邏輯經驗論者學習并受其影響。普特南堅定地認同科學實在論,他認為后者是科學理論所表述的核心觀點。他一直將科學實在論大體上理解為如下觀點,即成熟的科學理論基本上是對事物之所是的真實描述。
不過普特南雖然熟稔科學和數學,他卻是科學主義的堅定反對者。他在許多著述中明確表達了這一反對,包括在1975年的早期陳述,中期重述①參見Hilary Putnam, Renewing Philoso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x。,以及在此基礎上他學術生涯后期的重述。普特南在2012年引用他1975年所寫的一篇文章時強調,在其生涯中他一直認同科學是重要卻非唯一的知識來源。他寫道:“顯然我認真地看待科學,并且我將科學視為人類對于實在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尚有一個我希望不會被與之等同的傳統,它會認為科學知識是人類知識的全部。”②Hilary Putnam, Philosophy in an Age of Science, edited by David Macarthur, p.52.
就知覺(perceptions)問題來說,普特南認同所謂的直接或非中介實在論,又或同樣是知覺直接認知外在世界的立場。與此立場一致,比如在《三重繩索》一書中,他進而認為存在著精神性表象而且感覺素材或心智與世界之間的其他中介并不存在。③參見Hilary Putnam, The Threefold Cord: Mind, Body,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不過在2012年他拒絕了上述立場的進一步認同,而支持所謂的“相互影響論”(transactionalism)。這大體上是如下觀點,即知覺既依賴于環境也依賴于進行感知活動的個體,換句話說,知覺依賴于我們是誰或我們的本性,也依賴于環境。④參見Hilary Putnam, “How to Be a Sophisticated ‘Naive Realist’”, in Hilary Putnam, Philosophy in an Age of Science, edited by David Macarthu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635-639。與在《三重繩索》中發展的學說一致,普特南此時認為這樣一種相互影響會進一步涉及感受性(qualia)。感受性或感覺(sensations)通常被理解為主觀意識經驗的個體化實例,而該主觀意識經驗則被普特南理解為“感覺經驗的現象性特征”⑤參見Ibid., p.624。。這顯然意味著他認同以人類經驗為中心的實在論觀念。
我們如何評價這些有關實在論的一系列不同理論?第一種可能是,令許多研究者感到困惑的普特南實在論立場,隱隱地反映出實在論爭論令人困惑的狀態。第二種可能是,普特南對于實在論理解的淺薄使得每當他在研究中更進一步深入實在論的諸多層次時,他就改變了自己的觀點。第三種可能是,他在實在論爭論中所做的努力,展示出他在細分實在論爭論不同層面時令人欽佩的能力,但在將不同線索融合為一個整體理論時力有未逮。
值得注意的是,普特南與羅蒂一樣,是晚近實用主義分析陣營的領軍人物。羅蒂作為認識論懷疑論者與蘇格拉底遙相呼應,否認我們能夠獲得我們知道我們不知道以外的知識。如果獲知實在與獲知人類的實在這一區分能夠適用于普特南的實在論學說,那么很明顯他并非是笛卡爾式或早期康德式的表象主義實在論者,而是一位認同一種基于或局限于人類經驗的實在論的非表象主義實在論思想家。在此意義上,他同對他著作影響巨大的卡爾納普相類似。兩者的差別在于,普特南并未提出人類對于認知對象加以建構的學說(無論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也未指出人類經驗和科學實在論之間的連續性。但是在普特南看來,他曾經頗具影響而推介的內在實在論由于人類顯然無法把握或體驗實在本身而破產,所以他就無法再持有任何形式的古典或形而上學的實在論了。
5.認知建構主義與新實在論簡論
有必要簡述一下尚處于萌芽狀態的所謂的新實在論。新實在論是一股涵蓋廣泛卻大體而言算是方興未艾的思潮,它包括昆汀·梅拉蘇(Quentin Meillasoux)、馬庫斯·加布里埃爾(Markus Gabriel)、毛里奇奧·費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格拉漢姆·哈曼(Graham Harman)、雷·布拉西耶(Ray Brassier)以及伊恩·漢密爾頓·格蘭特(Iain Hamilton Grant)等人。
康德可以被解讀為基于其認知建構主義而將認知同一種相關主義(correlationism)關聯。新實在論大體而言是反康德的,它反對“相關主義”。當下新實在論的核心人物梅拉蘇將相關主義界定為“據此而言,我們只能獲知思維與存在之間的相互關系,而無法獨立獲知它們中的任何一個”①Quentin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 translated by Ray Brassier, London: Continuum, 2009, p.5.。他否定了哥白尼革命,而試圖返回形而上學實在論中。他認為相關主義(或真正的康德式“哥白尼革命”)是當下思想的最大威脅,并因支持托勒密式反對公轉的觀點而進一步拒絕了當下思想中的人類中心主義。
在梅拉蘇看來,“這些考量揭示了康德以來現代哲學的核心概念似乎就是相關性。我們以‘相關性’說明如下觀念,即我們只能獲得思維與存在之間的相互關系,而無法獨立獲知它們中的任何一個。我們因此用相關主義來稱呼任何保有我們如此界定的不可超越的相關性的思潮。因此,很可能任何否定樸素實在論的哲學就會變為相關主義的一種變體”②Quentin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 translated by Ray Brassier, p.13.。
這一普遍主張可能是對否認樸素實在論觀點的描述,它們包括普特南的觀點以及與批判哲學無關的學說。由于并不存在恰當理解哥白尼革命的共識,因此康德觀點不能被視為既定的,且其與相關主義之間存在的如梅拉蘇理解的關聯仍有待證明。一般而言,像后現代主義者們想要否認的那樣,新實在論者、思辨實在論者(speculative realists)以及傾向于其立場的同情者顯然更善于表明他們拒絕與接收什么,但還不太能夠對其中任何一種觀點形成論證來加以證明。
四、總結:巴門尼德之后的實在論與觀念論
本文在哲學傳統背景下討論一般性知識問題的不同方面。我們已經指出,這一問題源自古代巴門尼德認為知識是思維與存在的同一這一主張。我們進而論述了在證明知識取決于認知世界這一盛行的觀點中,沒有取得絲毫進展。最后我們提出了建構主義替代方案的旨趣。簡言之,這是一種認為我們知道且僅能知道我們所建構之物的現代理論。雖然未以其名,但認知建構主義廣泛見諸整個現代討論。未來解決知識問題取得的進步可能源自在巴門尼德的進路中對于認知建構主義的改進。
我們可以評述觀念論和實在論這兩個通常被理解為彼此不相容立場的關系來總結本文。那些抱持實在論而通常否定觀念論或建構主義立場的學者,往往由于誤解而對其所拒絕的觀點只有膚淺的把握。因此,晚近的一個例子是羅蒂這位非常著名的否認知識可能性的認知懷疑論者,被抨擊為是一位認知建構主義者。①參見Paul Boghossian, Fear of Knowledge: Against Relativism and Constructiv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將觀念論視為反實在論加以拒絕是誤解了觀念論、實在論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因為一切認知方法都是實在論的,不同的認知方法只是在它們所支持的實在論類別上有所不同。“觀念論”一詞只是在18世紀早期由萊布尼茨開始使用,但其內容要比該詞匯更為古老。在最早將觀念論視為一種哲學學說時,萊布尼茨這位德國思想家認為觀念論和唯物論是彼此相容的學說,它們至少在原則上能夠被綜合到一種單一立場。在回應皮埃爾·貝勒(Pierre Bayle)時,萊布尼茨反對“像伊壁鳩魯與霍布斯這些認為靈魂是物質的人”,并補充說在他的觀點中“無論在伊壁鳩魯和柏拉圖的假說中有何種善好、在最偉大的唯物論者與最偉大的觀念論者中有何善好,都被包括于此”②G.W.Leibniz,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edited by C.I.Gerhardt, Berlin: Weidmann, 1875-1890, vol.4, pp.559-560.。如果柏拉圖如同萊布尼茨所認為的那樣,是位觀念論者,那么觀念論或至少是某種形式的觀念論是與形而上學實在論相容的。不過這是一種特殊情況。
現代觀念論是建構主義式的,通過認知對象的建構而開始努力證明一種替代性的知識學說。雖然觀念論放棄了形而上學實在論,但它沒有否定實在論。如果“實在論”要求認知世界,那么沒有一種已被提出的理論提供了滿意的回答。因為我們沒有且無法獲知世界,而只能獲知在經驗中被給予的世界。相反,如果“實在論”意味著“經驗實在論”,那么經驗實在論和觀念論就是相容的,因為包括康德在內的觀念論者,沒有一位否認有關經驗性實在之物的知識。觀念論有許多種,比如,康德觀念論與實在論相容。康德的批判哲學依賴于實在或物自身,或換句話說依賴于外在世界的存在(雖然他否認我們能夠獲知這個世界)。這就說明萊布尼茨是正確的,即觀念論和實在論并非不相容而是彼此相容的,因為康德的批判哲學(引申來說,現代觀念論)并不否定而是依賴于外在世界的存在,因而也依賴于實在論。我的結論是,至少某些形式的觀念論和實在論是相容的,并且因為觀念論與實在論不相容而對觀念論產生的實在論式普遍敵意源自一種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