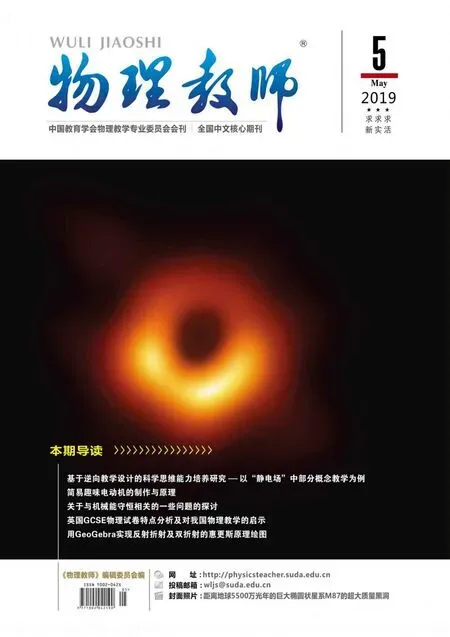無盡的追問
——緬懷杰出的核物理學家王淦昌先生
田 川
(重慶市第八中學校,重慶 沙坪壩 400030)
1998年12月25日,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禮堂.著名核物理學家、我國核科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王淦昌(圖1)院士的告別儀式在這里舉行.作為我國科技工作者中的杰出代表,他是我國原子核物理(兩彈)、宇宙射線、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在70年科研生涯中,他始終活躍在科研前沿,辛勤耕耘,孜孜以求,奮力攀登,取得了多項令世界矚目的科學成就.而他91年輝煌人生歷程的起點,還需從江蘇常熟的一個小村莊說起.

圖1 王淦昌
1 心懷岳武穆,漫漫求學路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蘇省常熟縣一個叫楓塘灣的小村莊,作為當地一位名醫老來的親生獨子(父親收養了兩位義子),幼年的王淦昌深受家人疼愛.但世事難料,4歲時,父親離世.父親在世時,每年在“義莊”舉行對貧困戶的捐贈活動,父親去世后,母親繼續做,使得這種捐贈活動從未間斷. 王淦昌所具有的諸如富有正義感、社會責任感、堅持原則、清正廉潔、謙虛質樸、平等待人、獎掖后進、助人為樂的高尚人格無需遠溯,只需從王淦昌的父母身上就可以看到這些品質的淵源.
1913年,6歲的王淦昌被母親送入私塾.兩年后,卓有遠見的母親又將王淦昌送到太倉縣的一所新式學堂,王淦昌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19年,五四運動的浪潮襲來,王淦昌也參加了游行,王淦昌晚年回憶這段往事,仍記憶猶新、頗為激動,他說:“這是我第一次上街游行,那時還小,只覺得能為國家振興出點力就是光榮,我從小就立志要做岳飛那樣的人.”1920年,小學畢業的王淦昌遠赴上海求學,就讀浦東中學.1925年,報考清華大學.或許是上蒼的安排,1925年清華正式開始招收大學生,就這樣,王淦昌成為了清華大學的首屆大學生.王淦昌在第一學期的普通課程學習中迷上了化學.由于對化學的濃厚興趣,王淦昌原本想選化學專業.然而旁聽葉企孫教授的一堂課,卻使他最終選擇了物理.
進入物理系后,師從吳有訓先生.吳有訓先生常常對學生說:“實驗物理的學習,要從使用螺絲刀開始”.1929年6月,王淦昌從物理系畢業,吳有訓邀請他留下來做助教,同時給了他一個研究課題《清華園周圍氡氣的強度及每天的變化》.王淦昌無論刮風下雨,一天不漏,每天都認真測量各項指標,一絲不茍,這項科學勞動持續了半年之久.吳有訓對王淦昌出色的工作和實驗結果十分滿意,親自把論文譯成英文,還把論文題目改為《北平上空大氣層的放射性》發表在清華大學論文集第一期上,這是清華大學第一篇用實驗報告形式所寫的論文.[1]年輕的王淦昌在葉企孫、吳有訓這兩位導師的指導下,用智慧和勤奮,扣開了核物理學之門,從此,踏上了獻身科學的漫漫之旅.
1930年,王淦昌考取江蘇官費留學,赴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德國居里夫人”的邁特內(Meitner).王淦昌在德國留學的四年是近代物理發展的黃金時期.1931年玻特(Bothe)發現一種很強的貫穿輻射,玻特認為是γ射線.王淦昌對此提出質疑,并提出如果改用云霧室做探測器,有助于弄清這種輻射的本質.遺憾的是王淦昌提出的實驗訴求被導師拒絕了.1932年查德威克就利用云霧室發現了中子,其實驗結果發表在2月17日出版的《自然》雜志.1935年查德威克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對此,邁特內曾沮喪地對王淦昌說:“這是運氣”.
1932年1月,王淦昌發表《關于RaE的連續β射線譜的上限》的論文.1933年7月14日,王淦昌又在德國《科學》期刊上發表了《γ射線的內光電效應》.由于太好學,常常深夜在大門已經上鎖后偷偷翻墻離開實驗室.1933年底王淦昌憑借論文《關于ThB+C+C的β譜》通過了以馮·勞厄(VonLaue)為主考的博士答辯.[2]1934年春,獲得博士學位后,便毅然選擇了回國.當時許多國外朋友婉言相勸:“科學沒有國界,中國那么落后,沒有從事科學研究的條件,你為什么要回去呢”.王淦昌回答道:“科學雖然沒有國界,但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我的祖國正在遭受苦難,她正需要我回去”.
2 輾轉西遷途,家國山河故
回國后的王淦昌先后在山東大學和浙江大學任教.由于年輕,人們親切地稱他為“Baby Professor”.“七七事變”后,浙大開始西遷,浙大西遷的路程是曲折的,先后換了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義、湄潭六處校址.歷經千難萬苦,還只能暫時安定,在宜山期間,教室都是大草棚,沒有凳子,教師就站著上,學生也站著聽,夜間自修沒有桌子,學生就趴在床上做習題.王淦昌將實驗室中的那一克鐳視為至寶,空襲警報響起時,什么東西都可以不帶,那個小鉛匣子必須揣在懷里.
在遵義期間,王淦昌的結核病加重,系里就讓他靜養,但王淦昌哪里閑得下來呢?這一期間他閱讀了大量國際權威物理期刊.由于進行前沿物理實驗的條件并不具備,因此他就給國際物理前沿研究出謀劃策,王淦昌形象地將其稱為——“搭橋”.
1943年王淦昌在美國《物理評論》雜志發表《關于探測中微子的一個建議》,同年該文被評為最佳論文之一.后來發現π介子的諾貝爾獎得主英國物理學家鮑威爾(Powell)的工作同《建議》相似.1945年王淦昌的《核力與重力的關系》、《中子的放射性》兩篇論文發表在當年的國際權威《自然》雜志上.[3]
抗戰結束后,1947年9月,全國選派了12名教授到美國做研究,其中就包括王淦昌.在不到一年的交流學習中,王淦昌就和瓊斯(Jones)合作發表論文《關于介子的衰變》.
1948年,鑒于在中微子方面做出的杰出貢獻,王淦昌獲得第二屆范旭東獎,第一屆獲獎者是侯德榜.
1948年底,竺可楨在杭州見到吳有訓時,談及王淦昌.竺可楨在當天的日記中寫到:“據正之(吳有訓)云,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出版《百年科學大記事》,中國人能名列其內者,唯彭桓武、王淦昌二人而已”.
3 茫茫戈壁處,核子化為菇
1950年4月中旬,王淦昌調到北京,與吳有訓、趙忠堯、錢三強、彭桓武、何澤慧共同著手籌劃“近代物理研究所”.1950年10月,經嚴濟慈介紹.王淦昌加入“九三學社”.同年參加川北新解放區的土改工作.朝鮮戰爭爆發后,王淦昌赴前線測定美國軍隊是否使用放射性武器.1952年10月,王淦昌從朝鮮戰場回國,開始主持制定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王淦昌調到所里主持宇宙射線研究,在他領導下1953年在云南落雪山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宇宙射線觀測站.
1956年赴蘇聯杜布納的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從事加速器研究.1959年王淦昌所帶領的研究組用動量8.3GeV/c的π-介子束作為入射粒子照射丙烷氣泡室后,在掃描得到的40000張氣泡室的照片中,于當年的3月9日,發現了一個反西格瑪負超子產生和湮滅的實例.同年的9月在基輔召開的國際高能物理會議上王淦昌宣布了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的事實.1960年3月24日,王淦昌正式將關于反西格瑪負超子的研究發表在國內的《物理學報》.同年蘇聯《實驗與理論物理》也刊發了此文.由于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1982年王淦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4]
1960年7月16日,赫魯曉夫發表照會,聲稱同年9月1日前將撤走全部在華專家.1961年4月3日王淦昌接受國家“爭氣彈”的秘密研究工作,從這一天起,蜚聲中外的王淦昌突然“消失”了.而這一消失就是17年之久.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一道強光閃過,伴隨著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大地驟然間劇烈地震顫起來,一顆碩大的火球轟鳴著、怒吼著,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吸起百米多高的沙塵,迅疾地托起滾滾翻騰的蘑菇狀煙云,向蒼天驕傲地呼嘯著,奔騰著,翻卷著…“成功啦!”“我們成功啦”.
1966年12月28日茫茫戈壁上又升起一顆美麗的“太陽”——我國在百米多高的鐵塔上,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1967年6月1日,通過飛機空投的形式,一朵蘑菇云再次升起.繼美、蘇、英之后,中國成為第四個掌握氫彈制造技術的核國家.
1963年,美、蘇、英3國簽訂了《關于禁止在大氣層、外太空和水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同年7月周恩來總理指示:研究地下核試驗.1967年10月,王淦昌和他的學生程開甲組織召開了我國首次地下實驗討論會,同年12月,核試驗轉入地下.在王淦昌的帶領下,科研團隊克服重重困難先后成功實現了三次地下核試驗.1976年年近七旬的王淦昌在風雪高原的大漠荒山中,在科研第一線組織了我國第三次地下核試驗.他還及時地檢測出洞內的氡氣,保護了隊員們的生命安全.通過三次地下核試驗,團隊獲得了寶貴的實驗數據,使得我國順利地攻克了地下核試驗的技術壁壘,保障了國家安全.
4 諾獎雖不渡,亦不悔當初
為了能夠清楚地看到核彈在內爆壓縮過程中物質變化的物理圖像,王淦昌促成了我國大型閃光X光機的研發,終于在1981年建成了強流脈沖電子束加速器,從此我國的閃光機躋身世界先進行列.科學家的貢獻水平,不僅僅在于他的科研成果,還在于他站得高、看得遠.跟蹤國際前沿課題,指導并預見科學發展的最新趨勢,王淦昌就是這樣的一位科學家.在王淦昌的建議下,中國核物理學會于1979年2月19日正式成立.
1879年3月31日美國三里島發生核電站事故,因此國內反核電呼聲高漲,王淦昌力排眾議極力促成了我國核電的建設.“九五”期間,我國核電建設呈現喜人形勢,一向謙虛的王淦昌自豪的說:“不是吹牛,核電站能有今天,是我盡力促成的.”
在裂變核能取得喜人成就后,王淦昌又把目光投向了聚變核能.王淦昌多次調研西南物理研究院研制的“托卡馬克”裝置.為了實現磁約束又間接地促成了激光技術的進一步飛躍.1984年12月王淦昌在《核科學工程》上發表了《慣性約束聚變研究的進展》一文,文中討論了“氟化氪激光及其應用”.[5]
1983年,美國針對蘇聯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歐洲也提出“尤里卡”(阿基米德泡澡后在街上高呼尤里卡,意思是找到了)計劃.為此1986年3月王淦昌又聯合一些科學家聯名向中央提出《關于跟蹤研究國外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同年11月,黨中央批文《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這就是著名的“863計劃”的由來.
1984年4月18日,在聯邦德國駐華使館,王淦昌接受了西柏林大學授予他的榮譽證書,以紀念他在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50周年.這個榮譽是為獲學位50年后仍然站在科研第一線的科學家而設立的.人們稱這樣的人為“金博士”.王淦昌是獲得這個榮譽的唯一的中國學者.
1987年年底,王淦昌與錢三強等25名著名科學家聯名報告國務院,提出《組建國家實驗室的建議》.
王淦昌隱姓埋名之后,有人曾為之遺憾.因為,王淦昌如果繼續在原來的科研領域工作,極有可能叩開諾貝爾獎的大門.然而,在王淦昌自己看來,與諾貝爾獎相比,祖國更加尊貴,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他說:“國家的強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
王淦昌雖然沒有獲得諾貝爾獎,但是他的學生李政道獲得了1957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幾十年后李政道還對浙大教授汪容說:“我在國內時受到三個人的幫助最大,即吳大猷、束星北、王淦昌三位先生”.[6]除了李政道,鄧稼先、程開甲等都是王淦昌的學生.
王淦昌始終不滿足于已經取得的成就,他常常引用牛頓的話:“我只是一個在科學大海邊撿貝殼的小孩”,并說:“牛頓尚且如此,我呢,充其量就是海水中的小水花而已”.
1996年4月,在原子能研究所內成立了基礎教育獎勵基金,王淦昌捐了3萬元.只要他的心臟還在跳動,他總是不辭辛勞地為各種事情忙碌,他的心總是想著祖國、想著科學、想著未來.
1998年12月10日,罹患胃癌[7]的王淦昌先生逝世于北京,享年91歲.
1999年9月18日,王淦昌被追授“兩彈一星”元勛.2000年春,攜手走過78個春秋(王淦昌13歲與吳月琴完婚)的王淦昌夫婦的骨灰合葬于故鄉常熟.2003年9月,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員會將1997年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王淦昌星”.2007年5月28日,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浙大都舉辦了王淦昌先生誕辰100周年的紀念活動.王淦昌先生的后人繼承了他的志愿,繼續耕耘在科學的園地.
“我愿以身許國”——王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