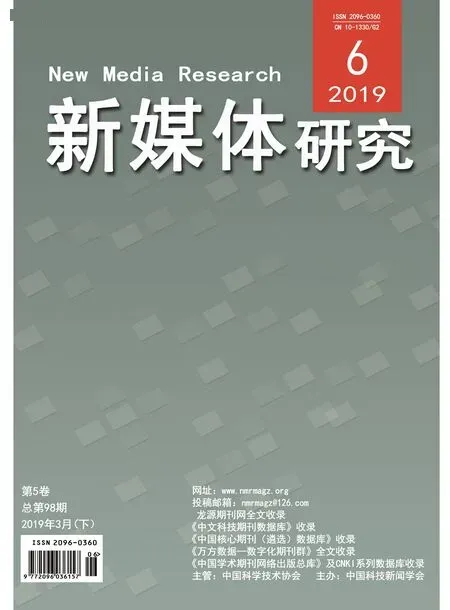新媒體用戶的社會交往心理研究
明珠
摘 ?要 ?當前,我們正處在“新新媒體”不斷涌現的時代浪潮中,作為用戶的我們擁有媒體的選擇權。文章旨在分析用戶在利用新媒體進行社交時的主要心理。
關鍵詞 ?新媒體;社會交往;用戶需求
中圖分類號 ?G2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9)06-0043-02
1 ?維系社會關系
1.1 ?延續現實生活中的社會交往——維護“圈層”
中國人的社會,是以“己”為中心的強關系的社會。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社會關系“這種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形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的論述準確且生動地解釋了中國傳統“圈層性”的人際關系。但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與城市化發展,我國社會的人際關系網悄然發生著變化,血緣與地緣不再決定一切。但我們的文化基因與社會基因終究沒有改變,我們依舊不斷維系著我們與生俱來的社會關系。
對這一種社交心理而言,新媒體只是現實生活中的“延伸”,為人際傳播增加了新的平臺。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與時間的不斷推移,很多傳統的社區、群體解散。但用戶可以在新媒體上重新聚集,將溝通的平臺從現實生活中轉移至虛擬空間,在這種虛擬空間內,多年未見的老同學可以暢所欲言,重溫美好時光,延續曾經年少時的“朋友圈”。
在微信朋友圈中,用戶編輯的內容是有對象性的,旁人無法知曉。所以無論是“秀恩愛”“炫富”還是“秀日常”,都是為了向身邊的親人、朋友展示自己的狀態,而他人則通過“點贊”這一行為表達“我在關注你”。
1.2 ?延伸現實生活中的社會交往——擴大“圈層”
在新媒體交流中,人際傳播關系也存在延伸性。這種延伸不僅表現在從熟人關系發展為新媒體線上交流的關系,也表現在從線上交際關系而發展為熟人交際關系。
對于后者,新媒體就是一種新技術,為我們提供機會去認識更多的人,營造了新的社交環境。傳統社交受到特定時空的限制,人們在社交對象的選擇上也十分有限,血緣與地緣基本上決定了一個人的圈子。新的技術則改變了這種情況,在新媒體社交中,我們能通過原本的朋友圈認識更多相關的人。例如:QQ時常為我們推薦與我們好友相關的陌生人,而新浪微博也專設“好友關注”一項,便于我們在熟人的基礎上擴大人際關系圈。
線上關系如果交往愉快也可以發展為線下關系。一些明星的粉絲后援會、網絡游戲聯盟的戰友,經常召開線下的見面會,“網戀奔現”也是線上關系發展為線下關系的代表。盡管用戶對于線上關系是否能順利轉為線下關系有自己的評判標準,但這種“限制”并不妨礙線上社交成為個體發展與維護社會關系的新路徑。用戶的線上交際關系和線下交際關系的相互延展,日常生活中,人們多有被他人邀請入群的經歷,這一舉措,就是典型的既是線下關系的延續,又是發展線上新關系的啟程。
2 ?從眾心理
媒體作為一種獲取信息的工具,在很多方面可以為受眾提供信息,這是媒體的首要功能。可如今,信息爆炸的時代。如何在海量信息中做出選擇?很多人面臨不知如何選擇的境遇時,會下意識地選擇從眾。從眾既是一種心理也是一種行為,它是基于人類的依賴感和歸屬感所形成的。
2.1 ?保持信息與渠道與他人的一致性
個體在受到群體的影響后,往往對自己的觀點、判斷和行為感到懷疑,甚至朝著群體大多數人一致的方向做出改變。所以當身邊的人都在使用一種新的媒體時,我們也將做出改變。若干年前,QQ的使用者數量遠高于微信,但很多人都因為身邊朋友使用微信的關系,不得不將自己的“關系圈”轉移到微信中。在一些人看到身邊人下載短視頻App并且時常上傳最新動態時,自己也會“跟風”注冊相關賬號,使自己躋身于和他人接觸相同事物的情境內、擁有與熟人在相同平臺進行對話的資格。
除了對多數人時刻保持對一些消息的敏感并不意味著對消息的興趣,他們只是為了保障自己“合群”。當身邊的人都在討論“今晚吃雞”“抖音小姐姐”“知否小公爺”時,如果自己不知道,則會有一種被孤立的感覺。人依賴群體,想在群體中找到歸屬感,所以無法接受自己“融入不進”的現實,于是開始用大家都在使用的App、打最流行的游戲、每天多次去看微博熱搜榜。
2.2 ?使用與群體相同的話語體系
在進行網絡社交時,除了保持自己的信息與獲取信息的渠道的一致性外。用戶也保證自己的話語體系與所在群體相同。最近在網絡流行的“我酸了”“你pick誰”“官宣”等詞被廣泛使用。在被眾多信息圍繞時,我們將傾向于最可能被大眾認同的那些。很多網絡流行詞一開始還不廣為人知,可一旦身邊有人使用,用戶就會嘗試去了解該詞的由來,為了達到更好的社交效果,也會開始使用。
以“我酸了”“檸檬精”為例,這2個詞流行于“飯圈”中,用于表達仰慕的明星與其他人(特別是異性)有交流時的羨慕導致自己酸成了一顆“檸檬精”,意思有些類似于“吃醋”。2019年春節聯歡晚會,相聲演員岳云鵬接到了青年偶像李易峰拋出的籃球,李易峰的粉絲紛紛在視頻下留言“我酸成了檸檬精”,這樣的評論占據評論的大多數。
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提到“孤立的他可能是個有教養的個人,但在群體中他卻變成了野蠻人”。在勒龐看來,群體是沒有理性的。而新媒體語境下的從眾,實質就是對群體情緒與群體觀念的認同,相同的話語體系就是群體情緒宣泄的表現之一。
2.3 ?無聲地從眾——沉默
沉默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同時也表達出用戶一種復雜的心情。沉默的原因有很多,在新聞傳播領域,“沉默”并不單單是指受眾對一件事情保持不評價的狀態,也代表著受眾是否敢說出自己內心最真實的想法。
第一種,“不知表達什么”。受眾在使用新媒體時,遇到與自己關聯較少的事件,常常會有“吃瓜”心理。例如2018年底出的“D&G事件”,很多微博用戶并不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單憑“辱華”二字便對該品牌大肆批評。這類事件還很多,反轉新聞在曝光之初,大家對事件并不了然的情況下,內心深處其實并不知道該表達什么。互聯網社交的門檻很低,人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如何用戶看見網絡上的“一邊倒”情況時,便瞬間了然,認為那就是自己的想法。于是為初具雛形的輿論“獻力”或是保持沉默。倘若這些意見無法成型,他們則會去找尋意見領袖,參考他們的意見和聲音。
第二種,“不知如何表達”。這一種情況與用戶的媒介素養有關,受眾想參與卻又沒有能力準確表達自己想法。新媒體并不能提高受眾的媒介素養,相反地,它加深了受眾的碎片化閱讀習慣,降低了受眾的理性思維方式。相比之下,傳統媒體更為客觀中肯的言論更有利于使群眾靜心思考事件的來龍去脈,而不是一味瘋狂地贊同實際上有失偏頗的觀點。“不知如何表達”造成的結果與“不知表達什么”一樣,用戶最終都會參考他人觀點,但是此時的用戶大致擁有自己的感性想法,所以他們會借鑒他們信任的意見領袖的意見。無論是網絡大 V還是主流媒體的聲音,他們都在話語權上擁有權威性。
第三種,“我知道,但不表達”。即使網絡擁有匿名性,但是隨著網絡管理的嚴格化規范化,人們在網絡上發言也只能是“戴著鐐銬跳舞”,每個網民固有的ID就像是一張身份證,讓人們無從躲避。
隨著網絡平臺的逐漸完善與大眾對新媒體的不斷熟悉,網絡與現實不斷聯動,這迫使人們即使在網絡虛擬平臺上發言也要謹言慎行,特別是發表與主流意見相悖的言論。用戶不僅要承受現實帶來的壓力,在網絡平臺上也要承受相對而言更加復雜的網絡群體壓力。只要言論表達不得當,質疑聲將如潮涌來,只剩下孤立無援的自己。
而在熟悉的新媒體圈子里,我們更無法任意表達自己的想法,在家族微信群中,被催婚的年輕人依舊敢怒不敢言,他唯一的權利就是沉默或是像日常生活中一樣虛假應和。
3 ?結束語
在新媒體社交中,既延續了中國傳統社交以地域與血緣為中心的特征,也為當代人提供了結交新朋友的途徑。在新媒體語境下,出現了線上社交與線下社交共同發展的情況。在這新舊交織的社交情境下,用戶的選擇更大,但他們最終的選擇主要是圍繞著維護社會關系和從眾心理來展開。
參考文獻
[1]王博文.目前微信朋友圈中的社會交往研究——以“師生關系”為例[J].傳媒論壇,2018,1(27).
[2]劉艷.基于微信傳播的人際交往研究[D].長沙:湖南大學,2018.
[3]周子云,鄧林.社交媒體人際傳播的三個特點[J].青年記者,2018(14).
[4]孫華.傳播學視閾下的雙十一樂隊花車效應[J].傳媒觀察,2017(2):3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