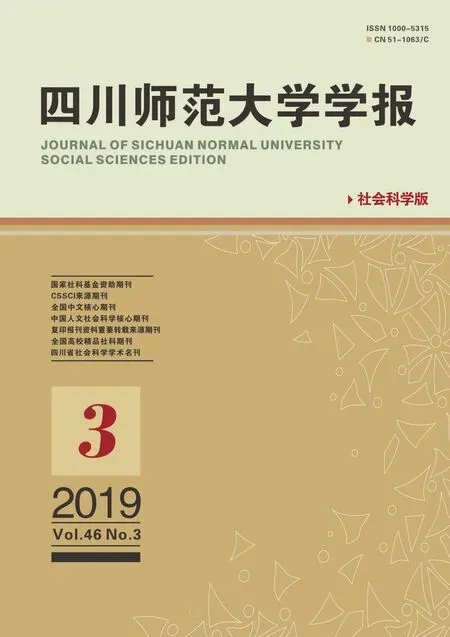我國憲法修正案的性質檢視:憲法文本的組成部分抑或修正指南?
(四川大學 法學院,成都 610207)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①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②。無論是從條數、字數還是從對于憲法文本的修改幅度來看,2018年憲法修正案都堪稱歷次憲法修正案之最,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其中的第五十二條不僅首次變動了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③的體例結構而且首次增加了它的總條數: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中增加了第七節“監察委員會”,同時增加了5條,《憲法》的總條數因而由先前的138條增至143條④。盡管如此,自我國1988年局部修憲產生憲法修正案以來,憲法修正案的性質卻一直不甚明確。實務界和理論界均尚未就如下問題形成相對統一的認知:憲法修正案究竟是憲法文本的組成部分抑或修正指南?
對于這一問題的探究涉及憲法文本的具體形態,但這一工作的意義并非僅限于形式層面。憲法修正案的定性關系到憲法文本的統一。若是將憲法修正案當作憲法文本的組成部分,現行《憲法》的標準文本當屬1982年12月4日公布施行的《憲法》⑤加上5次憲法修正案;如果將憲法修正案視為憲法文本的修正指南,現行《憲法》的標準文本即為根據歷次憲法修正案修正的《憲法》⑥。毋庸置疑,一國憲法典的文本應當是唯一確定的,這一點不應因局部修憲而發生變化。但在我國,面對前述兩個迥然有別的憲法文本,人們在閱讀和引用憲法典時難免無所適從,這自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現行《憲法》的權威。基于“認真對待我國憲法文本”⑦的立場,下文將從合法性和合理性兩個維度來審視我國憲法修正案的兩種定性。
一 作為憲法文本的組成部分
早在1999年局部修憲前后,我國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問題就已經引起了憲法學界的關注⑧。2004年局部修憲以后,憲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遭到了一系列批評。胡錦光教授提出:憲法“修正案不是對正文的直接修改,而是間接修改或者補充。因此,修正案應該可以作為獨立的條款予以引用”⑨[1]。這一觀點在我國憲法學界頗具代表性。若依此邏輯,我國的憲法修正案理應是現行《憲法》的有機組成部分,惟其如此,方才有可能作為獨立的條款得以引用。同時應當看到,對于“憲法修正案”的這一定性確實具有特定的歷史語境。
(一)作為憲法文本組成部分的歷史語境
在比較法層面,我國憲法學者對于我國憲法修正案的批評大多是以美國憲法修正案為參照的。因此,我們首先有必要回顧美國創設憲法修正案的具體方案。在世界范圍內,美國是第一個制定成文憲法典并施行至今的國家,不僅如此,該國也是第一個運用憲法修正案且踐行至今的國家。《美利堅合眾國憲法》⑩第五條使用了“amendments to this Constitution”這一表述,中文通譯為“憲法修正案”。但至于其具體形式如何,《美國憲法》本身未作任何規定。不論是在費城制憲會議上還是在各州討論批準該《憲法》的過程中,這一技術性較強的細節問題都未引起美國制憲者的關注。1789年6月8日,時值第一屆眾議院的第一個會期,眾議院議長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 Jr.)提出了9條憲法修正議案,即《權利法案》最初的草案。直到8月13日,眾議院方才對這些議案進行審議,同時就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問題展開了集中討論。而這一討論主要表現為“植入”(interweave)方案與“接續”(supplement)方案之爭。
所謂“植入方案”,即在憲法原文中直接植入新的內容,也包括直接變更或者刪去舊的內容。在該方案之下,憲法修正案是憲法文本的修正指南,憲法文本因修正案的通過而發生更替。這個意義的憲法修正案,類似于當今德國的“基本法修改法”或者法國的“憲法性法律”。麥迪遜本人即是“植入方案”的提出者。除了他以外,發言支持該方案的眾議員還包括史密斯(Smith)、瓦伊寧(Vining)、格里(Gerry)和哈特利(Hartley)。所謂“接續”方案,即在憲法原文之后,不斷接續憲法修正案,后來的修正案不復述或者提及憲法原文以及先前修正案的條文數和具體內容。依據后法優于前法的沖突規則,修正案得以取代與之不一致的憲法原文,后來的修正案得以取代與之不一致的先前修正案。在這種方案之下,憲法修正案是憲法文本的組成部分,憲法文本因修正案的通過而增加篇幅。羅杰·謝爾曼(Roger Sherman)明確反對麥迪遜提出的“植入”方案,同時提出了“接續”方案。發言支持“接續”方案的眾議員還包括利弗莫爾(Livermore)、克萊默(Clymer)、斯通(Stone)、勞倫斯(Lawrence)和杰克遜(Jackson)。雖然“植入”方案在8月13日的議事表決中占有一定優勢,但“接續”方案經過8月19日的討論卻得到了更多眾議員的認同(見表1)。最終,“國會決定這些修正案將被添加到文件的后面,而不是融入到原來的文件中”[2]118。至此,美國的修憲實踐最終確定采用“接續”方案。
表1.詹姆斯·麥迪遜提出的9條憲法修正議案

表1.詹姆斯·麥迪遜提出的9條憲法修正議案
議案順序涉及的主要內容修憲的最初方案修憲的最終結果第一主權在民原則在序言之前增加部分內容未成為修正案第二眾議員人數修改第1條第2款第3項未成為修正案第三眾議員薪酬調整在第1條第6款第1項第1句之后增加部分內容成為第27條修正案第四各種憲法權利在第1條第9款第3項和第4項之間插入部分內容部分成為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8、第9條修正案第五平等的良心自由以及出版自由和在刑事案件中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在第1條第10款第1項和第2項之間插入部分內容部分成為第1、第7條修正案第六普通法訴訟在第3條第2款第2項之后增加部分內容部分成為第7條修正案第七刑事程序權利修改第3條第2款第3項未成為修正案第八橫向分權原則、縱向分權原則以及各州保留權力在第6條之后插入部分內容,成為第7條部分成為第10條修正案第九憲法條文數的變更第7條改為第8條未成為修正案
由表1可知,在麥迪遜提出的9條憲法修正議案中,有相當一部分經采納最終成為《美國憲法》的一部分。與其設想不同的是,新的內容并未植入憲法原文當中,卻形成了10條憲法修正案,而憲法原文沒有絲毫變動。在麥迪遜等人看來,相對于“植入”方案,“接續”方案主要有兩個局限:其一,不便于確定和認知憲法文本的含義;其二,不利于保持憲法文本的體系。這些局限都是顯而易見的。其中,第一個局限是“接續”方案遭受詬病的最主要原因,它涉及憲法文本的實際效用,人們不得不前后比對相關的憲法條文才能確定特定憲法條文的含義。第二個局限涉及憲法文本的外觀形式,若將憲法修正案接續在憲法原文之后作為《美國憲法》的一部分,憲法原文之后的憲法條文則只能按照修正案的入憲時間排序,這些條文前后之間通常不存在內容上的邏輯關聯。
那么,“接續”方案較之于“植入”方案的優點何在呢?謝爾曼等人主要是從如下四個方面闡述的:第一,有助于保留憲法原文的整體結構;第二,有助于維系憲法文本的穩定;第三,有助于避免僭越人民制憲的權力;第四,有助于防止后世對憲法原文的誤讀。顯然,第一個優點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它要求憲法原文的整體結構基本合理,也要求修憲者對于憲法文本表現出足夠的尊重。第二個優點的提出,過于牽強。如若“憲法文本的穩定”是指憲法原文形式上的“穩定”,其邏輯便是:修正案的增加不會使憲法原文的文字發生任何變化;如若這一表述是指整部憲法典內容上的“穩定”,其邏輯則是:為了減少閱讀和引用憲法典的不便,人民將盡可能降低增加修正案的頻率。然而,局部不能等同于整體,憲法原文的恒定不能等同于整部憲法典的恒定;形式應當讓位于內容,方便閱讀和引用憲法文本的考慮也不能阻止對憲法文本的必要修改。第三個優點的提出,源自美利堅立國之初的特定觀念。其邏輯在于:憲法修正案所體現的是各州政府修憲的權力而非全體人民制憲的權力,若采用“植入”方案,各州政府便得以直接改變憲法原文,這就篡奪了人民的制憲權。可是,該邏輯將變動憲法原文等同于重新制憲,明顯不符合現代主流的制憲權、修憲權理論。第四個優點的提出,立足于美國憲法原文的文本細節。憲法原文最后一條即第七條之后有如下說明:“本《憲法》于美利堅聯合各州獨立后第十二年,我主第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經出席各州一致同意完成。我們謹在此簽名作證。”而各州參加制憲會議代表們的簽名緊接其后。因此,如果在變動憲法原文的同時保留這些說明和簽名,后人很有可能混淆憲法原文和憲法修正文本。但這個問題不難解決:可以考慮在憲法修正文本中刪去上述的說明、簽名或者加入修憲說明。應該看到,除了上述四個優點之外,“接續”方案還可以充分展現憲法文本的歷史演進。當然,第一屆眾議院討論該方案時,《美國憲法》僅施行數年,而且尚未修改,眾議員們自然無從獲知這一功效,更遑論以此來支持“接續”方案。
綜上所述,美國在制憲之時只是決定采用“憲法修正案”進行修憲,直到第一次修憲時才確立了“憲法修正案”的具體形式,從而選擇了“接續”方案。根據《美國憲法》第五條,經特定方式提出的憲法修正案,由特定數量之州立法機關或州制憲會議批準后,即成為該《憲法》之一部分而發生實際效力。據此,這個意義上的“憲法修正案”雖然獨立于憲法原文,但無疑是憲法文本的組成部分。
回顧美國創設憲法修正案的具體方案之后,我們有必要將理論視域移向我國,探究我國引入憲法修正案的最初設想。我國憲法原文本身并未明示通過憲法修正案進行修憲。但是,最遲至1988年首次局部修憲之前,修憲者們就此達成了共識。依據時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劉政的回顧,1988年2月27日,當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會議研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向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提出修改憲法案時,彭真委員長提出:“這次對憲法的修改采取修正案的方式,這是美國的修憲方式,比法國、蘇聯和我國過去的修改憲法辦法好。彭沖副委員長和王漢斌秘書長對實行這種修憲方式作了說明。采取這種方式,得到了委員長會議和常委會會議全體組成人員的贊同”[3]。而根據時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景宇的回顧,“修改憲法的方式,在當年制定憲法時就慎重研究過,確定采取憲法修正案的方式,這是借鑒美國修改憲法的辦法”[4]79。
盡管如此,上述回顧只是表明:1988年局部修憲時甚至現行《憲法》起草時,修憲者們曾經主張師法美國,采取憲法修正案的方式。至于他們是否贊成引入“接續”方案,即一并效仿美國憲法修正案的具體形態,筆者尚未發現相關史料可以提供直接的證明。結合1988年局部修憲的歷史背景與憲法學界的主流論說來看,修憲者們主張采用憲法修正案的主要考慮就是確保現行《憲法》的穩定,他們希望控制修憲的幅度,試圖避免產生新的憲法典。由此推論,“接續”方案相對于“植入”方案應當更加符合修憲者們的最初設想,原因很簡單:后一種方案必然催生出有可能取代憲法原文的憲法修正文本。另外,1988年局部修憲前后,官方并未要求編輯產生憲法修正文本,該文本也不曾在坊間流行。這一點也可以佐證上述推斷。但應當看到,1988年憲法修正案形似修憲指南,在具體形式上明顯區別于美國的憲法修正案。至于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了最初設想與實際做法之間的明顯出入,尚不得而知。
(二)作為憲法文本組成部分的現實困境
依據美國修憲實踐采用的“接續”方案,憲法修正案即為憲法文本的組成部分。盡管如此,無論是相對于其他國家的現行憲法典,還是較之于本國的聯邦法律和各州憲法,《美國憲法》在修改方式上都是極為特殊的。放眼全球,當前運用“憲法修正案”修憲的國家并不鮮見。然而,除了美國之外,這些國家基本上都將憲法修正案作為憲法文本的修正指南。換言之,就美國而言,“接續”方案早已確立并且一直在修憲實踐中得以應用。但從世界范圍來看,“植入”方案已然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既然美國是憲法修正案的“原產國”,那么他山之石為何難以攻玉呢?究其原因,采用憲法修正案并將其作為憲法文本的組成部分,是一種高成本、低收益的修憲模式。由于美國的憲法原文及其修改實踐極富個性,該國的修憲模式難以為絕大多數國家所復制。我國亦不例外。
如前所述,“接續”方案具有普遍意義的優點無非有二:一方面,有助于保留憲法原文的整體結構;另一方面,有利于展現憲法文本的歷史演進。但對于我國而言,它們的價值有限。我國現行《憲法》的體例結構頗為穩定,在2018年以前不曾發生任何變動。然而,隨著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以及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開,2018年局部修憲在第三章“國家機構”之下增加了“監察委員會”一節。由此觀之,調整這部“改革憲法”的原文結構正是改革本身的要求,但“接續”方案不變動憲法原文,自然無法實現這一結構調整,因而難以順應改革所需的憲法變遷。此外,《美國憲法》具有200多年的歷史,而我國現行《憲法》只有區區30多年的歷史。相較而言,我國憲法修正案的歷史認知功能目前是非常有限的。
比較中美兩國的憲法原文和修憲實踐可知,“接續”方案在我國不僅難以揚其長,而且無法避其短。該方案最為主要的局限莫過于:不便于確定和認知憲法文本的含義。換言之,對于閱讀和引用憲法文本而言,“接續”方案顯然不夠便捷。
第一,我國的憲法原文在篇幅上明顯長于美國的憲法原文。據統計,我國的憲法原文達16069字,而美國的憲法原文僅有6219字,前者在篇幅上是后者的2.58倍。其中,前者之“序言”在篇幅上更是后者之“序言”的23.56倍。實際上,美國的憲法原文加上憲法修正案總共也只有10457字,仍然明顯短于我國的憲法原文。不同于美國的憲法原文,我國的憲法原文不僅設有基本權利篇章,還包括篇幅較長的“序言”和“總綱”。在“接續”方案之下,人們閱讀和引用憲法文本時往往不得不比對憲法原文與憲法修正案。因此,憲法原文的篇幅較長,確定和認知憲法文本的含義就需要更高的時間成本,存在更高的出錯幾率。
第二,我國的修憲在頻率上明顯高于美國的修憲。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點可以歸因于:相對于美國憲法原文,我國憲法原文的篇幅較長,既涉及更多的問題,又包含更細的規定,其穩定性相對較低。如若面臨重要的改革,現行《憲法》就有可能需要修改。實際上,這部“改革憲法”本身就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改革的產物。自1788年批準生效以來,《美國憲法》共經歷18次修改,產生27條憲法修正案,以此計算,它平均每12.78年經歷1次修改,平均每8.52年產生1條憲法修正案。而自1982年公布施行以來,我國現行《憲法》共經歷5次修改,產生52條憲法修正案,以此計算,它平均每7.2年經歷1次修改,平均每0.69年產生1條憲法修正案。由此觀之,如果以每一次修改憲法所平均經歷的時間來度量,我國的修憲頻率明顯高于美國的修憲頻率;而若以每產生一條憲法修正案所經歷的時間來度量,我國的修憲頻率則更是遠遠高于美國的修憲頻率。而就憲法規范變動的幅度和憲法典增加的長度而言,第二種度量標準更有意義。綜上,相對于美國的憲法原文及其修正案,我國的憲法原文及其修正案更加不便于閱讀和引用。
第三,我國的修憲明顯更多地體現為對于既有憲法規范的更改。在我國現行《憲法》的52條修正案中,37條修正案只涉及憲法規范的更改,7條修正案同時涉及憲法規范的增加和更改,分別占比71.15%和13.46%。而在《美國憲法》的27條修正案中,只有3條修正案僅涉及憲法規范的更改,只有3條修正案同時涉及憲法規范的增加和更改,二者均占比11.11%。可見,在我國,閱讀和引用憲法原文及先前的憲法修正案時更有必要比對后來的憲法修正案。
那么,在“接續”方案之下,我國可否改變上述情況,從而實質性地提高閱讀和引用憲法文本的便捷性呢?這一做法不但是不可行的,恐怕也是不適當的。第一,作為歷史的范疇,我國現行《憲法》的原文是固定不變的,不可能縮小篇幅。第二,我國今后的修憲仍將保持較高的頻率。一方面,現行《憲法》的“總綱”一章比較全面地規定了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重要制度,其“國家機構”一章則比較詳細地規定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類國家機關。一旦面臨必要的重要改革或者重大政策調整,現行《憲法》就勢必要進行相應的修改。譬如,為了適應經濟體制改革,1988年、1999年和2004年三次局部修憲均涉及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地位和待遇。又如,為了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2018年局部修憲加入了有關“監察委員會”的5條并將它們單獨列為一節。另一方面,現行《憲法》的“序言”包含一系列宣示性較強而規范性較弱的規定,這些規定涉及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就和經驗。而從我國修憲的慣例來看,“序言”的有關規定在表述上一直與執政黨的章程和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保持較高的一致性。除了1988年局部修憲外,我國的歷次局部修憲均依照執政黨的特定權威表述對這些規定進行調整。在2018年3月5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晨提出:“我國憲法必須隨著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完善發展。……由憲法及時確認黨和人民創造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以更好發揮憲法的規范、引領、推動、保障作用,是實踐發展的必然要求。”[5]由此觀之,執政黨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將適時、適度地融入憲法文本當中,這已然是我國修憲的傳統和特色。第三,我國今后的修憲仍將更多地表現為對于既有憲法規范的更改。美國憲法原文很少涉及憲法權利,《權利法案》及其后的多條憲法修正案陸續將一系列重要的權利寫入《美國憲法》。基于此,美國的修憲更多地表現為增加新的憲法規范。而我國的憲法原文自公布施行之時就已包含體系化的基本權利篇章,這或許可以解釋我國憲法修正案為何較少“增加”新的憲法規范。此外,我國的修憲多次依照執政黨最新的權威表述而對“序言”、“總綱”中的提法和措辭進行調整,這一類修改均屬于對既有憲法規范的“更改”。對此,相較于“接續”方案,“植入”方案自然更加直截了當。
二 作為憲法文本的修改指南
就美國在世界范圍內創設憲法修正案的歷史語境而言,憲法修正案應當被定性為憲法文本的組成部分。然而,我國憲法修正案的性質畢竟應當與我國的修憲實踐相適應。既然如此,對于“憲法修正案”這一比較法范疇,我國的修憲實踐或許就可以取其名而舍其實,將其定性為憲法文本的修改指南。畢竟,中美兩國語境下的“憲法修正案”分別是以中文和英文表述的,將二者的意涵全然對等或許是翻譯上的“失準”。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比較權威的法學詞典,《北京大學法學百科全書·憲法學 行政法學》已經嘗試在兩種意義上界定“憲法修正案”一詞。根據其“憲法修正案”詞條,“少數國家采取憲法原文不變,而將憲法修正案附于憲法正文之后的做法,修正案直接成為憲法的有機部分,被修正的憲法原文自然失效,如美國就是如此。多數國家采取以修正案的文字替代被修正的憲法原文的做法,對憲法條款按修改后的格式重新編排、公布,我國就是采用這種做法”[6]514。依照這一表述,我國的憲法修正案應當被定性為憲法文本的修正指南,從而區別于美國的憲法修正案。事實上,我國的修憲實踐一直具有這一傾向。
(一)作為憲法文本修正指南的實踐傾向
正如前文提到的,較之于美國的憲法修正案,我國的憲法修正案在形式上更加類似于修憲指南。它們分為兩種類型:更改型修正案和增加型修正案。其中,第一類修正案具有比較統一的句式,即:原憲法條文數+原憲法規定+“修改為”+新的憲法規定。而第二類修正案則存在四種句式。第一種句式為:原憲法條文數+“增加規定”+新的憲法規定;第二種句式為:原憲法條文數+原憲法規定+“前增寫”或“后增加”或“后增寫一句,內容為”+新的憲法規定;第三種句式為:原憲法條文數+“增加一款(項),作為第×款(項)”+新的憲法規定;第四種句式為:憲法章數+憲法章名+“增加一節(條),作為第×節(條)”+新的憲法規定。其中,部分采用第三、四種句式的憲法修正案指明了相關憲法規定在條文數或者節數上的相應改變。上述句式無一不是直接在憲法原文中更改或者增加相關內容,客觀上引導讀者去閱讀最新的修正文本,此種做法當然更加類似于“植入”方案而非“接續”方案,有可能偏離了我國修憲者們借鑒美國修憲模式的最初設想。但應該看到,這種做法的確更加能夠適應我國的修憲實踐。增加型修正案或許可以相對輕易地效仿美國憲法修正案的具體形式,但更改型修正案卻不然。在美國的“接續”方案之下,若欲達成“更改”原規定的實際效果,憲法修正案一般不得不明示刪去該規定所在的整個憲法條款,而后再行增加新的相關規定。譬如,我國2004年局部修憲以“緊急狀態”取代了“戒嚴”這一憲法概念,其做法就是通過憲法修正案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直接針對憲法原文第六十七條第二十項、第八十條進行更改。倘若采行“接續”方案,憲法修正案就不得不首先廢止憲法原文的第六十七條第二十項和第八十條,而后重新加以規定。如若不然,閱讀者很可能誤以為“緊急狀態”與“戒嚴”是兩個并列的憲法概念,二者之間不存在替代與被替代的關系。在“接續”方案之下,若欲改之,必先廢之。這種先刪后增的做法難以使人一目了然,并不便捷。
針對1993年以后的4次局部修憲,中共中央或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權威文件明確要求:按照憲法修正案把憲法原文改過來,形成當時最新的憲法修正文本。譬如,1999年局部修憲前提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后附《憲法原文與修改后條文對照表》[7]110。這次局部修憲時,《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提出:“這次憲法修改,繼續沿用1988年和1993年的修正案方式,同時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過來。”又如,2018年局部修憲時,《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提出:“建議本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后,由大會秘書處根據憲法修正案對憲法有關內容作相應的修正,將1982年憲法原文、歷次憲法修正案和根據憲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即2018年修正文本)同時予以公布。”盡管如此,這些權威文件均未明示:最新的憲法修正文本應當公布于何種出版物。
就我國憲法文本的公布而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在所有公報中乃至一切形式的官方出版物中應當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該公報每逢局部修憲時是否刊載憲法修正文本,就可以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修憲者對于憲法修正案之性質的認知。其邏輯在于:如若憲法修正案果真是現行《憲法》的組成部分,那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中刊載憲法修正文本就未免有畫蛇添足之嫌。1988年局部修憲之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并未公布當時最新的憲法修正案文本。1993年和1999年局部修憲時,這種情況沒有發生變化,但自1993年局部修憲起,各大出版社就開始出版憲法修正文本了。2004年和2018年局部修憲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及時公布了最新的憲法修正案文本,而在2004年局部修憲之后,各大出版社已經普遍出版憲法修正文本了。從現行《憲法》的第一次局部修正到最近一次局部修正,憲法修正文本在官方和坊間日益流行。就2004年之后憲法文本的實際使用情況來看,憲法修正文本幾乎完全取代了憲法原文及其修正案。這就意味著,憲法修正案只是在局部修憲之時發揮作用,此后便基本歸于沉寂,只能充當人們了解憲法發展的歷史文獻。
在我國所有的現行法律中,唯有《刑法》是通過“修正案”進行局部修改的。1997年3月14日,《刑法》由全國人大全面修訂。“或許是因為憲法修正案的示范效應,更主要的是,鑒于此前采用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這兩種補充和完善方式暴露出來的問題,刑法學界開始呼吁改變刑法修改方式,主張通過刑法修正案來修改刑法”[9],這一建議最終被修法者采納。1997年《刑法》迄今為止的10次修正都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刑法修正案》來實現的。就具體的表述方式而言,我國的刑法修正案與憲法修正案并無二致,更像是1997年《刑法》的修改指南而非其組成部分。只不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從未刊載根據刑法修正案修正而來的刑法修正文本。根據我國《立法法》第五十八條第三款和第五十九條第二款,法律被修改的,應當公布新的法律文本,而標準文本應當刊載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然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只刊載過刑法原文及其修正案,就這一點來看,刑法原文及其修正案才是1997年《刑法》的標準文本。但在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中,刑法修正案與憲法修正案面臨著相同的尷尬:一旦通過便很少有人問津,鮮有機會被閱讀和引用。但本文認為,比較務實的做法是將刑法修正文本刊載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使其成為標準文本,而不是改變刑法修正案的具體形式。原因在于:不管是從通過的總次數來看還是從含有的總條數來看,我國的刑法修正案都遠遠超過了憲法修正案。因此,即使能夠在形式上獲得一定程度的簡化,刑法修正案仍不宜作為1997年《刑法》的組成部分。
無獨有偶,除了《刑法》以外,一些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也通過“修正案”進行局部修改。不僅如此,它們的修正案在表述方式上也與憲法修正案基本一致。另外,其中相當一部分修正案在末尾進行了類似如下的說明:特定的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或者地方政府規章“根據本修正案作相應的修正,重新公布”。正如憲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案一樣,一旦修正文本出現以后,這些修正案便很少被人們所閱讀和引用。綜上所述,我國語境下的“修正案”——當然也包括“憲法修正案”——更適宜于被定性為法律文本的修改指南而非組成部分。
(二)作為憲法文本修正指南的規范障礙
將憲法修正案定性為現行《憲法》的修正指南,實際上就等于承認了憲法修正文本作為標準文本的地位。但問題在于,不同于我國的憲法原文及其修正案,我國的憲法修正文本畢竟從未由全國人大通過——盡管2004年和2018年憲法修正文本確曾刊載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既然如此,憲法原文及其修正案可否“自動生成”作為標準文本的憲法修正文本呢?鑒于憲法修正案已就如何修改憲法原文提供了細致詳盡的指引,所謂“自動生成”并不存在明顯的技術瓶頸。然而,它目前畢竟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據。這正是將憲法修正案作為憲法文本之修正指南的規范障礙,也是憲法修正文本屢遭批評和質疑的主要緣由。僅僅將憲法修正文本與憲法原文及其修正案同時公布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恐怕不足以突破這一規范障礙,反而會使得憲法修正案的性質乃至現行《憲法》的標準文本更加難以確定。
盡管如此,上述規范障礙并非不能通過適當的舉措得以消解。我國現行《憲法》有關修憲程序的規定可見于其第六十四條第一款:“憲法的修改,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提議,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該條款并未規定是否采用憲法修正案來修憲,更談不上明示憲法修正案的基本性質了。那么,全國人大是否可以通過修憲在該條款中增加相關規定呢?這似乎是一勞永逸之舉,但成本明顯較高,而且只能待到我國下一次局部修憲方才有可能實行。那么,全國人大在修憲時是否可以同時通過憲法修正案和憲法修正文本呢?如此就可以確定憲法修正文本作為標準文本的地位。可是,既然可由全國人大直接通過新的憲法文本,那么憲法修正案的存在便屬多余。這種做法與我國1982年之前的全面修憲并無實質的差異。
本文認為,就消解憲法修正案作為修憲指南的規范障礙而言,立法路徑相對于修憲路徑更為適宜。實際上,現行《憲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已經為我國探索具體的修憲模式預留了充分的空間。考慮到采取修正案的修憲方式所導致的憲法文本問題,杜強強教授建議制定《憲法修改程序法》,其內容就包括:憲法修正案的公布以及憲法全文的處理程序和方式[10]。但本文傾向于采取更加便捷的立法路徑——修改現行的法律或者通過專門的決定。作為我國憲制之下唯一的修憲主體,全國人大應當主導這一過程。因此,全國人大既可以考慮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又可以考慮通過專門決定,其名稱可以定為《第×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次會議關于確定標準憲法文本的決定》。不管采取何種具體做法,關鍵在于作出如下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后,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根據憲法修正案對憲法有關內容作相應的修正,由此編輯產生最新的憲法修正文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對于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的編輯工作實施監督。該憲法修正文本是標準憲法文本,應當及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上刊載。”基于這一規定,我國憲法修正案作為修憲指南便不存在規范障礙。
三 結語
我國憲法修正案的兩種定性究竟何去何從?早在我國首次局部修憲之前,修憲者本就應該做出選擇。及至我國第五次局部修憲之后,修憲者仍有必要進行決斷。就我國的歷次局部修憲而言,憲法修正案都是由全國人大根據憲定的修憲程序通過的。所以,其本身應當屬于憲法級別而非法律級別。對于憲法修正案的定性并不會影響其效力位階。盡管如此,檢視我國憲法修正案的性質確實具有不容小覷的實質意義。首先,正如本文開篇所述,這一工作有助于確定我國唯一的標準憲法文本,從而維護現行《憲法》的權威。倘若憲法修正案缺乏相對明確的定性,我們在閱讀和引用憲法條文時仍將徘徊在兩個憲法文本——憲法原文及其修正案與憲法修正文本——之間。若是作為憲法文本的組成部分,憲法修正案自當與憲法原文一同被閱讀和引用,至于憲法修正文本就不宜頻頻“現身”,甚至可以完全消失。若是作為憲法文本的修正指南,憲法修正案則只是在通過前后被公諸于世,隨即成為重要的修憲史材料,而根據其生成的憲法修正文本則是被閱讀和引用的標準文本。另外,這一工作試圖綜合比較憲法修正案的兩種定性,在此基礎上研判哪一種定性更加有利于我國的修憲實踐和憲法實施。
就合法性維度而言,將我國憲法修正案作為憲法文本的組成部分更加妥當。該定性契合美國創設憲法修正案以及我國引入憲法修正案的歷史語境。基于這一定性,憲法原文及其修正案作為標準文本基本上不存在規范障礙。但從合理性維度來看,將我國憲法修正案作為憲法文本的修正指南則更為科學。該定性可以保證憲法文本的實用性,便于人們確定和認知憲法文本的含義。事實上,我國的修憲實踐已經表現出支持此種定性的傾向。在領導起草1954年《憲法》的過程中,毛澤東提出了“搞憲法是搞科學”的著名論斷[11]116。竊以為,制憲如此,修憲亦然。一國憲法修正案的基本性質以及相應的具體形式應當與該國的修憲實踐相適應,這正是修憲的基本規律。修憲規則可以更改,修憲規律卻無從改變。顯然,第二種定性顯然更加適合我國的修憲實踐。
注釋:
①下文簡稱為“全國人大”。
②下文簡稱為“憲法修正案”。若無特別限定,下文中的“憲法修正案”均指我國的憲法修正案。
③下文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簡稱為“我國《憲法》”,將“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分別簡稱為“我國1954年《憲法》”和“我國現行《憲法》”。
④為了表述的便宜,本文對現行《憲法》條文數和具體條款的援引均以2018年修正后的版本為準。
⑤下文將這個版本的我國現行《憲法》簡稱為“我國憲法原文”。
⑥下文將這個版本的我國現行《憲法》簡稱為“我國憲法修正文本”。
⑦韓大元教授曾專門撰文倡導認真對待我國的憲法文本,詳見:韓大元《認真對待我國憲法文本》,《清華法學》2012年第6期。
⑧具有代表性的集中討論,詳見《憲法修改問題筆談》,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3期。
⑨2018年局部修憲之后,胡教授重申了上述觀點。詳見:胡錦光《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語境下的憲法修改》,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
⑩下文簡稱為“《美國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