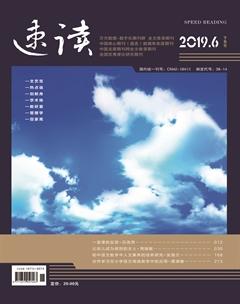融鑄一家之言,成人人可讀之注
有感于斯言,胸中積郁繁復思緒,竟遲遲不敢落筆。大抵是自知才疏學淺,讀畢心懷敬仰歆慕之情,不敢妄加評論。于是又反復通讀幾遍,輔之閱讀了相關論文,草草看了些別家談論語的集子,這才下定決心從先生的自序里面摘了自以為可以概覽其人治學態度與本書的兩句話,從這里談起。
知人論世,錢穆先生著此書時正值學術盛年,而彼時中國正處于內憂外患壓迫下,剛剛踉蹌著步入近代。重壓之下,民族傳統的知識、思想與信仰價值體系面臨著解體和重構,如先生所言,朱本已經過去七百多年了,其中內容對于今日的指導意義必然有所偏離,而論語作為一本思想指導性的思想集合本,必然是要有其可適用性的。先生寫作初衷大概有二:一是對于《論語》一書的解說紛紜,諸多大賢都有著自己的視角和體悟,此書欲備采眾說,折衷求是,熔鑄為一家之言;二是論語其言至簡,普羅大眾正確領悟的門檻太高,需要一本平易而不失嚴謹的注,成為人人皆可讀之注。
也就是說,本書的著作方向起初就被確定為“人人可讀之”的普泛性注釋讀本,這有兩點值得思考。首先,人之為學所求不過有益于社會,那么學術和文化的普及就不能局限于知識領域的高的層級,不可以專才自居自限,應更多的使學術成果易被接受。這一點前些年有大學已經做出了嘗試,試圖“學術下移”,并擬定了職稱評價的相關辦法,雖然在執行層面上無疑是存有漏洞的,但是其出發點的確值得贊賞。錢穆先生此書的受眾預設和寫作思維對今天專業化、職業化的治學傾向有很大的啟發。其次,雖為國學大師,撰寫這份“普適性讀本”之時,他仍保有高度的嚴謹精神,多次返稿、改訂,乃至“常一人,或半天,或全天,獨坐空樓,已涼天氣未寒時,簾寂寂,至今回味,仍感到樂趣無窮”。如此,十載方得功成。他一直保有著“溫情與敬意”的文化態度,由學入信,本書即體現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仰。這也是他一生所秉持的風骨。
回歸文本,所謂新解,無非兩層含義:一為解,即對于《論語》文本的分析闡釋;一為新,此新指的是錢老薈萃前賢思想而凝練以“時代之語言觀念加以申述”。
彼時正值白話文運動剛興起之際,斟酌嘗試過后,先生最終決意使用較簡直的文言,規避純白話對于論語精意的過分繁化和淺薄化,同時也兼顧了文章的可讀性。學者,后覺習效先覺之所學也;習者,如鳥學飛,數數反復。正如錢老所言“雖或多費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浚其深慧。”真正得到學習論語的精髓所在。
既得魚兔,筌蹄可棄。這是錢穆先生在《漫談〈論語新解〉》一文中談到的。此書旨在幫助讀者理解論語,理解孔子其人其哲思,并非著力要抽離出來特定概念,單獨立言,甚至“離開了《論語》原文,我的新解便更無少許剩余的獨立價值可言,那便是我的成功,那便是我作新解時所要到達的一個理想境界。”因而錢注與以朱熹為代表的宋代理學家們最大的差異就在于,錢主要是依原文之勢做解既為注疏類著述,先生致力于貼合原文,還原本初文意,不抽離出來抽象的“義”、“禮”,進行獨立的延伸定義,而是依孔原意“就人就事論”。
作為“人人可讀之注”,在嚴謹的學術與簡平的語言表述和社會倡導之間尋找平衡點尤為重要。本書不側重于清代的考據學派,亦不側重于宋代獨立升華價值的取向,而是如錢穆先生在《漫談〈論語新解〉》一文中所言:“我寫《新解》雖說是義理考據辭章三方兼顧,主要自以解釋義理為重”。重在解說論語背后包蘊的孔子的哲思,而并沒有陷入對于獨立文本的過分糾結之中,在嚴謹治學和追求內理之間尋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平衡點。
錢賓四先生的另一個學術特質是以史學立場注釋經學,這一方面體現在本書中有著浮光掠影對于彼時時代歷史問題的呼應,一方面體現在其在闡釋孔子的道德觀的基礎上,亦著眼于孔子的政治見地,具體表現為對于其所著《春秋》的重視,強調孔子一方面對于政治法度是有所新創的,一方面(尤在禮制等方面)又是“信而好古的”。
正如在錢穆先生發表的其他文章中提到《論語新解》時所指出的,論語中體現的孔子的哲思多以“結論”的形式直接呈現,略去了西方哲學體系架構中所必不可少的問題提出、反復思辨、得解的過程,但這并不可以說明孔子熠熠生輝的智慧結晶并非哲思。而是說明探求以《論語》為代表的中國哲學著作時,應從中國文化自有的演進脈絡出發,而不是以外來思想架構去肢解經典,自縛于西方哲學的邏輯框架之中。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相信錢老是有著真正的屬于儒家的濟世情懷與擔當的學者,以溫情與敬意傳遞自己所信仰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的精魂。熔鑄而成的一家之言是探求論語精神的當代價值的思考,所成的人人可讀之注又何嘗不是旨在喚起人們對于祖國文化的認同感。因為他相信中華之脈必不絕于此,未來仍是方圓千里萬里的江山,這是一種不講道理的熱情,也是一種兢兢業業學習中國深厚傳統文化之后所得出的合理推想,由學入信,不外乎此。
通于古今,無物不然。以廣袤星光引路,恰如北辰。
作者簡介
褚昱辰(2000—),女,漢族,山東濟南人,本科學生,研究方向:經濟犯罪偵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