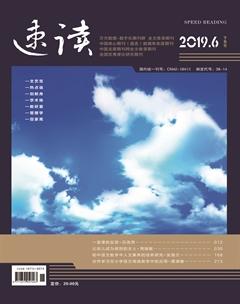“象”與“情”的統一
電影作為藝術門類的其中一種,是動態的再現藝術。電影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藝術形象和性格,在植根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藝術氛圍中反映和再現生活的本質,以體現電影作為藝術呈現在世人眼中的美。電影《黃河絕戀》汲取抗日戰爭時陜北農村以及八路軍的抗戰故事素材,經過適當的藝術加工和創造,放大故事中存在的符合藝術工作者,即電影導演“偏好”的敘事因子,將其依據一定的敘事結構和方式予以整合和排序,運用愛情介于戰爭、西方人切入東方的歷史敘事視角講述迥異于傳統歷史書寫的“抗戰回憶錄”。導演馮小寧成功突破了中國戰爭題材電影的單一敘事結構,嘗試展現西方視角下的東方文化,通過男女主角跨國的愛情故事勾勒東方的抗日傳奇,展現全新的東方的文化世界。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說:“當事物被賦予活生生的形式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事物的枯燥的記述時更易于認識它,更易于對它發生興趣。”當這種形式被東西方觀眾熱切接受和談論時,藝術“再現和說明生活使人感到興趣的現象”的作用得以實現。
作為藝術表達方式之一的電影總在生活的基礎上創造高于生活的情節,它放大現實生活中普遍人物的某些特征或個性,加以改造使其成為熒屏里的“典型”。《黃河絕戀》的男主角歐文緊急墜機踏入黃土大地并與中國軍醫安潔產生愛情,兩人在戰火硝煙中相伴相隨,逐步了解對方直至墜入愛河。在泅渡黃河、后有日兵的追擊下,安潔身中數槍,為不拖累歐文決定舍生取義換取對方的存活——這種不顧個人生死保全他人、維護正義和履行職責的個人犧牲,為陷入絕境的所愛之人放棄自己的生命便是一種“典型”。李澤厚認為,典型作為個性體現共性的特點,其實質正在于它是在偶然性的現象中體現著必然性的本質和規律。男主角歐文在偶然的墜機事故中結識安潔、黑子等人,雙方在深入交往、共同抵御外敵入侵和迫害的過程中產生深厚情誼,故事高潮里為愛情、責任、正義的悲壯犧牲接二連三出現,在這種“偶然性”衍生而來的情節恰恰體現人民為反抗外敵而悲壯犧牲、在所不辭的家國情懷等特定時代下潛藏著的偉大人性,即人之為人的必然性本質。
藝術通過典型體現本質必然才能高于現實。電影主要通過安潔、歐文兩人的愛情故事塑造了為愛情犧牲的安潔、為家國大義葬送生命的黑子、寨主、黑子父親等典型人物形象,傳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普世價值觀以及面對共同危難下人類跨越意識形態、種族、語言等差異所顯現的人性。人性中最本真的情感(包括愛情、親情、友情等)在沉重悲痛的戰火硝煙襯托下得以凸顯和放大,戰爭、愛情等一系列故事母題在近乎于生活的藝術環境中敘述得更為深入,抽象的藝術主題在體現本質的“典型”中煉化和升華。無怪乎《黃河絕戀》成為“中國最經典的戰爭愛情電影之一”,這部電影通過對“典型”的塑造展現其作為動態藝術的優勢和長處,成功地被受眾了解、領會和接受,實現“情”“象”的統一和融合。
藝術的生命、美的秘密就在有限的偶然的具體形象里充滿了生活本質的無限、必然的內容,“微塵中有大千,剎那間見終古”。電影賦予具體有限的基于現實的人物形象以典型性格和特征,使“典型”具備美的深廣的客觀社會性和它生動的具體形象性。
“意境”也是如此。在意境的形成中,“境”是基礎,其中包括了直接喚起情感的某種具體的景色以及與這些景物相聯系的整個生活。電影《黃河絕戀》將鏡頭對準了孕育華夏民族的母親河——黃河以及華夏民族發源地陜北高原,以此為重要形象(或可稱“意象”)構筑了電影男女主角相識、相知、相戀的宏大地理環境。電影植根于客觀真實的生活,用鏡頭呈現符合于、近乎于生活本來面目的環境——熱切大膽的陜北對唱情歌,溝壑縱橫的黃土地,灰頭土臉但淳樸善良的陜北村民,秋天火紅的楓樹林,滾滾東逝的黃河水,綿延萬里的長城,日寇鐵蹄下滿目瘡痍的陜北農村……這些具體的形象最終融匯成電影鏡頭著力渲染、雕琢的客觀“意境”。基于相對客觀真實的意境,導演馮小寧通過對各種意境的形象進行拆分、重構,把音樂、建筑、風景、人物、語言等轉化為視覺形象并聯結為統一體。電影組合運用推、拉、升、降、搖等鏡頭動作,造成正、側、仰、俯、平等各種不同的鏡頭角度,綜合展示了渾厚樸實、遼闊無垠的黃土高原生活環境。
中國美學一直強調情感是藝術的內在生命。“境”雖然是形成意境的基礎,但在意境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情”。導演馮小寧在拍攝“洋人眼中的中國”戰爭三部曲(包括《黃河絕戀》《紫日》《紅河谷》)時,曾經描述過自己的創作意圖:通過外國人視點看到中國人民在侵略者前不屈的民族精神,看到他們博大的胸懷、崇高的人性和對和平的呼喚。具有民族圖騰寓意的黃土地和黃河,以其豐沃厚重的土壤和綿長的支流滋養了中華民族的祖先,并使民族在黃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它是民族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更成為華夏文化的象征符號。朱光潛在《談美》中寫道: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覺。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二者缺一都不能見出美。當電影里的老年歐文緩緩道來經歷過的“中國往事”,電影則開始講述西方視點下的中國世界——黃河作為東方文化的象征,在黃河邊上黑子、三炮、寨主等人前赴后繼、視死如歸的抗日傳奇,歐文安潔的“黃河絕戀”,都成為導演情感傾向的落腳點。
所有藝術都是“象”與“情”的統一。藝術之為藝術,在于它所把握和反映的是生活現象中集中、概括、提煉了的某種本質的深淵的真實。而這種深遠的生活真實里,藝術家主觀的愛憎、理想也就溶在其中。《黃河絕戀》的創作融合了主客觀的“象”與“情”,盡管在有限的技術和成本之下電影的“客觀”略微粗糙和失真,但其“情”毋庸置疑。
作者簡介
林文靜(1998—),女,漢族,廣東惠州人,單位:華南師范大學,2016系本科生,漢語言文學(師范)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