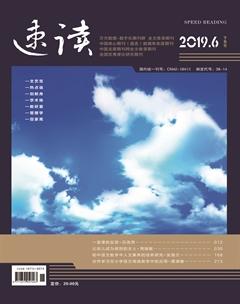評論作者能否加入作家協會,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匡吉
一位朋友熱愛且擅長評論寫作,多年來在各大報刊發表很多作品,可謂量多質優。前段時間,他申請加入某作家協會,當把作品提交審核時,卻被告之不符合加入條件,理由是:他那些在報紙新聞版面或欄目發表的評論不屬于文學作品,應當屬于新聞作品。
既然這樣,也只好作罷,但這位朋友始終疑惑:評論作者為什么不能加入作家協會呢?
對于這個問題,還是先看看有關政策規定怎么說。比如,申請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根據《中國作家協會章程》,申請人應是“發表或出版過具有一定水平文學創作、理論評論、翻譯作品者,或從事文學編輯、教學、組織工作有顯著成績者”。根據《中國作家協會個人會員申請審批辦法(試行)》及有關附件,文學創作主要是指小說、散文、報告文學、詩歌、詩詞、影視戲劇文學、兒童文學和網絡文學等;而理論評論,也僅限于文學方面的理論和評論,一般都是發表在文學期刊或報紙副刊。因此,以作品類別來看,評論作品確實不在范圍內。
而揆諸現實,評論作者也很少有加入作家協會的。即便有加入的,恐怕靠的不是評論作品;至于沒有加入的,除了有的是因為個人沒產生加入的想法,更多是由于不符合加入的條件。
其實,評論作者能否加入作家協會,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有人可能會問:寫雜文可以加入作家協會,寫評論怎么不能加入呢?不否認,雜文與評論是有區別的。雖然兩者都是以“論”為主,但人們通常認為,前者屬于文學,后者屬于新聞。所以雜文作者申請加入作家協會時,雜文作品都是歸入散文門類;而評論作者想要加作家協會,評論作品卻沒有可歸的門類。應該說,對雜文與評論這樣區分并非沒有道理,且不說兩者寫法不同、風格有異,就連發表的陣地也不一樣。就拿報紙來看,雜文主要發表在文學副刊,評論主要發表在新聞版或評論版。
然而也應注意到,雜文與評論實際上也有聯系,有時兩者就像孿生兄弟一樣,難以分辨清楚誰是誰。比如,有的雜文作品具有明顯的評論風格,有些評論作品富有濃厚的雜文味道。近年來,報紙副刊上楷體加框的雜文欄目很難讓人看到,雜文陣地幾近絕跡。有些雜文作者要么去寫評論,要么把雜文發表在報刊評論版面和欄目。像這樣的有雜文味或者本身就是雜文的評論,被文學拒之門外,似乎有些不應該。因此,說雜文屬于文學,大概不會有錯;要說評論屬于新聞,好象有點片面。
關于新聞的概念,漢語詞典解釋為:一是借助語言、文字、圖片、錄像等,向公眾傳播的消息。二是泛指社會上新近發生的事情。三是新聞體裁,包括消息、通訊、特寫等。根本上講,新聞反映的是事實,無論通過什么方式和媒介,都是作者客觀的記述,因而真實是新聞的生命。相比較而言,評論表達的是觀點,不管針對什么現象和問題,都有作者主觀的見解,故而新意是評論是靈魂。
如果非說評論作品不屬于文學、而屬于新聞,那么評論作者是不是就可以加入記者協會了呢?非也!加入記者協會只能是新聞工作者,業余評論作者非但加入不了,連參加中國新聞工作獎評選的資格都沒有。中國記者協會頒布的《中國新聞獎評選辦法》就明確,“中國新聞獎參評作品為以上新聞單位原創,由新聞工作者采寫制作,并在上一年度內刊播的新聞作品”。顯然,只有新聞工作者撰寫的評論才能參評。
一定程度上講,評論被歸入在新聞之列,恐怕是因為評論主要是更多通過新聞媒介作傳播,從而發揮輿論引導功能。這也不能因此說評論就屬于新聞,說評論與新聞有交叉好像更合適。當然,從評論本身來看,有些評論確實跟新聞有關,比如那種以新聞為由頭、對剛剛發生或發現的新聞事實、現象和問題所寫的評論,被稱為時事評論,簡稱時評。然而,有些評論卻與新聞無關,比如那種以人們在學習、工作、生活方面的思想動態、思想傾向或思想問題為對象的評論,被稱為思想評論。這樣的評論能屬于新聞嗎?
如今是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加上媒體的空前發達,評論有了很廣闊的生存空間。報刊等傳統紙質媒體很多都有評論版面和欄目,網絡和微信公眾號等新媒體的評論更是層出不窮。無論是評論作者還是評論作品,都越來越多,可以說是很龐大的作者群體和作品規模。不少評論作者寫的評論作品,文辭優美、感情真摯,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如果評論這個領域內,因為評判標準和條件的原因,優秀評論作者不能擠身作家行列,優秀評論作品不能登入文學殿堂,這不能不是一種遺憾。
什么是文學?根據《辭海》的解釋,廣義泛指一切思想的表現,而以文字記述的著作;狹義則專指以藝術的手法,表現思想、情感或想像的作品。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之一,古今中外都曾把一切用文字書寫的書籍文獻統稱為文學。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的文學概念,似乎都應該包括評論。就拿古代文學作品來說,中國古代寫得好的散文,事實上大多都是政論文。像賈誼的《過秦論》《治安策》、司馬相如的《上書諫獵》、諸葛亮的《出師表》、韓愈的《爭臣論》、歐陽修的《伶官傳序》、蘇洵的《六國論》《管仲論》等等,這些名垂千古的文學經典,就風格、寫法來看,難道不是評論嗎?古時如此,當今亦然,優秀評論完全可以納入文學范圍。
包容性、融合性是文學的基本特征。事物是聯系的,藝術是相通的。文學起源于人類的思維活動,是社會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一部作品屬不屬于文學,主要取決于內在本質,不在于外在形態。并非只有純正“文學元素”的才算是文學作品。過去,報告文學因為介于新聞報導和小說之間,曾不被主流文學認可,如今已歸入文學正統。2015年白俄羅斯作家、記者斯維蘭娜·阿列克謝維奇,以其杰出的紀實文學作品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她的復調式書寫,是對我們時代苦難和勇氣的紀念”,因此被媒體稱為“非虛構者寫作的勝利”。此事曾引起爭議,有人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一個寫非虛構作品的記者”“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殊不知,接下來還有更大爭議、更加奇怪的事情——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美國民謠歌手鮑勃·迪倫,以表彰他在“美國歌曲的偉大傳統中開創了一個新的詩意表達”。民謠歌手憑著民謠歌詞,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雖然有些不可思議,但也在情理之中。有人撰文寫道:“一百年來,諾獎追尋優質文學沒有狹隘的門檻,沒有對獲獎者身份、作品形式、國籍等設定特定的界限,而是開放的評選機制和原則。一方面給更多優秀創作者以機會,另一方面拓寬了文學的界定范圍,這更符合當代文化研究的方向,也更有利于推動人類文學藝術的發展。”
古今中外,文學的界定一直難有定論。不管怎么說,隨著形勢的發展、時代的變遷,文學的界定標準、范圍和規則,也應與時俱進、隨事而制。鮑勃·迪倫被授予獎諾貝爾文學獎,充分體現了文學本身的包容性和藝術行進的融合性。由此想到,連民謠歌手都可以當文學作家,民謠歌詞都可以成文學作品,那么評論作者為什么不能當文學作家、評論作品為什么不能成文學作品?
文學的發展過程,應該是不斷自我充實和完善的過程。不妨聯想一下,現代奧運會的發展作為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體育盛會,從1896年舉辦第1屆開始,至今已舉辦31屆。比賽項目最初只有9個大項目,現在已增加到28個大項目。除此之外,奧運會的種類也越來越多,比如夏奧運、冬奧運、殘奧運、青奧運和特奧運等。對于文學藝術創作來講,體裁樣式和表現形式越來越豐富,符合發展規律和發展方向。倘若“文學圈”把自己圈起來,不能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文學藝術的路子只會越走越窄。只有突破文學的場域,打破固有的藝術藩籬,才會讓文學藝術更有生氣、更有活力。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而產生的網絡文學,曾經沒被文學界看好,當其繁榮到不得不被重視時才被接納。實際上,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非但不是對立的兩極,反倒是互相滲透的有機體系。比如,不少傳統文學通過電子化成為了網絡文學的一部分,網絡文學作者也受到了傳統文學的熏陶;又如,網絡文學通過出版進入傳統文學領域,并依靠網絡的巨大影響力,進而影響到傳統文學。
話說回來,讓評論從古代回歸到今天文學領域,同樣可以給文學注入新的活力。我們都知道,文章體裁包括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和應用文。在上學時學習寫作文階段,這些體裁都要學習和掌握,其中議論文被普遍認為是很重要、很難寫的一種。毫無疑問,評論就屬于議論文。盡管文學創作不等同文章寫作,但文學體裁中缺少評論這一文體,對文學并非有益。特別是在當今雜文日漸式微、并且逐漸被評論取代的情況下,評論恰好可以成為一種創作形式的補充。歷史上唐代大文學家韓愈、柳宗元等人倡導的古文運動,主張文道合一,強調“因事陳詞”“文從字順”,開拓了散文新天地。現在,以文載道仍然是評論的追求。評論寫作,因其出于對政治性、群眾性、針對性的把握和具有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的表達,而展現出思想的魅力和語言的藝術。從這方面來看,優秀的評論作品,應當是優秀的文學作品。
社會生活是文學創作的唯一源泉。一個作品的文學價值,在于能否為人們提供精神指引。正所謂知人論世、觀人知仁,只有根植于、來源于現實的文學作品,才能在既適合群眾口味、又提升群眾品味中,引導讀者更加深刻和理性地認識社會、理解生活。如今,有些作家寫的作品已很少讓人看到,也很少有人愛看,這未必都是藝術性不夠所致,更多是現實性缺乏使然。
記得幾年前看過這樣的報道,中國作家協會新會員名單公布后,廣州市民和文化界人士向媒體表示,名單上的22名廣東省作家“一個都不認識”,讀過這批新會員作品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這種現象,雖然并非是審核標準和程序的問題,但不妨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一下:為什么“一個都不認識”?這究竟是大眾遠離文學,還是這些入會作家寫的作品離群眾太遠呢?作為作家,應該關注社會、關注百姓、關注民生。僅看這一點,事實上很多評論作者已經做到了。無論是時事評論,還是思想評論,都是在“接地氣”的“關注”中思考的結果、創作的結晶。
作家協會作為黨和政府聯系廣大作家、文學工作者的橋梁和紐帶,是繁榮文學事業、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社會力量。加強作家協會建設,呼喚評論作者;促進文學藝術繁榮,需要評論作品。因此,作家協會的大門應該向評論作者敞開,文學藝術的舞臺應當給評論作品留有一席之地。起碼說,作家協會在吸收會員的問題上,不妨轉變觀念、改進做法,比如把評論作品歸入“散文”一類,或者在“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門類之外,另外增加“雜文、言論”一個類別,將雜文從“散文”中撥離出來,同評論歸入此類。通過這樣的原則和機制,與新聞有交集的評論如能擠身文學行列,既可以讓文學的內涵得到豐富、外延得到拓展,還有利于評論的發展和進步。
誠然,作家協會接納評論作者,絕非意味著降低門檻。可以肯定地講,并非所有的評論作者都能達到作家水平,也并非所有的評論作品都能稱為文學作品。目前來看,評論作者隊伍還參差不齊,評論作品還良莠雜揉,尤其是重數量、輕質量的問題一度比較突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無論什么體裁、什么內容,是不是好作品、有沒有生命力,都要看寫得怎樣。所以作為評論作者,除了不吐不快地想寫外,還應該以負責任的態度,把評論寫作當成文學創作來對待,爭取寫好每篇作品、多出一些精品。
總之,至于評論作者能不能加入作家協會,對于作者本人來講,還是靠作品說話;對于作家協會而言,還得由作品決定。(2019.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