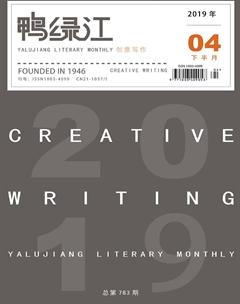創意想象與世界的重構:游戲改編電影
一
游戲改編電影是一個典型的21世紀的現象。這個現象從20世紀末開始,直到今天似乎仍然方興未艾,持續地影響著全球電影的格局。當我們看《古墓麗影》或《生化危機》這樣的電影,對游戲迷來說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體驗,對未接觸過游戲的觀眾來說就是一部普通的電影。于是經過游戲改編的電影會受到不同角度的關注。電影與游戲的關聯在今天方興未艾,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深刻地改變我們生活的時代,是值得格外關注的,它既改變電影也改變游戲。在這兩個相似但不同的講故事的體驗之間,在同樣的影像和聲音但不同的形態之間,都存在著復雜的界限和跨越界限的嘗試,誰都意識到兩者有相似性,但兩者又是如此地不同。這個現象值得關注和探討之處一是在于游戲與電影的異同,電影和游戲究竟有哪些相似和差異,它們的想象力是如何呈現的?二是電影和游戲之間相互作用的意義究竟何在?改編本身具有何種價值?這些問題似乎對正方興未艾的中國的電影和游戲來說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
電影當然是現代科技和工業化的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它在20世紀初的出現是個奇跡。它對人們生活的改變是如此巨大,讓人們在影像和聲音所展現的故事中沉醉,在一個光影的世界里重新想象自己的生活。它最好地在文化上顯示了工業化的力量。在幽暗的電影院中,人們在故事中所看到的世界既指向我們所生活的真實世界,也指向一個虛構的幻想世界。電影是人類虛構敘事在20世紀最好的呈現,它所呈現的是他人的故事,這些故事由于我們的觀看而具有了高度的價值,讓我們為劇中的故事和人所牽動。電影的文化是一種觀看的文化,我們通過銀幕來理解故事,讓我們在他人的故事中獲得某種生活的意義和價值。我們在這里是一個被動的觀看者。故事從開頭到結束的全過程都不能由我們主導,我們的感受當然千差萬別,但故事本身難以變化。雖然會有各種復雜的敘事效果,但無論如何開放,我們的被動性難以改變。這似乎是現代性工業社會的生活模式的一種展現。
游戲(這里的“游戲”二字毋庸置疑地指向電子游戲,相信已經不會有任何歧義)則是20世紀后期信息時代的重要成果。它可以說是在21世紀初期的最好的表征。它和電影雖然都追求視覺的滿足,但其根本的立足點卻有所改變;游戲是一種具有高度參與性的視聽呈現,雖然和電影有相似的視聽表現,但我們的參與卻讓游戲改變自己的敘事路徑,過關或失敗是我們自己的行為造成的。這里的一切是交互、互動的結果。我們自己介入了故事本身,讓故事在每一個關口都可能被改變,故事的繼續完全取決于我們的選擇或能力在。在通關、格斗、玄幻的歷史傳奇等游戲類型中,我們都有某種主動的選擇,我們按下某些鍵,做出某些選擇都會讓過程本身發生不可逆的變化。這些變化最后決定了故事的結局。在這樣的故事里,我們永遠通過自己的手成為想象中的故事的一個主角,我們不是靜觀而是參與,不是被動而是主動。這種主動性正是游戲所產生的內在動力。這似乎正是某種后工業的結果,也指向了某種后現代的新的生活形式。
電影/游戲之間看起來都是由視覺主導的敘述,但其內在的動力不同。靜觀/參與和被動/主動之間的差異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虛擬性”的作用。其實,所謂“虛擬性”常被用來說明電腦和網絡所構筑的世界,我們都會認為這是一個和現實有關,但超越了現實所創造的比現實還現實的另外一個世界。在虛擬的世界之中,人們也有一種“生活”,這種生活本身也具有巨大的意義,許多人似乎都認為它比真實的世界更真實。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觀察“虛擬性”的作用,就可以發現“虛擬性”的最好的表征就是游戲。游戲的世界是不及物的,好像和我們的現實世界的相關性降低到了最低點,它是天馬行空般地創造了一個虛擬的世界。我們進入這個世界,想象一種和現實的主體性完全不同的新的自我的主體建構,我們不再是現實生活中的自我,而是一個超越了現實的虛擬世界中的人,我們可以通過想象完成神奇的任務,建構一個不同于現實的自我。這種虛擬的效應其實是游戲的魅力所在。這種虛擬性的作用就是讓我們在現實中的失落感在虛擬之中得以超越,獲得一種欣快的滿足。因此游戲會在超真實之中讓真實的狀況在片刻中被徹底超越。我們可以把自己具體地等同于游戲中的主人公,因為這個主人公的行動正完全是“我”的意志的外化,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我”的化身或替身。這就是一種真正的“扮演”。我們超離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的角色,在游戲中體驗到自我實現的路徑。雖然我們明知這一切是虛擬的,但也知道這一切的虛擬比真實還真實,讓我們在玩的同時忘卻現實的自我,進入一個虛擬的自我。游戲的視角永遠是主人公的視角,我們永遠和主人公認同,和他一起進入故事,直接變成他。這就是虛擬的力量。它的體驗和參與的特性是電影難以給予的。我們可以不斷地重復進入這個故事,但最后的結局也有成有敗,故事的結果常常不同。在游戲中固定的是程序,由此獲得的初始情境是確定的,而不確定的是故事的路徑和結局。這些都可以在程序中有更多的設置。但電影的優勢在于它可以通過故事過程中的復雜細節來展示自己的唯一結局的合理性,通過似真的感受將結局合理化為唯一的結果。但游戲的“虛擬性”則缺少展示復雜細節的愿望和能力。
但電影與此不同,它是依賴講述“他人”的故事來建構自身的,不可能讓我們直接操控主人公,化身或替身為主人公,只能靠所謂的鏡頭語言將我們的主體位置鎖定在觀看者的位置上。我們雖然可以隨著情節而感動,但那個世界我們難以進入,無法在其中發揮作用,我們仍然是被動的。電影讓我們相信故事的真實性,讓我們感動或受觸動,但它不可能讓我們直接改變具體人物的命運,也無法更改故事的架構。但電影比游戲復雜和微妙的是它可以給人以想象復雜社會關系和生活形態的能力,游戲中人的選擇有限,但電影里我們看到的各種生活的可能性無窮。電影故事有機會比游戲更復雜更微妙,同時也更讓我們在外面去觀察。在電影里,銀幕既是展示又是間離。展示一個我們在現實中無緣看到的“他人”的故事,但又阻止我們直接“進入”故事。故事是別人的,這一切不是讓我們在“虛擬性”中扮演角色,而是讓我們處在一種“虛構性”之中。“虛構性”是純粹講故事,沒有參與的機會,參與問題在電影中是無法解決的。在這里“虛擬性”是一種進入和參與的路徑,故事由于有了你的介入而發生改變,程序已經考慮了多種可能性,而不需通過故事本身的復雜性來反思。
實際上,電影是工業化階段的產物,其技術手段還達不到具有互動性,因此雖然希望我們感動投入,進入故事,但這都有不可能解決的困擾,它的基本元素是“講故事”,不得不由編劇和導演講完所有的故事。我們在其間面對的“大他者”是故事本身。而游戲是在信息時代的電腦和互聯網時代發展的,它設定的是考慮到故事的復雜性的程序,你可以在程序的設定之下玩故事,讓這里的“大他者”是故事之上的程序。這個區分其實是最關鍵的。就是電影的唯一依靠是故事,而游戲則依賴的是程序;電影的故事不可變,只能由我們的感受加以闡釋和理解,但游戲的故事可變,由于它之上的程序已經安排了可能的各種選擇,我們可以自己直接改變故事本身。這種差異性是最值得思考的。
三
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美國通過游戲改編的電影層出不窮。人們看到了電影和游戲在講故事方面的共同性,因此認為電影有機會將游戲的觀眾吸引到電影之中。但十年左右的實踐卻讓人們發現,成功的游戲改編成電影之后同樣成功的范例很少,既有少數成功的例子也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而電影改編游戲的嘗試效果還更好些。其實這非常容易理解。一是從“虛擬性”回返確定的“虛構性”存在著難以逾越的困難。將開放的各種可能收束為確定的結局往往使得游戲迷們感到失望。“虛擬性”的多樣可能性變成固定的結果會使得習慣游戲思維的人永遠覺得電影扼殺了他們選擇另外可能性的機會。二是電影所具有的展示復雜細節的能力,在游戲改編電影中往往難以呈現,游戲本身的作用是將流程的各種可能加以選擇,在其中難以將電影的生動性展示出來,使得傳統的電影觀眾也不能夠滿意。“虛構性”的豐富性的缺失使得這種改編常常試圖兩面討好,但最后卻是兩面不討好。這其實是這種改編常會面臨的困難。這有點像過去電影和戲劇的關系。從戲劇改編電影容易成功,而從電影改編戲劇就不容易成功。從電影改編游戲容易成功,而從游戲改編電影不容易成功。癥結就在于其新的形式比傳統的形式更具新的元素。這些元素在傳統的形式中難以適應和容納,使得改編變得困難。電影和游戲是否是相似但不兼容的文化類型,值得繼續思考。
電影在今天的“后現代”時代仍然是我們主要的娛樂形式之一,但游戲的崛起肯定也是重要的事件。兩者的關系仍然是我們時代的重要議題,值得探索下去。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