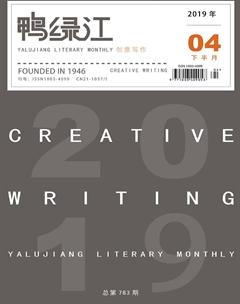歸途
你終于閃耀了嗎?我旅途的終點。
——瓦萊里《水仙辭》
一
——聽說你的病情更嚴重了,還是和以前一樣嗎?
——是的,我看了以前留在聽診記錄上的,酷似孩童顛倒錯亂的咿呀學語。現在比以前更嚴重了。
“在冬天光線過于充足的日子里,我透明的心甚至也有光線爬進。也就是在這種時候我一邊幻想自己身上生出無遮無攔的雙翼,一邊強烈預想到我這一生恐將一事無成。”
——啊,似乎顯得棘手了。
——記得我曾講過的嗎?我覺得人類吵鬧得過分。我覺得存在是一個漫長的康復過程,仿佛我的每一天都是從不治之癥中重生過來。與鉆石一樣,我不斷地被自己的粉塵切割。我只得在自己身上,不斷克服著這個時代。
——你大概又是極度的悲觀主義者吧。你并不一味覺得這世界很糟,相反,你覺得這世界挺好的,只是這漫天繁華都與自己無關,并且以后也不會有關聯。
——大概如此,這感覺很像在遙遠的南美叢林里有與自己精神相連的樹不斷被砍伐。
我不屬于這個時代。
——這樣啊……那這次,我給你講個故事吧。
——不錯的建議,愿洗耳恭聽。
在他意識到自己可能是地球那場被降維的浩劫中唯一的幸存者時,已經是新紀元三十年了。
紀元的概念,來源于人類自己。當發現異文明后,屬于地球的新紀元就此展開。人類陷入了不斷的騷亂與星際戰爭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毀滅性災難,陷入泥潭。其實也不用多做解釋,這實在是容易想象的時代。
在這三十年里,同他一樣,被外放的星旅者——實際上是在重大事件里被流放的罪人們,大多為天才,都沒有獲得被召回的權利。也許是有的吧,無奈運氣不好,犯下的罪責又難以赦免。況且他的歸屬地實在偏遠,甚至偏遠到無法與任何其他星球達成交流。
卡俄斯處于外環星系的邊緣,屬于九次可見宇宙范圍。大約是29.37唐緯 ,緯度偏低,附近的區域很空曠。它半徑不大,重力不強,環繞氣體不少,因為距離中心星系偏遠,所以一直很安全,孤立,且信息閉塞。
請想象一下他的樣子,在無邊的漆黑中有一顆藍色的星球,裹在一層奶白色的云霧中。它沒有任何光亮,甚至在幾千萬光年之外都只能看見人造的燈火。
要說唯一的歸屬感,只是在他的到來之前人類在瞭望臺上留下的唯一痕跡,一首詩:
那么多昂貴的證據,塵土
使我們相信難免一死
……
陰影與大理石的修辭學
允諾或預示了備受向往的
成為死者的光榮
二
——Chaos?這真是個好名字,我曾經讀過他的故事,被子Erebus殺死的混沌,純粹的欲望和無人性的載體。真是諷刺,博爾赫斯寫下這首詩的時候,肯定也未曾料到會是異文明的燈塔吧。
——嗯哼,你知道嗎?這很像中國古代的一對很出名的聯子,上聯這樣講:“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
——這讓我想起,悲劇來自于通識與基調,是一切無法抵抗的最終命運。我們看它時只能驕傲又謙遜地想,事已至此,好自為之。
卡俄斯人的身材短小,柔軟透明。很像充滿水的氣球,又似行走在地面上的水母。他們身體結構松散且外表鮮艷,體表是和細胞膜結構類似的流動指膜,不能隨便透過,彼此相遇時卻可以相互融合在一起。他們性格溫和友善,可是反應極度遲鈍,思想全透明。因為特殊的位置,他們與周圍星球的文明有相差懸殊的時間尺度。
讓他覺得有趣的是當兩個卡俄斯人相遇路過時,他們身體的一部分會短暫重疊混合,再開始重新分配。在這種奇怪的重疊中,他們對自己的肢體并不看重,因為隨時變化,所以只能認知自己永遠都是自己。
他至今無法判斷卡俄斯人的壽命長短,因為互相物質的不斷交換,使一個個嶄新的生命隨時誕生,又迫使一個個蒼老的靈魂隨時死去。似乎他們是可以永生的,生于混沌之中,永遠的難舍難分。
與他們交流實在困難,盡管翻譯器可以解決語言問題,但他們的思想從不在同一維度。卡俄斯人的物質文明對比人類還停留在史前期。而精神上更不樂觀,他們并沒有對事物清晰的認知和對倫理的劃分。如此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沒有高等文明愿意把戰火沖向卡俄斯,對于這種毫無抵抗能力的低等星球,即便坐標暴露,也是浪費罷了。
他想起選擇這里的初衷,大抵是因為,那層奶白色云霧里大片暗淡的藍色吧。
三
——他一定很孤獨,被迫流放的天才,一定曾為夢想奮不顧身過吧。
——的確如此,只是后來他明白,傳統意義上的成功鏡像,一旦用自由衡量,就顯得實在難以啟齒。
提起他的放逐,已經是很遙遠的事了。
審判來源于人工智能革命,舊人類的擔憂實現,盡管他作為業內首席專家負隅頑抗,也沒能改變人類被迫與人工智能達成共和協定的局面。
人類的輿論導向再也無法壓制,他背負了無比沉重的罪名和所有高層領導人為洗白有意無意的指向,被迫流放。那年他三十四歲,黃金的年齡,女兒剛剛二歲而已。他用盡最后一點人脈幫家人打點好了新住所,踏入了永別的遠途。
你看,這就是人類的劣根性,需要他的時候奉若圭章,不需要的時候便看作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了。
這實在很像科塔薩爾講述的,人們發明了滅蠅器,一塊糖放在里面,眾多蒼蠅們絕望地死去。就這樣斷送了與這些動物發展兄弟情誼的可能,——它們本配得上更好的命運。
嘲諷的是,高等文明對于地球的毀滅,卡俄斯交換物質的特殊性竟使他成為唯一的幸存者。
“徒手建海市蜃樓之人,擺酒灼月熱無客宴席。坍塌。余殼軀生還。永葬荒墟,絮果獨吞。又見宴起,歡歡喜無盡。”
他年輕時曾聽一位教授講道,“人生來就只有一個想法,終其一生不過是在不斷豐富它。”他當時覺得,一輩子只圍著一個念頭轉,這未免也太反動了。直到如今,他才明白他是對的:人這輩子都在追隨一個想法。可是在如此漫長的流放生涯中,他唯一的信念——家園與親人盡毀,如今真正的孑然一身,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了。
其實卡俄斯人并不知道,自我的保留,只是一種錯覺。在重疊的瞬間,最初的兩個人就不存在了。他們成為兩個嶄新的人,新的人不知道相遇之前的一切,以為自己就是自己,一直沒有變過。
之后,他做出了決定。
他在等這一刻,不用任何人動手,死亡是最好的重生。
漫長的實驗和飛行器改造,耗盡了他畢生學術和心血。失敗后又成功,成功后再毀于一旦,不斷反復于無常止步于起點。他想求得一條歸途,一條回家的路,為此,他等了三十年,終于趕在了死亡之前。
他知道自己已瀕臨大限,年老的身體不再敏銳矯捷,一切的行動都十分艱難,希望似乎被關進潘多拉的盒子中,永無天日。
他只能反復回憶,離鄉時母親唱的那首家鄉的歌謠,那時年幼不懂,現在恍如隔世:
“你從那么遠的地方趕來/你還那么年輕/你還那么衰颯/這天地的際遇莫過于生死浮休啊/不如永結無情游/我是人間折梅客你是關外水云侯”
四
——你知道嗎?給你講完這個故事之后我就不再是我,你也不再是你了。我們在時空中一點點重疊,從此之后你我身上都會帶有對方的分子,成為嶄新的生命。
——你是說,卡俄斯就是我們自己的星球嗎?
——我們自己的星球,你說是哪一個呢?有哪個星球曾經屬于過我們,還是我們曾經屬于過哪一個星球?
——那,殉道者成功了嗎?
——我喜歡這個稱呼,這是個好名字。其實故事應該結束了,但我相信,他應該回去了。
極度的悲傷在他身后炸出一片片火紅的煙花,絲絲纏眷。往日迸濺的記憶被反復厭棄,此刻終將亙古懸掛。當文明走向終結,他選擇自刎烏江。他知道神性不過是維度框架下被迫誕生的澄澈,真正的勝利,是當揭開宇宙的面紗,殘存的人類選擇與文明共存亡,再無力戰斗的時刻。
智慧的參數再也無法運算,他選擇跌落時空的縫隙,永遠卡在平行宇宙的風塵口。嗆著淚,終將緘默。
是否真的有神明存在。如若存在,在無辜者雙手被捆綁送往刑場之時,令他牢房的窗縫間有雌菊燦爛盛放——或許這就是神能做的。真主之外再無真主,他們皆不在此列。
地球是和他離開時一樣的顏色,鮮艷于二維的畫面里。他嘗試伸手去碰,卻明白再也無法靠近。
宇宙本來就是奇跡,它承載著十一維的無數文明。除了互相廝殺,本質上任何文明都是相同的。
與獅子和羊一起共聽俄爾普斯彈奏,這是人類的理想。
他活在最后的故事線里。
這是新的造物詩。
尾 ?聲
——你還記得《三體》里智子和程心的那段對話嗎?
——“那總比全軍覆沒強”,智子說。
“從我們的價值觀來講,未必。”程心暗想。
——我大概明白了。
——明白什么?
——我想我能走回去了,走向歸途。
“趕緊起床,要遲到了啊”,咚咚的腳步聲在清晨顯得格外清晰,光霎時就填滿了整間屋子,母親的臉一點點在我瞳孔里放大,她走到床邊,一邊拽我一邊問。
“你在自言自語什么呢?”
張忱涵:河北省宣化一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