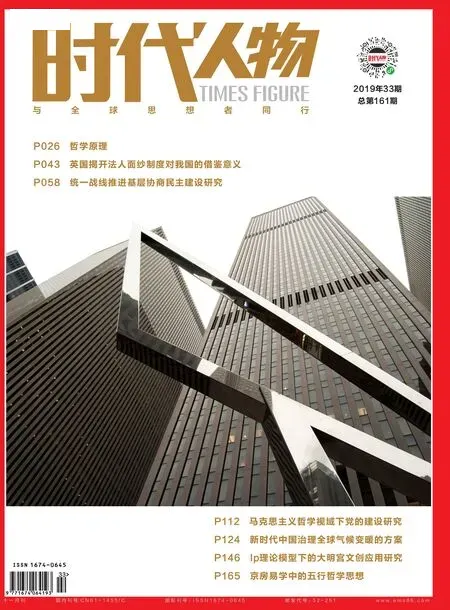英國揭開法人面紗制度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李哲 包哲鈺
(蘭州財經大學 甘肅蘭州 730020)
一、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起源
公司是一個遵循法律的規定和程序設立的法人實體,也是為了經營目的而設立的組織。在法學理論中,“主體”一詞是用來描述任何權利和義務的承擔單位,因此公司法的主體就是公司,而公司擁有自己獨立的法人資格。法人可以擁有財產,有權起訴和被起訴,能夠成為合同的一方,是承擔法律責任和義務的單位。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又稱為“揭開法人面紗”原則(the Principle of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是一種來自英美法系的學說。具體指法院在某些情況下否認公司的人格和股東的有限責任,并使股東或董事對公司或債務的行為承擔個人責任的制度。
16世紀到18世紀之間,英國法律經過不停地演變,最終將公司具有人格變成國際公認的事實,英美法系學者生動地將法人人格描繪為公司的面紗,將公司法人人格與股東的個人人格分開,保護他們免受公司債權人的直接追責。公司人格與股東人格的分離主要體現在其財產分離上。雖然公司的財產由股東的出資構成,但它由公司獨立控制。公司法人對公司財產的債務承擔獨立責任,股東僅對有限責任承擔責任,即不對公司債權人直接承擔責任,只對公司資本限額承擔責任。這種“面紗”的優點是不言而喻的,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一些風險。一些股東將使用這種面紗違反誠信原則,規避法律義務,濫用法人資格或嚴重損害債權人利益。為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就誕生了。
二、英國揭開法人面紗制度的立法現狀及表現形式
Salomon v.Salomon是英國公司法中最重要的法人人格案例。[1]從那以后,出現了揭開公司面紗的原則。英國是普通法系國家,這一原則的歷史積累反映在各種判例中,但英國成文法也有規定。英國對于揭開公司面紗的原則非常謹慎,所以成文法中嚴格限制債權人直接追究公司股東責任的權利,避免濫用該原則,限制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
(一)代理
如果公司與其股東之間,或集團公司的母公司與其子公司之間存在明確的代理關系,則法院可以揭開公司的公司面紗。明確的代理關系可以理解為授權,或者股東或母公司具有如此強大的控制權,公司被視為股東或母公司的代理人。Re FG Films案件的判決表明,股東對公司的控制或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控制必須達到相當程度,且證明受控公司的運作純粹是出于股東或母公司的目的,那么公司的行為應被視為股東或母公司的行為[2]。
然而,在代理理論的實踐中,法院認定對公司過度控制的股東應對其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這主要強調了股東與公司之間的代理或控制關系是錯誤的。在所有公司行動或無所作為的背后,必須有人的主動性。總有一些股東在參與業務控制的時候,自然地利用這種控制來促進自己的利益,這是投資的本質。控制的事實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公司很難真正獨立于股東。因此,現在在實踐中,雖然代理理論在邏輯上是可行的,但實際操作起來困難重重。
(二)虛假外觀
如果公司的成立只是一個幌子,掩蓋了公司成立的真正目的或公司的實際情況,或者說,當公司成立的目的是欺騙債權人或逃避法律時,法院應該揭開公司的面紗。判斷公司的成立是否是欺詐行為并非易事。在Adams v.Cape案件中,上訴法院認為,如果被告使用該公司作為掩護來逃避法律對被告施加的某些限制或剝奪第三方相對于被告的權利,那么該公司的成立實屬欺詐行為。[3]Gilford Motor Company Ltd v.Horne案中,霍恩作為吉爾福德汽車公司的前雇員,其簽訂了競業禁止協議同意在他離開后不從前雇主那里招募任何顧客。然而為了規避這一限制,他以妻子的名義成立了一家有限公司,并代表公司向前雇主招攬客戶。上訴法院由此認定該公司的成立就是為了掩蓋霍恩的罪行[4]。根據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欺詐、虛假行為可能導致公司在特定原因下否認法人人格,但這些原因并非詳盡無遺,這還需要法院結合具體情況自行解釋和決定。
(三)單一經濟體
在DHN v.Tower Hamlets案中,DHN通過其子公司Bronze Company經營自己的業務,該公司與DHN公司有相同的董事,根本沒有業務。它唯一的資產是DHN作為許可證持有人的房地產。另一家子公司擁有DHN的車輛,但也沒有開展任何業務。然后,DHN被迫關閉,因為它被政府強迫收購。如果DHN對土地有實際利益而不僅僅是許可證持有人,那么DHN只能獲得大量補償。[5]當時,丹寧勛爵認為集團公司實際上是一個單一的經濟單位,應該被視為一個整體,因此DHN應該得到補償。然而,在Woolfson v.Strathclyde地區委員會的案件中,上議院拒絕了丹寧勛爵的意見,并認為除非子公司是母公司的虛假外觀,否則公司的面紗無法被刺穿。[6]斯萊德勛爵在Adams v.Cape案中也被剝奪了丹寧勛爵的觀點。斯萊德勛爵認為,基本原則應該是集團公司中的每個公司都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法律單位,擁有獨立的法律權利并承擔單獨的法律義務和責任。
英國法院應該更加關注母公司建立子公司的真正目的。如果集團公司為了欺詐和逃避責任而設立子公司,法院則應當揭開公司面紗并防止濫用有限責任原則。如果這個原則被集團公司濫用,母公司可以通過放棄其子公司而不是履行其法律責任來輕易逃避法律制裁。因此,無辜的公司債權人將無法獲得足夠的救濟補償。這將導致難以想象的不良后果,甚至對整個社會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三、我國法人人格否認制度
(一)立法現狀
中國公司法立法起步較晚,發展緩慢。直到2006年,公司法才首次將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納入成文法。其中第20條規定了公司股東的禁止行為,第64條規定了一人公司的責任。由于公司法規定的相應法規存在許多不完善之處,因此為大量公司逃避法律和逃避責任提供了機會。面對這個問題,許多專家學者提出,在不損害公司制度的兩個基石,即股東的有限責任和法人獨立人格制度的情況下,應在個案中有條理地運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實踐中的案例積累固然是一種好方法,但是中國不是英美法系國家,因為立法環境的差異,中國也不能運用判例法。故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僅在成文法中確立,會在實際運用中造成許多不便及問題。
(二)表現形式
我國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在立法中只有原則性的規定,但在借鑒國外理論及實踐經驗的基礎之上,結合我國法制現狀,采取制定法的方式,在除了《公司法》以外的民法、訴訟法等一般法中做出了相應的一些規定。其中法人人格否認的具體情形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公司資本顯著不足,《公司法》第28條以及31條規定了股東出資不足的責任;虛設股東,以公司形式獲取非法利益;以非法目的虛假設立公司逃避責任;母公司對子公司過度干預;財產混同,業務混同以及人格混同。由此可見,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只適用于公司的獨立人格和股東的有限責任被濫用的情況。它不能適用于公司的正常法律行為,否則將成為公司法的漏洞[7]。
(三)問題及缺陷
中國公司法明確規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但它在實踐中仍然存在問題。法院很難就“嚴重損害”的定義達成一致,而法官對案件的判決主要是基于他們對法律的理解。損害在多大程度上可稱為“嚴重損害”,這個在實踐中都是由個案法官自由衡量。只有在“嚴重損害”的情況下,債權人才能援引這一規定來保護他們的權利,則損害并不嚴重的情況下,債權人就不能引用這一規定了嗎?以及對于母公司對子公司的過度控制,“過度”一詞也并沒有明確的概念及范圍,導致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難以找到合適的標準。另外,在《公司法》第六十四條中,只對一人有限公司的財產混同問題作出規定,但只將公司類型限制為一人有限責任公司顯然是不合理的。如果股東設立母子公司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公司以避免債務,而這些公司的公司財產與股東財產混淆,債權人如何援引第六十四條作為保護其權利的基礎?我國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適用中仍存在著許多問題待解決[8]。
四、我國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完善建議
顯然,英國公司法比中國公司法更為成熟。由于我國不是判例法國家,有關揭開公司面紗的規定僅在成文法中有明文規定。英國發展至今,在揭開法人面紗的適用情形上進行了很多次的變化,在2013年,Perst v.Petrodel的判決中,Sumption J將法人面紗的揭開僅限于兩種情況,首先是“隱藏原則”,類似于虛假外觀;而另一個是“逃避原則”,類似于以合法行為掩蓋非法目的,實屬欺詐。除此之外的情形不揭開事實上的公司面紗,這一案件再次恢復了salmon案件的指導作用。由此可見,中國的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否認情形仍還存在著一些英國法律已經廢除的情形。據此,本文在中國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完善上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完善相關法律規定及指導案例
我國現行《公司法》中并沒有明確列明濫用法人獨立人格具體有哪些形式,實踐中出現什么情況才能適用有關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規定。
在英國法中,當幾家公司實際上是一個經濟共同體時,法院往往會揭開公司的面紗。但由于母公司與子公司的特殊關系,理論上宜將單一經濟實體理論作為揭開面紗的例外。中國法院不能直接排除單一經濟實體理論的適用,而應綜合母公司或控股公司的目的進行判斷。若其目的確實有損債權人的利益,那么這個面紗則必須揭開。我國應出臺司法解釋或匯編適用于這種情況的案例,在實踐中給予法官適當的指導。
(二)濫用公司獨立人格的情形縮減
英國法中的代理即是我國法律認為的過度控制,當股東對公司的控制過度時,則視為公司只是控制股東的代理。但是在實踐中,對公司過度控制的股東應對其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這忽略了股東與公司之間的緊密關系。公司很難真正獨立于股東,因為公司的背后是人在操控,商業經營的本質就是獲取更多利益,股東在經營過程中對公司的控制過度的事實時常發生。在過度控制這一需要否認法人人格的情形上來看,理論在邏輯上是行得通的,但實踐中對于過度控制的界定卻難以區分。若是股東在過度控制中造成了財產混同業務混同等情形,是有必要揭開法人面紗的,但是筆者認為單純的過度控制這是公司生產經營活動中的大概率發生的一件事,若將此作為濫用法人人格的情形之一,那么股東的利益會受到侵害,且股東責任過于苛刻。
五、結論
英國法中揭開法人面紗的原則顯然更加成熟,雖然二者屬于不同的法律體系,但是我國應在借鑒英國公司法的精髓同時,保留自己的特色,求同存異,不能盲目移植。對于濫用獨立法人的情形進行系統規定或出具案例指導是當前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所急需的。例如我國《公司法》在第二十八條和三十一條中規定了股東資本不足的情形,及時履行出資是股東的義務,虛假出資、資本不足、抽逃出資等情形,使公司陷入了沒有足夠資產償還債務的困境,這對于公司的債權人而言是不公平的。以及母子公司作為一個單一經濟實體時,利用這種特殊關系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在實踐中屢次出現。因此出具相關指導案例更能在實踐中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