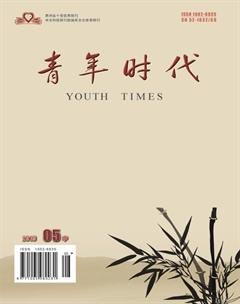談談貶官文化的積極意義
陳惠玲
摘 要:本文以嶺南地區歷史上比較有名的貶官對象為例,探討貶官文化的積極影響,由此促進人們對于貶官文化更深入、完整的認知,發揮貶官文化的價值,將會推動嶺南地區乃至中國社會文明傳統的進一步傳承,引導社會文化向積極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貶官文化;積極意義;嶺南地區
提到中國古代,我們會發現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在歷史上不曾間斷,那就是貶謫。有意思的是,中國古代的封建朝廷,大凡做官之人,幾乎都或多或少地不免要遭受貶謫罷黜,“貶官文化”也由此應運而生。而我想將視角對準自己所在的這片嶺南大地,以幾位代表性的貶官為例,去探討貶官文化在一方水土中所積淀的意義與價值。
古代中國,宦海沉浮,官員稍有不慎,就會遭到貶謫。而官員被貶原因復雜,但最主要的還是因罪或蒙冤而被貶,比如唐代著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就是劉禹錫、柳宗元等改革派因永貞革新失敗,被政敵保守派造謠誹謗而被貶。而流放貶逐之地又多是荒涼閉塞的偏遠邊地,經濟文化落后,尤其是嶺南地區,地處南蠻,古屬百越之地,歷史上開發較晚,常被人稱作化外之地,瘴癘之鄉。謫宦之人,流放被貶,仕途失意,人生也就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與打擊,內心苦悶可想而知。在交通不便、路途艱險、前程未卜的古代,每一次遠行都有可能意味著生離死別,此生可能再難與親人故鄉相見,更何況是被貶到氣候濕熱、瘴氣橫行的嶺南,一路上,官員們都極有可能面臨死亡的威脅。韓愈在《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中即寫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可見詩人對于被貶潮州早已抱著送死的心態,蘇軾被貶儋州,亦做了最壞的打算。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向來是古代讀書人最高的政治理想。而一旦遭受貶謫,對于官員的政治生涯來說將會是巨大的不幸,人生也會因此蒙上了苦難與沉重的陰影。但透過苦痛與悲愁的表層,我們也應看到貶官文化的背后,其實也蘊含著積極的意義與深刻的歷史價值。
貶官群體當中,并非所有人都是賢良之士,都值得我們同情與肯定,但貶官之人中亦不乏德才兼備之士,他們來自文明較為發達之地,擁有較高的文化層次修養,為政一方,為民謀福祉,干實事,政績斐然,為當地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譬如劉禹錫,由京城被貶至筆者的家鄉連州當刺史,在任四年半,勵精圖治,治理社會虛浮的不良風氣,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同時深入民間,與當地的瑤族百姓同勞作,共娛樂,極大地加強了漢瑤兩族間的團結,使連州社會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圖景;當連州出現疫情時,他又向柳州的柳宗元及湖南道州的薛景求援,將好友寄來的救命藥方編成藥書《傳信方》,并廣為傳播,濟世救民,解決民生疾苦。更值得一提的是,劉禹錫在連州期間,重教興文,親自執教講學,開啟了連州一代之文風,當時甚至吸引了荊楚吳越一帶的儒生遠赴連州求學,為連州日后“科第甲通省”奠定了重要基礎。而韓愈貶潮期間,勸課農桑,釋放奴隸,在當地廣施善政,解民困苦,同時興辦學校,培育人才,亦極大地推動了潮州文教事業的發展。海南儋州也在蘇軾的治理下,面貌發生極大的改變,民生改善,文明開化。
曾有人說“東坡不幸海南幸”。或許在許多人眼里,包括貶官他們自己看來,流放被貶是人生之大不幸,但對于當地百姓而言,這些有著卓越才干的官員的到來卻是極大的福音與幸事。正是他們的努力,造福了一方黎民百姓,為當地社會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更深一層意義上,也推動了中原文明在嶺南地區的傳播,使嶺南地區的文明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影響深遠,惠及后世。
許多被貶的官員,其實都是有著深厚學識與較高文學造詣的讀書人,這些文人士大夫在謫宦期間,雖歷經凄風苦雨,顛沛流離,卻始終堅持文學創作,迎來他們文學創作的高峰。他們或投向當地山川景物的懷抱,寄情山水,排解內心苦悶,寫下了眾多燦爛的游記詩篇,或著書論述,思考哲學問題,探究社會人生。貶逐帶給他們的不只是寂寞艱苦的環境,也給了他們平心靜氣的機會,讓他們能沉下心去追問,去思考,在艱難困苦中磨練自己的人格,讓它獲得一種升華,在對人生得失的反思中,積淀思想的深度,從而促成內在心靈與精神境界的提升。
可以說,如果沒有貶謫柳州跟永州的經歷及受此影響而形成的心境的變化,那么柳宗元也就不會寫出像“永州八記”這樣的散文佳作,因為在錘煉的過程中,謫宦的經歷已經成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融入他的思想與情感當中,那些文字也因此方能穿越時空而不朽。而韓愈在宦游途中,除創作出經典的哲學名篇“五原”外,亦留下了大量像《鱷魚文》這樣的優秀詩文。劉禹錫被貶連州期間,寫下15篇散文,73篇詩歌,蘇軾遷海南,為我們留下了《居儋錄》……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或許正如杜甫所說:文章憎命達。中國文人的不幸,卻是中國文壇的大幸。如果沒有貶謫的經歷,也許他們也就不會創造出如此巨大的超越過往的文學成就。與此同時,我們會發現在那些詩文當中,許多都寄托著像思鄉、離別這樣的豐富的情感,承載著他們關涉社會人生的深刻的思考,而這正構成了中國文學永恒主題中的一部分,燦爛的貶官文學流傳至今,早已成為中華文藝寶庫中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曾說道:“中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貶官文化。隨之而來,許多文化遺跡也就是貶官行跡。貶官失了寵,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劇意識也就爬上了心頭;貶到了外頭,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與山水親熱。這一來,文章有了,詩詞也有了,而且往往寫得不壞。過了一個時候,或過了一個時代,事過境遷,連朝廷也覺得此人不錯,恢復名譽。于是,人品與文品雙全,傳之史冊,誦之后人。他們親熱過的山水亭閣,也便成了遺跡。地因人傳,人因地傳,兩相幫親,俱備聲名。”從文章論述的角度來看,貶官文化何嘗不是官員與謫宦之地的一種相互成全?貶謫的經歷其實又何嘗不是貶官們不幸中的幸運呢?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其實亦實現了自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理想。
正如柳州因柳宗元而聞名,潮州迎來過韓愈,連州因劉禹錫的存在更為人所知,惠州與儋州也同樣擁有屬于他們的蘇軾。貶官的到來,留下了眾多物質性的文化遺跡,亦為當地增添了文化韻味與歷史涵養,像劉禹錫在連州建成的吏隱亭,嶺南名園海陽湖,蘇軾在惠州修筑的西湖蘇堤,韓愈的靈山寺留衣亭等等,都成為了嶺南今日重要的歷史文化與旅游資源。但貶官文化的價值卻不只是停留在這些看得見的文化遺跡之上,更深層更本質之處是一種內在精神、品格的貫注與傳承,它會超越時空,深刻影響一方水土的文化涵養與精神傳統,塑造當地百姓的文化性格,正如韓愈被貶陽山、潮州,劉禹錫被貶連州,蘇軾被逐惠州、儋州,他們對于教化的重視發展,促使當地得以成為文明禮儀之地,當重視文教的傳統被延續,必將澤被后世。
“不虛南謫八千里,贏得江山都姓韓。”試想,若不是韓愈身上那種人格魅力的光輝,又怎會讓百姓為他立祠紀念;如果不一心為民,劉禹錫、蘇軾之輩又怎會贏得當地百姓乃至后世人的敬仰與尊崇。
而許許多多像韓愈、柳宗元一般的遷客騷人,也因為類似于潮州、柳州的存在,在困苦的境遇中完成了自我思想與人格的超越,實現道德文章的突破,在成就自我的同時,也贏得了世人的認可、景仰與紀念,成為了今天我們所認知的真正意義上的他們。
當人生的苦難接二連三地到來,當命運的玩笑一次次帶給我們沉重的打擊,我們該如何面對與承受?是保持住生命的達觀,抑或是在頹廢中沉淪?或許,貶官文化可以為我們帶來情感、意志與精神上的啟發。透過那些文字與故事,我們依舊能領略到它們的背后作者所隱含的的人格魅力與人生態度,并從中汲取力量,尋求到屬于自己的答案。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十幾年的貶謫生涯,正是蘇軾政治上最失敗,生活遭受最多苦難的時期,而東坡先生卻能用一種詼諧的語言總結自我,看似自嘲,其實也是對自我的一種肯定,背后的樂觀灑脫、超然物外,令人動容。
一個人倘若有著堅定的理想信念,那么不論他遭受何種排擠打擊,內心也會保持安然,不受影響;由此,我們也就能理解柳宗元立下的“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的心志與誓言,也就會明白為何劉禹錫被貶卻不消沉,相反能在蠻荒之地散播文明,繼續堅定地施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他們的身上,我們會體察到各種關于人生的哲學以及處世的智慧,其中既有儒家的堅持,也有道家的豁達與佛家的釋然。未來的人生道路該如何選擇,以何種心態面對未來,貶官文化其實也為我們的思考和選擇帶來了更多的啟發與可能性。
身處現今這個浮躁喧囂的社會,人們似乎已經缺失了一種耐得住寂寞的品德,過于功利,講求實用主義,渴望功名,卻又不愿忍受孤獨與寂寞,對于人生也缺乏深入的追問與深刻的思考。而貶官文化,恰恰能在這一方面給予我們新的啟迪,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個體人生與社會群體的關系,去反思,去感悟,不斷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有所發現,從而有所改變,有所長進。
在有形與無形之中,貶官文化早已為我們留下豐厚的文化精神遺產。
時至今日,我們越來越需要以一種辯證的態度看待貶官文化,既要看到它所反映的人才受貶、政治黑暗等問題,也能認識其背后的積極意義,而這需要無數人的付出與努力。在對貶官文化進行研究保護的同時,積極開發利用有關資源,促進人們對于貶官文化更深入、完整的認知,發揮貶官文化的價值,將會推動嶺南地區乃至中國社會文明傳統的進一步傳承,引導社會文化向積極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曾紀鑫.韓愈貶潮州[J].同舟共進,2014(11):76-81.
[2]周正,張西愛.應重視海南“貶官文化”的開發利用[J].今日海南,2012(0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