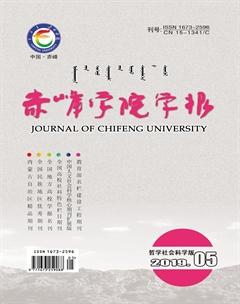法國現代“經典作家”一窺
曾彩虹 盛麗
摘 要:米歇爾·圖尼埃和朱利安·格拉克,同為法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大師,前者被譽為“新寓言派”代表作家,后者則被認為是“超現實主義”在嚴肅文學界的代表。他們看似具體截然不同的人生經歷和各具特色的文學創作,但是這兩位現代“經典作家”在文學批評、寫作體裁、精神追求等方面都有著驚人的相通之處。
關鍵詞:米歇爾·圖尼埃;朱利安·格拉克;“經典作家”;人與自然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9)05-0080-05
20世紀法國文學的主要特征是“離經叛道、標新立異”[1],涌現了大量以“反傳統”“反理性”“反陳規”為標志的革新作品。但是在這種對19世紀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傳統的法國文學進行顛覆的主流之下,也暗涌著對舊世紀的繼承和發揚。目前國內的法國文學研究領域對這個新舊交替時期的作家及其作品涉略甚少,更無從談起對他們進行交叉對比研究。針對這樣的一個空白地帶,筆者選出了兩位極具代表的作家。他們在中國學界的影響與他們在法國顯赫的文學聲譽相比落差頗大,這也反映出國內對該領域研究的缺失。
他們分別是:米歇爾·圖尼埃Michel Tournier(1924年—2016年),法國當代文學大師,被國內譽為法國當代“新寓言派”代表作家。圖尼埃自稱“哲學的走私犯”,其文學創作以“神話改寫”和蘊含深邃哲理為顯著特點。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1910年—2007年),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和評論家,在20世紀的法國被譽為“最后一位古典作家”。其小說具有明顯的散文化色彩和詩化傾向,是法國“詩意小說”的代表作家。
本文試圖從兩位看似毫無交集的人生經歷出發,通過對比兩位作家的寫作風格、文學理念的異同,旨在從文學創作中提煉出他們的哲學追求,以及探析以他們為代表的法國現代經典作家“突破性地繼承了法國小說傳統”[2],但又為了區別于傳統的古典小說時所做的妥協與堅持。也希望能為讀者打開一片新的文學天地,體驗法蘭西文學的多樣性和深層內涵。
一、圖尼埃的格拉克情結
(一)生活經歷
兩位文學巨星都出生于20世紀初,又相繼在21世紀初隕落。相同的時代背景讓他們面臨了許多相似的人生境遇,但各自的價值觀和人生閱歷又讓他們做出了或相同或迥異的選擇。首先,兩位作家的最初志向都不是寫作而是成為教師。圖尼埃在哲學教師資格會考失利后,因為無法達成擔任大學哲學教授的志愿,轉而進入電臺、電視臺及出版社,擔任編輯及制作人的工作。正是不同的職業生涯決定了二人日后面對媒體和文學獎項時截然相反的態度。而格拉克原名路易·普瓦提埃(Louis Poirier),在這個名字的庇護下,他過著與文學界毫無交集的生活。普瓦提埃曾就讀于法國著名貴族學校亨利四世中學,后考入以培養精英著稱的巴黎高等師范學校,主修歷史和地理,畢業后在外省和巴黎的幾所中學教書,直至七十歲退休。其次,他們都是真正意義上“晚熟”的作家:圖尼埃在42歲才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禮拜五或太平洋的靈薄獄》。格拉克雖然在27歲時就發表了他的處女作《阿爾戈古堡》,但他直言在此之前從未想過從事寫作。不過,在發表了第一部作品之后他們都從此筆耕不輟。圖尼埃的一生再沒有放棄過寫作,一直持續到他2016年逝世之前。格拉克也有相同的創作熱情,即使晚年深居簡出,也只是停止了發表但并未停止寫作。厚積薄發,正是之前豐富的閱讀和人生經歷的積累,才成就了兩位作家之后的輝煌。
更具有戲劇性的是圖尼埃和格拉克都在法國最重要的龔古爾文學獎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早在1951年,格拉克憑借《沙岸風云》獲得了這項殊榮。雖然作家本人拒絕領獎,但這并不影響該獎項對其文學成就的肯定。十九年之后,圖尼埃同樣受到了龔古爾文學獎的青睞,憑借《榿木王》這部作品在1970年獲得了該獎項,不同的是他欣然接受了。圖尼埃走得更遠一些,他不僅是伽利瑪出版社的閱讀評審委員會成員,而且在1972年加入了龔古爾學院。此外,兩位作家都與德國有著不解之緣。圖尼埃出生在一個父母都通曉德語的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就深受德語教育及德國文學藝術的熏陶。他在法國取得文學及法學學位后,留學德國攻讀哲學。格拉克因為受到了德國浪漫主義以及超現實主義影響,作品摻雜著怪異的內容以及富想象力的意向。
從他們的生活交集看,雖然算不上交往甚密,但筆者還是發現了一些微妙且耐人尋味的聯系。1950年代,格拉克在巴黎任教時曾住在蒙巴納斯區一條名為Armand Moisant的街上。同一時期,圖尼埃因為沒有獲得教師資格證,開始向廣播行業進發。彼時,他的工作地點就在這條街上。他們也許在這條街上相遇過。格拉克和羅歇·尼米埃相熟,而尼米埃則是圖尼埃的在巴斯德高中的同窗。
(二)圖尼埃評格拉克
圖尼埃在評價格拉克時,對他的文學前輩格拉克充滿敬意。在與米歇爾·馬丹—羅郎(Michel Martin-Roland)的一次交談中,圖尼埃便直接宣稱自己“十分欽佩朱利安·格拉克”[3]。在接受法國著名周刊《快報》采訪被問及最推崇的當代作家時,圖尼埃的回答是且僅是朱利安·格拉克,還補充到他的所有作品都值得去讀。圖尼埃在Initiales雜志[4]向格拉克致敬的特別期刊上發表過的對其高度的評價,認為他是當時在世作家中最偉大的一個,以作家和評論家的雙重身份主宰法國文學已超過50年,并且把法國文學批評的藝術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圖尼埃發現格拉克分析作品總是清晰有力,而且由于對文學深沉的愛他的評論常常是殘酷的。文學隨筆《首字花飾》和《邊讀邊寫》就是其中最為優秀的文學評論。不過對圖尼埃而言,最能展現格拉克才能的是他的小說和旅行筆記。因為人們不會忘記格拉克曾經當過中學地理老師。但是,當路易·普瓦提埃老師變成作家朱利安·格拉克時,他成了一個令人敬佩的最偉大的“風景畫家(paysagiste)。格拉克對一個省、一個地區、一座城市、一條河流或一座山的看法是無與倫比的。作為仰慕者,圖尼埃在2006年再次提及格拉克的文學藝術的豐富之處在于明顯的基調和靈感的統一,正是這種統一成就了他的偉大[5]。雖然格拉克作品主題多樣,但是整個作品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致性。這種類似的嚴謹可和保羅·瓦列里相媲美。在圖尼埃眼中,這一切的關鍵點恰恰在于格拉克首先是一位“風景畫家”,他知道如何看待城市、鄉村、森林、生物以及一個幾乎具有生物統一性的有機整體,其基本特征之一便是純粹的對當前的空間感知。在圖尼埃對于格拉格的評價中,多次提到“風景畫家”一詞,他認為這個詞并不僅僅是對畫家的稱呼,作家也有權使用這一稱號。
于1998年2月28日,在其書庫創建者兼主持人Arlette Bouloumié的提議下,圖尼埃拜訪了當時隱居故鄉圣夫洛朗勒維耶伊縣的格拉克。在通過閱讀神交多年之后,兩位作家終于得以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圖尼埃本人還特別強調過自己的文學評論集《飛行的吸血鬼》與格拉克的文學隨筆《邊讀邊寫》是幾乎同時出版的。兩個看似不同的偉大作家卻有著令人著迷的相似之處,最后,他們的作品都被昂熱大學的圖書館收藏并分別建立了一個圖尼埃書庫和一個格拉克書庫。
二、不謀而合的創作之路
(一)文學類型
圖尼埃首先開始的是長篇小說的創作,于1967年發表他的第一部小說《禮拜五或太平洋上的靈薄獄》。1980年發表了他的第四部小說《加斯帕、梅爾基奧爾與巴爾塔扎爾》。但是他分別于1971年和1983年將這兩部作品改編為更為短小簡悍的《禮拜五或原始生活》和《三王》。這預示著圖尼埃學作的文學類型的轉變,他逐漸放棄了復雜的長篇小說的創作,而是偏向簡練的短篇故事,尋求著一種所有人能懂得更為簡明扼要的語言。相較于長篇小說,圖尼埃更強調故事的重要性。
在《愛情半夜餐》里圖尼埃借主人公之口發表的關于小說和故事的看法,足以窺探到作者對短篇故事的推崇。他認為小說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是悲觀的,而故事是甜蜜親切的。沉重的小說如果開始憑借“真實性”占上風,讓人信服,但是故事最終會因為它的“美麗和力量取勝,最終散發讓人無法抵擋的光芒”[6]。圖尼埃認為《皮埃羅或夜的秘密》是他寫過的最好的作品,因為就連孩童都可以讀懂。他把故事視為一種散文詩,清晰而簡潔的寫作是他的追求。故事和詩歌的相同點在圖尼埃看來就在于其簡練而語義豐富。這便解釋了圖尼埃后期從長篇轉向短片《大松雞》,甚至是《飛行的吸血鬼》這樣的斷片創作的變化。
格拉克的創作也經歷了從前期完整的小說敘述轉向短小的斷片寫作的演變。雖然具體的操作方式有所不同,但格拉克和圖尼埃都很喜歡斷片寫作。圖尼埃還特別強調過自己的閱讀筆記集《飛行的吸血鬼》和他心目中代表文學批評最高水平的格拉克的文集《邊讀邊寫》是幾乎同時出版的。這兩本書都是斷片寫作的代表之作,都體現了格拉克一直強調的文學創作之間的連續性,圖尼埃對此也完全贊成。這種斷片式寫作在格拉克的小說創作中也有體現,是其小說現代性的根本所在:現代小說要求放棄情節,把更少的注意力投入到重大的外部事件和命運的浮沉,因為這些并不能揭示我們所探索事物的本質。相反地,格拉克堅信生活的任何片段,哪怕是隨意挑選的、無論是任何時刻,都包含著命運的整體也都能夠再現命運的全貌。秉持著這樣的原則創作的小說,是可以隨意截取任何片段來閱讀的。此外,格拉克后期的部分作品呈現出鮮明的浪漫主義斷片性,即文學自身的完整性和相對于周圍世界而言的獨立性。《首字花飾》開始,格拉克正式放棄了之前以小說為主的完整敘事,嘗試篇幅短小、一般不超過半頁紙的斷片寫作。這些斷片作品,無論是《路》,還是《邊讀邊寫》都具有自由性和獨立性的特征。
(二)體裁選擇
當我們再次著眼對比圖尼埃和格拉克的具體文本時,就會發現相近的歷史時代在他們的作品中留下了相似的烙印。圖尼埃與格拉克關于德國的交集是與戰爭分不開的——奇怪的戰爭(le dr?觝le de guerre)(二戰全面爆發初期英法在西線對德國“宣而不戰”的狀態)。圖尼埃筆下的穆爾霍戰俘營也許會勾起格拉克一些傷心的回憶,因為二戰期間他正是在這里被囚禁過。這場法蘭西歷史上的“恥辱之戰”被圖尼埃和格拉克分別移植到了自己的作品《榿木王》和《林中陽臺》。
雖然格拉克的童年無憂無慮,幾乎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但他十一歲之后在遠離家鄉的南特中學度過的長達七年寄宿生活卻與圖尼埃在《圣靈之風》中對童年教育制度過于機械和缺乏創新性的抨擊如出一轍。而在圖尼埃的《榿木王》中,占據全書約五分之二篇幅對迪弗熱少年時代不幸的講述也是從他離開家鄉進入圣克里斯托夫中學開始的,這是個即像監獄又像教堂的寄宿學校。格拉克在回憶這段形同監禁的閉塞生活時這樣寫道:“秩序、統一、等級、課程,每天重復著同樣的東西,這是一個殘酷的制度。”[7]也正是這段漫長的學年幽閉生活讓格拉克隊“離開去度假”的想法充滿渴望,并成了其文學創作當中貫穿始終的主題。因為這即是自由的象征也是對單調幽閉的教育制度的反抗。
格拉克的小說雖然大多以戰爭為題材,但從未涉足正面戰場,其筆下的人物大多對具體的戰況一無所知,處在一種茫然的等待當中。在他的小說創作當中,外部事件都是無法確定的,主人公與周圍人和事物的交流才是作者關注的重點。也正是同樣意識到了外部事件在小說敘述中的無力感,圖尼埃完全避開了正面描述《榿木王》故事發生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戰爭雙方的交鋒,轉而將目光投向了始終表現得像戰爭的局外人的主人公阿爾貝·迪弗熱。作品集中描寫了他在戰爭期間的各種內心感受、魔鬼般的直覺,這一切被稱之為“征兆”,并反復強調“一切都是征兆”[8]。這樣的解讀方式也與現代小說提倡通過片段解讀整體的原則不謀而合,格拉克與圖尼埃再一次在現代性方面不謀而合。
雖然具體的表現手法和寫作題材各異,圖尼埃和格拉克都不約而同地在他們的創造中再現了戰爭經歷以及相似的童年感悟。并且他們的創作都從早期長篇的敘事學作品過度到了后期的斷片式評論和自傳寫作。年齡的增長和精力的下降并不是主要原因,這其中更多的是隨著閱歷的積累,對生命的感悟都回歸樸實和本真。
三、圖尼埃和格拉克的詩意世界
(一)積極的人生態度
格拉克看似與文學毫無交集的地理老師的經歷深刻地影響著他的世界觀和文學創作。首先,系統的地理學習使他具備了獨特的觀察環境的能力,雖然并沒有刻意要應用地理學去研究人是如何被他周圍的環境所改變的,但在其寫作的時候本能地關注人和地點、人與環境之間的聯系。景物的描寫在格拉克的作品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不僅調動視覺,還充分運用視覺、觸覺甚至全身的感官去感受周圍的環境,在景物中尋找人物的命運。用圖尼埃的話來總結就是“在他的小說當中,風景重來都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它深刻地影響著人物的行為,甚至可以說它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角”[4]。
圖尼埃和格拉克都處在法國“新小說”盛行時期,但是這兩位作家卻被稱為“經典作家”,他們并沒有一味地摒棄傳統,否定、打破一切,遵循“新小說”近似冷酷的寫作手法,他們在創作中更多追求的是一種積極的價值觀,接受肯定這個世界。贊美生活,熱愛生命,回歸自然,希冀與自然融為一體,這種積極樂觀的人生觀世界觀在圖尼埃和格拉克寫作中完全契合的。圖尼埃在文學評論集《飛行的吸血鬼》對安德烈·紀德進行評價時,劃分了兩類人,一類是肯定生活的人,一類是否定生活的人,并認為紀德是肯定生活的典型代表。“肯定生活的人是難以想象灰色的、可恨的被否定的世界,在那個世界充斥著反自然、憎惡與帶著溫度的、顫抖的和濕潤的生命打交道的種族”[9]。圖尼埃和格拉克在作品中表達的更多是對這個世界的贊歌。圖尼埃在《思想之鏡》將“嘲諷”和“贊美”進行了一個二元對比,相較于前者,他更愿意去頌揚世界之美,英雄之偉大和少女之優美[10]。
(二)追求詩意的生活
如果在圖尼埃前期的作品中,小說的開頭籠罩著灰暗的氛圍,結局則是逐漸明朗歡快走向光明。在《禮拜五或太平洋上的靈薄獄》中,絕望的頹廢的魯濱遜最初在蚊蠅飛舞的野豬浸泡的爛泥塘中打滾,但是禮拜五到來以后便開始了向太陽城的轉變,魯濱遜最后成了自然本原的一分子。但是沉重、黑暗和憂郁色彩在圖尼埃后期的作品中逐漸褪去了,集中體現在他后期發表的Petites proses(1986年)、Célébrations(1999年)和Journal extime(2002年)這三部作品。圖尼埃還曾以幽默筆調親筆寫下了為自己準備的墓志銘:我熱愛你,你給了我百倍,感謝你,生活。這種為頌揚生命、生活和人類的美而寫作的傾向從作品Célébrations(慶祝)這一標題中更是顯而易見。作者對自然、城市、房子、孩子、身體等生活的每一個看似平淡無味的微小的事物都帶有極大的好奇心,對世界的美充滿贊嘆驚奇。細微到對葡萄酒、野草、刺猬等的描述,甚至到稱贊膝蓋的完美,形容它是一種既簡單又復雜,堅硬又脆弱,具有攻擊性和易損性,是力氣、動力和騰躍的關鍵環節。這便是圖尼埃的生存哲學,快樂哲學。
正是由于對地理學的熱愛,格拉克有了很多和大自然接觸的機會,用自己的腳步丈量著法蘭西的大好河山。因為對法蘭西這片土地飽含深情,雖然他的作品都是在戰爭的背景下發生的,但他從不描寫正面戰場,而是關注他的同胞如何在這樣動蕩不安的大環境下開辟“世外桃源”,依然努力幸福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因為從根本上來講,圖尼埃和格拉克都是積極樂觀的人,都是勇敢對生活說“是”的人。這樣的世界觀是圖尼埃能夠與格拉克產生如此大的共鳴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們與薩特的分歧所在。格拉克把薩特定位為對生活說“不”的一類人當中,他的作品雖然都兼具文學、哲學以及政治,但缺少與詩學的聯系。格拉克毫無保留地盛贊薩特是偉大的作家,但自認為無法勝任解讀這樣的鴻篇巨制,并且不符合他的個人文學偏好。
圖尼埃和格拉克都崇尚回歸自然,而二者對人類、生活、世界的積極態度被分別概括成了一種詩意的世界觀:圖尼埃稱之為“宇宙的沖動”,而格拉克則命名為“擬人化的植物”。格拉克的這一概念與帕斯卡爾的“人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的觀念是一致的。他們都承認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但也強調了思想的偉大。因為能夠思考,即使渺小如一株植物,也能戰勝浩瀚的宇宙。
四、結論
圖尼埃和格拉克無論是在生活經歷亦或是在文學創作上看似迥然不同,但這兩位文學大師卻有著意想不到的聯系和驚人的相似。前者擅長神話改寫,而后者以詩意化寫作著稱,在“新小說”的創作背景下仍更多堅持傳統,回歸經典。他們除了長篇小說的創作,都逐漸向短篇,甚至是向斷片過渡。而在他們的作品中,20世紀的時代氛圍在其中留下了類似的時代特征,特別是對于兒童、教育體制的關注,有關二戰的主題選擇,甚至在圖尼埃的《榿木王》中發現了格拉克二戰中的個人經歷的影子,以及德國文化對二者的影響等。他們也深切地關注著人與自然的融合問題,著力于刻畫自然、生活、人類、宇宙之“美”,而非“惡”,積極地面對一切是他們共同的價值追求,也是共同的寫作精神。圖尼埃與格拉克的交集當然遠遠不止如此,但限于篇幅以及筆者能力的有限,本文的意圖是通過這種比較研究向讀者呈現這兩位偉大的經典作家潛在的研究價值,期待吸引越來越多的人關注這方面的研究。他們從未過時,他們仍然具有現代的活力。
參考文獻:
〔1〕劉成富.現當代法國文學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107.
〔2〕袁筱一.文字·傳奇:法國現代經典作家與作品[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2.
〔3〕Michel Martin-Roland.Michel Tournier. Je mavance masqué[M].Paris: édition écritures, 2011.64.
〔4〕Michel Tournier. Rencontre Jeudi [J].Initiales, Revue Groupement Libraire, Paris, 1997 ?Numéro Hommage à Julien Gracq, 1997.9.
〔5〕Michel Tournier. Julien Gracq Avant Toutun Paysagiste[J].Revue.2006.68.
〔6〕米歇爾·圖尼埃著,姚夢穎譯.愛情半夜餐[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34-35.
〔7〕王靜.于連·格拉克和他的《西爾特沙岸》[J].世界文學,1991,(02):153.
〔8〕米歇爾·圖尼埃,許鈞譯.榿木王[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5.
〔9〕Michel Tournier. Le Voldu Vampire[M]. Paris: Gallimard, 1997.228.
〔10〕Michel Tournier. Le Miroir desidées[M]. Paris: Gallimard, 1996.105.
(責任編輯 徐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