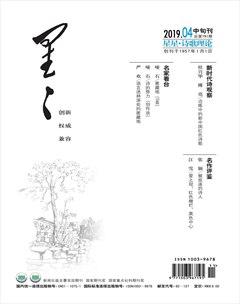傾聽萬物清澈的流漾
黃恩鵬
在詩人清水不多的散文詩作品里,我還是喜歡她的《彼岸的水聲》。因此,我首先就從這組作品談起。這組作品是一個長章。長章難寫,也易流于拖沓。她在寫作的第一時間曾給我看過。就這個長章來說,詩文本所注入的思理是清澈的,有“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感受,也有莊子立于水畔詰問自然與天地生命的存在法則的感受。水,是古詩人常用的意象,比如王維、李白、蘇東坡。我記得當(dāng)時我以“入興貴閑”概說她的散文詩作品整體的澄凈。“入興貴閑”出自劉勰《文心雕龍》之《物色》篇,其云:“是以四序紛回,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從文本法度說,劉勰這段創(chuàng)作論,是說陶養(yǎng)文氣,要以優(yōu)游心境對待;要清心養(yǎng)氣,才能有所感知自然物象所衍生的生命境界。清水熱愛自然生態(tài),關(guān)注人類的生命本源——水,也因此在寫作上,灌注了自然中心主義這一理念。水是生命的喻象,人類與萬物,離不開水。水是距離,廣遠(yuǎn)與精微,都是人的審美鏡像。詩題的“彼岸”,是空間距離形成的維度。這個維度,也可理解為時間的長度。“彼岸”是歷史的指證,或者說文本存在。這樣的一個指證與存在,或是故地的憶想、生命的追問、靈魂的思考。
《水的聲音》先從冬日開始,冬天的水,純凈、清冽,不急不躁,平靜透徹。水的謙卑,也是人的謙卑。從“水”的作為,聯(lián)想到自然品格:冬天。荒林。冷冽的風(fēng)。冰。燈盞。鳥聲。然后進到人的層面:誰在江畔聽濤。可以說詩人這個長章,是一組“問水”詩。她從一開始,就提出“誰能聽到水聲?”“整整一個冬天,是誰穿過荒林,穿過了冷冽的風(fēng),取回那火里的冰?”以及設(shè)置“干凈之水”“江畔聽水”等詩命題。清水是一個聽者,水聲普通,但在詩人耳中,卻不盡然。水聲,哲學(xué)之思,是歷史與現(xiàn)實的逶迤交織。“致虛極,守靜篤,是水的美德”(之二)乃老子之道家哲學(xué)。“水邊躑躅”(之八)乃汨羅江懷沙而死的屈原。“看萬物入水,蕩滌污垢”(之九)乃游歷泗水的孔子。“江畔問月的那個人”(之二)乃對“人生有限宇宙無限”進行生命之問的唐朝詩人張若虛。還有彼特拉克的泉水(之三)和梭羅的瓦爾登湖水(之九)。當(dāng)然,圍繞著水聲的,有鳥兒和草木,亦有人的襟抱:“抵達大海之前,這些卑微之水學(xué)會了更大的智慧和堅強。”(之七)“彼岸很遠(yuǎn)”與“水聲很近”(之十)的喻象辨析,是思想的抵達。這組作品,我想若是以哲學(xué)來闡示,或許有如下幾種釋義:一是對自然萬物的本原或本體生命的悟覺;二是對客觀存在的性質(zhì)或元素的關(guān)注;三是對自然靈魂與人的精神靈魂有效意義對接。這是自然中心主義的本質(zhì)。
大地美好,萬物靜謐。天道,自然道,皆是大道。凡是清純的存在,非凡的存在,也一定有美好的人類道德存在。清水在“美好”的詩意言說里,有意無意契合了荷爾德林“人,要詩意地棲居”或利奧波德“生態(tài)道德決定人的道德”之理念,這種“美好”,也決定了她把寫作視域,放在了對自然萬物深入細(xì)心的觀察上。從一株小繡線菊到一朵小紅耳鵯,從一滴懸墜的雨到一脈細(xì)小的溪流。從一小片兒月光到一朵白云。從一尾魚的喋語到一群魚的荒蕪喧囂。從一截火焰到一小段雷電的長度。萬物之謎,皆可入詩。莊子《齊物論》中提出了“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審美命題,與“人與天地精神同往來”之大生命觀瞻是相同的。事實上,“物化”的詩歌本質(zhì),以及與自然天地相通與生命氣象的氤氳感,是創(chuàng)作中的精神因素。對“本我”來說,與世界本質(zhì)相聯(lián)類,或可用物化、物忘的觀念,加以貫通。那么,讀瞬息萬變的天地,便渾然忘記自身的存在。在一章好的散文詩文本里,通采精微之筆,是促成廣遠(yuǎn)之勢的必然。清水在把握語言與意義生成的節(jié)奏上有著女性獨有的矜持。她不鋪排、不拖沓、不累贅。收放有度,見思即止。寥寥幾句,已然將物象之喻收入觳中。她的身邊皆有清澈之水,她的耳畔無處不是水的聲韻——在煮茶的時光里聽水、在鳥鳴聲里聽水、在細(xì)小花朵下聽水、在舊物的憶想里聽水、在漂動的蓮蓬下聽水、在清涼的月光下聽水、在芊芊草木下聽水……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
《旅程》:“一些水馱著月亮涉風(fēng)行走。”“水的絲綢剛剛織成,初雪喂養(yǎng)在織錦里。”“你忘記了種種痛楚。除了徹底不息的水聲,你聽不到任何聲音。”水的旅程,更是人類的腳步循著的正途。循著自然的腳步,定有美好的天地。《卑微之物》:“稍不留神,一些卑微之物轉(zhuǎn)眼就變成了金子。”對低微之物,不以人類為中心來言說,是整體的生命意識,是人性與自然的合拍。我們有時候恰恰自以為大,丟掉了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一些寶貴的,就是被我遺棄的“金子”。《失眠》:“難以入睡的身體,多么需要一場雨!驚慌的鳥群,徹底未眠。”人是需要內(nèi)在覺醒的。海德格爾關(guān)于“敞開”與“遮敝”之辨,須要仔細(xì)咂味。詩人以對自然和人生那種深切的關(guān)懷與敏感的審美觸角,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藝術(shù)價值。于是以頗具新鮮感的筆觸予以“陌生化”呈現(xiàn),將平素所熟悉的物象,以特征化的細(xì)節(jié)表現(xiàn)出來,使被“遮蔽”的事物,得以審美地“敞開”。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詩意的“敞開”,讓人發(fā)現(xiàn)了令人訝異的美。《夜釣長江》:“夜釣長江。魚群在大水里潛伏。沒有一枚燈光。星星已經(jīng)把江堤照亮。”大寫意式的夜之景象,抒情的畫卷。雖是寫夜晚之釣,卻是鋪展開的亮色。萬物一體,融天地大境,有著神巧的渾灝之氣。那么詩人所創(chuàng)化的意境,就一定要有董逌所言“圣人以神運化,與天地同巧。寓物賦形,隨意以得。蓋自遠(yuǎn)造中,筆驅(qū)造化,發(fā)于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是隨所遇而見”的藝術(shù)品格。從而,能讓散文詩的言簡意深,更為突顯。《大禹渡夜晚的水手歌唱》或許更像一章小敘事文本:“聽我說吧。用一棵樹的沉默。說一條通往我們的路。說黃河的渴刺穿了肉體。沒有十萬行兵策馬白草。沒有咆哮的滾滾的怒濤。黃河,正以她最大的平靜隱忍在遠(yuǎn)處。”冷熱抒情掌控得當(dāng)。詩人在靜謐之夜,聆聽著樹、黃河、堤壩,將巨濤與風(fēng)暴納于胸懷,正是以小喻大的理念的貫徹。
清水是一位純凈的寫作者。很顯然,她將創(chuàng)作視角放在了自然天地之間。讀與寫,兩者從來是不分家的。她研讀愛默生、梭羅、蕾切爾·卡遜、約翰·繆爾、亨利·貝斯頓,以及我國唐代山水詩人、大旅行家徐霞客的游記散文,她為著名畫家徐賢佩先生創(chuàng)作的《葵花童子》系列所配的散文詩,是她的靈心浚發(fā)之作。她從諸多的自然本真的意境里撈取清澈,從諸多卑微的事物里讀到了高貴與不凡,從中穎悟到自然大境所衍生的精神靈魂。這是可貴的。“生命游歷同時也是精神宗教”(后記)。如此,我讀她的文字,感受一種精巧打磨的詩魂,一種唯美的浪漫主義。這種以“自然中心主義”為理念的創(chuàng)作,正是我們的散文詩稀缺的,也正是能慰藉我們內(nèi)心的好作品。我真誠期待清水在今后創(chuàng)作中能更好地突破自己,在天地大境里放飛出更多更美更自由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