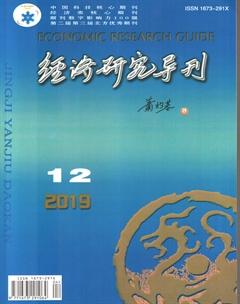列斐伏爾空間生產視域下的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原因探析
黃煥漢 郭雅玲
摘 要:隨著全球化不斷推進和深入,資本主義為內在動力的現代化和城市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改變的普遍性過程。在中國以現代化為引領的城市化進程一路高歌猛進的當下,空間生產在中國成為一項重要的社會實踐,空間化的問題日益凸顯,因此不得不面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有著共性的歷史語境和現實矛盾。借助列斐伏爾的空間批評理論,反觀中國的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原因,或許可以為中國城市化的過度快速化提供一些啟示。
關鍵詞:空間生產;城市化;資本主義再生產;社會關系;意識形態
中圖分類號:F299.2?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19)12-0121-04
2017年初,國家統計局公布2016年多項宏觀經濟數據。其中,城市化數據顯示,從城鄉結構看,城鎮常住人口79 298萬人,比上年末增加2 182萬人,鄉村常住人口58 973萬人,減少1 373萬人,城市化率高達57.35%。中國城市化步入史無前例的高速發展時期,其實從2011年以后城市化率超越50%,2015年增至56.1%,發展如此之快,不能不令人震驚。同樣令人震驚的是我國城市化的超速發展使得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在短時間內流入城市,直接導致城市人口擁擠、住宅問題、環境污染、食品供應、城中村和城市邊緣人口等問題。與此同時,中國鄉村由于污染企業的進駐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加上青壯年外出帶來系列問題,如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等問題,造成農村的日益凋敝和萎縮。雖然城市化被定義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被定義為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但中國的快速城市化面對的種種問題顯而易見,如此中國城市化的模式當下就在持續,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似乎難以擺脫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這一角色。本文將分為三部分對其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原因進行探析。第一部分,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第二部分,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原因;第三部分,中國城市化的啟示。
一、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論
1.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論的提出。20世紀早期之前,馬克思的社會關系生產和與再生產辯證法理論闡釋了資本主義對勞動的剝削和基本生產資料的再生產是其發展的主要方式。20世紀初,盧森堡通過資本積累理論,闡明了資本主義依靠非資本主義的獲得生存和發展的關系。20世紀中期以后,列斐伏爾在他的《日常生活批判》里,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再生產的領域已經入侵和延伸到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早已不再局限于經濟生產過程中,欲望和身體都被控制和操縱,資本主義也實現了其自身的合法性的生產與再生產,使得無產階級認同了其經濟及利益、資本主義關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局限于無產階級起來反抗資產階級的斗爭已經成為不可能。列斐伏爾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他的社會批判理論轉向了空間,資本主義對日常生活的控制只不過是空間控制的一部分。他用空間性容納了日常生活、異化及城市化的問題,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榨取剩余價值的主要方式轉向了空間剝削。列斐伏爾提出了空間生產理論,在筆者看來這正是列斐伏爾把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語境要求當代化了。
2.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論。列斐伏爾在《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中指出:“空間的生產……主要是表現在具有一定歷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擴張、社會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間性組織的問題等各方面。”[1]列斐伏爾提出的空間生產指的就是空間本身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包括城市空間生產、區域空間生產、全球空間生產也包括抽象的空間生產。他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解讀空間,并對資本主義再生產機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空間的生產可以與任何商品的生產相比。”[2]馬克思在《資本論》的開頭就為我們揭示了財富在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主的社會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聚集,而“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商品開始”[3]。因此當下的空間生產,空間成為商品并不是什么新的生產方式,而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圍繞實現空間的生產,而鋪設的道路和地鐵、物流等網絡及技術發展正是服務于空間的生產,或者可以說是使得空間生產得以實現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人們長期忽視了空間,是由于“事實上,污染、環境、生態與生態系統、發展及其后果,把關于空間的問題粉碎并掩蓋了”[2]。空間生產并不等同于商品商品生產,“空間從來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蘊含著某種意義。”[4]空間對社會成員來說是一個支配性的、征服性的、權威性的空間,甚者我們可以把“死亡被拋到了我們身后”[2]!這正是由于人們對自然的脫離,或者城市空間對自然的隔絕帶來的后果。人們幾乎或者很少想到某個時間我們最終死亡而回歸自然,對自然的無情掠奪和傷害,甚至不顧或是沒有想到我們的后代如何面對滿目瘡痍的環境。列斐伏爾把空間和社會關系作為他研究的重點,通過對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關系的研究揭示資本主義如何通過空間生產暫時克服危機并取得經濟增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不僅是為了剩余價值的榨取,更是為了勞動力的買賣關系的繼續交易而生產,以及資本流通過程中的全部關系的生產。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異化及其在生產本質上由對勞動的控制轉至對空間的控制,對人身體的控制,在列斐伏爾看來,“空間的生產,開端于身體的生產。”[4]城市化的實質是對日常生活的現代性空間化,空間化的戰略使得資本主義成功生產了其再生產關系,這樣導致的一些社會關系的形成同時一些社會關系的瓦解,加上通過對空間的抽象化和神秘化使得人們始終處于被意識形態蒙蔽的狀態中安穩地為資本積累服務。
3.空間生產的特點。“人們處理空間,也就是住宅單元的方式,是讓他們恢復均質性,可以和他們部分比較,因而也可以交易。”[2]可見,空間生產的第一個特點便是均質化。為了實現空間的商品化,把一切存在物均質化,即把空間變換成無特色、無內涵、風格一致單調無奇的符號和人造景觀。第二個特點是符號化。資本主義生產大量符號和圖像。把馬克思揭示的商品拜物教轉變為符號拜物教。人與人的關系通過物與物的關系體現,由此人們滿眼看見的都是“等價物”和“物”的價值,而價值被“等價物”和“物”完全遮蔽了,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拜物教的奧秘所在。列斐伏爾也正是看到了當下資本主義把商品轉變成了符號和圖像,通過對符號和圖像的控制實現對人的身體和欲望的控制。第三個特點是暴力化。在抽象空間的符號背后隱藏的是知識和暴力的控制。人從出生到死亡,身體到思想,都由龐大的知識和權力網絡控制。“暴力內在于抽象空間及其使用之中。”[4]
4.空間生產的矛盾。空間生產的均質化、符號化、暴力化衍生出空間生產的另一類特點:空間的分離化、碎片化以及等級化。“作為空間,和空間一道,被分成了碎片,被分割了。”[2]這種碎片的和被分割的空間買賣方式,是與資本主義的分散性組織形式和分散性權力相一致的,通過資本主義的競爭方式實現了不同空間的商業化和分割買賣。最終空間生產創造和強化了空間的不平衡發展,而空間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積累的內在要求。因此,在資本條件下,空間消費表現為空間生產的要素,空間生產體系決定著空間消費體系。空間消費標志著消費者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名望。空間成了區分社會階層和等級的標志,實質是空間的社會關系的生產,勞動者在進行空間消費的過程中接受了空間化的意識形態——空間的區分、空間的隔離及空間的差異和歧視,進而勞動者接受了資本的合理,誤以為資本和勞動的對立不存在了。早期的資本主義矛盾焦點集中在工資與利潤,馬克思在《資本論》通過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利潤和工資的矛盾,從而讓我們看清楚了資本與勞動、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列斐伏爾指出這些矛盾在空間生產中被拋棄了。如今并不是說矛盾不存在,而是時代發展的變化,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實現方式和作用機制也發生了變化,通過把空間和空間里的一切轉變為商品,出現了空間矛盾——資本主義對空間進行等級結構性控制和占有并把空間同質化、碎片化為商品,以至于商品如此富足的同時,對于大多數社會成員來說卻是物質匱乏的;以至于之前的空間被摧毀,時空聯系被中斷,環境被破壞,而這必定激起底層民眾的不滿。資本主義通過地價的調節、城市房租的榨取和城市空間的控制和生產等空間行為,獲得的剩余價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這種剝削比對勞動力直接剝削更為隱蔽,程度更大,通過空間生產、控制、隔離和差異化,制造空間的不平衡發展,形成空間的競爭,必定導致尖銳的空間矛盾。
5.空間生產的實質。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空間生產并不是依賴資本主義制度而存在,空間生產可以與各種制度相結合,而資本主義把空間生產極致化和對空間生產的控制,使得在21世紀的今天和未來的很長時間內資本主義制度依然強大。資本主義空間的生產策略便是在多層面上對中心和邊緣進行區分,制造中心和邊緣的差距,使得邊緣不斷向中心聚攏。在中心飽和之后,新的中心不斷被復制,城市化便是制造中心和邊緣差異的空間戰略的實踐形式。因此,通過對空間的意識形態和空間矛盾的揭示構成了列斐伏爾把握空間和社會關系的研究重點,不同空間的關系其實是不同的社會關系,列斐伏爾指出,“社會關系的生產和某些關系的再生產。”“空間變成了這種再生產的場所,包括都市的空間、娛樂的空間、所謂的教育的空間、日常生活的空間等等。這種再生產通過一種和現存社會相關的方案來完成。”[2]不同的階層,占據著不同的空間,不同空間由不同的利益群體控制,由此使得社會空間成了空間等級的支架。列斐伏爾在空間生產中指出,社會主義并非單純的是國家政權的更迭、公有制的實行,建立社會主義新國家,單純改變制度,是無法解決人的異化、生活空間異化及國家政治權力異化的問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的日常生活異化及政治經濟思想異化,同樣與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令人震驚。總體來說,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創造出新的生活模式,發展主義價值觀下的壓迫和壓抑,只能讓人想到“剝削”這兩個字,更沒有創造出新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一切宣傳口號變成符號,而符號背后卻沒有實際意義。空間發展的不平衡必然會引發以追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發展主義中心論,生態環境的惡化,發展的不平衡,貧富差距,空間的隔離和分異等空間問題的產生導致階級矛盾以空間矛盾為突出表現。城市的規劃其實是空間的隔離,嚴格的空間區分,為的是使權力保持在一個禁閉的空間中進而排斥和驅逐非權力者,同時使得不同空間里的人相對固定,甚至是互不來往,便于權力者觀察和控制,整個井然有序的城市是實行等級結構空間占用、區分空間、控制消費的的統治機器。
二、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原因
中國的城鄉發展在21世紀朝著更加不平衡的方向發展,隨著城市化快速推進,農村的日益衰敗和萎縮。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從另一個視角闡釋了中國快速城市化的原因。
1.資本主義榨取剩余價值的主要方式轉向了空間剝削。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矛盾及環境能源的緩解是建立在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能源被破壞和榨取、經濟利益受損的基礎上的。空間的控制和占領才是獲取最大和最全面剩余價值的有效手段。資本空間的擴張和掠奪行徑導致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被嚴重侵害及全球環境的加劇惡化。發達國家將其內部畸形的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的后果向外部轉嫁,這種轉嫁具有明顯的對外擴張性,憑借購買力和市場化的手段,大量購買和消費區域之外的,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土地資源、水資源,以及女性。這種擴張緩和了發達國家內的農業和農村問題,卻侵蝕了區域之外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這便是發達國家的空間占領和控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系。”[5]落戶,創業,建立聯系的目的是占領空間,造成空間發展的不平衡,用“城市—鄉村”“發達—落后”“中心—邊緣”“富裕—貧窮”“大都市—小城市”等符號為空間貼上標簽,進而為榨取剩余價值而進行空間轉移。核心和邊緣不平等是空間剝削帶來的直接產物。在鄉村,落后地區、邊緣地區、貧窮地區在生態環境被破壞,資源枯竭之后幾乎處于絕路,不僅失去了原有的優勢(環境或資源或傳統文化),也沒有現代化的前景,反而淪落為依附性的地區。“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世界體系的構建其實資本主義所塑造中心與邊緣的空間結構關系,發展中國家陷入了空間結構體系,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隨著資本發展和擴張,尤其當本國的官僚與資本與外國資本利益密切聯系時,空間生產本身及其內部的一切自然成為他們搜刮剩余價值的來源。不可否認,邊緣國家也同時得到發展,但發展是扭曲的,最明顯的事實便是本國的生產大部分是為了滿足出口,滿足發達國家對原材料的需要,索取也由城市伸向落后的鄉村和城鎮。中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就是在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及資本主義的空間占領和擴張下進行的。
2.空間生產造就的空間發展不平衡促使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主義主導下追趕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工業化才能產出更多的GDP。我們看到的是名目繁多的開發區和工業園,提供給跨國公司和企業的投資優惠措施也紛紛出籠,農業和鄉村發展都必須讓路給工業擴張。為了GDP的增長,可以將農業用地變為工業,因為商業和建設用地在同樣面積的土地上建設工廠、住宅樓或商業設施,要遠比農業經營創造出更多的GDP和稅收。只有把空間均質化、碎片化才可能把空間轉化為商品,因此需要單純以經濟效用和稅收等經濟尺度來衡量土地,需要考慮社會文化傳承,以及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多元價值,需要重新把空間變為單調無內涵的可以衡量的商品進行銷售。這樣一種大規模的城鄉改造運動,使城市化搭上高速列車,不僅使中國城市和農村地區的自然和文化景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也預示著相當數量的中國社會成員只能擁有“小區”里的“住房”,而喪失掉多重意義的“家園”。城市化,不是城市戰勝農村,而是城市和農村同時被改變,是城市和農村的時空中斷。
3.空間的不平衡發展和分異以及空間生產對身體和意識形態的控制使得城市對農村的勞動力者有著強大吸引力。一方面,農業經營已經不足以維持新的社會狀況下農民的生存經濟,而必須通過“打工”來彌補的今天也導致大量農村人口的跨省區流動。中國城鄉的差距的懸殊,消滅農村,正是空間生產的必然要求,而現代化則是空間生產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表面上看來農村人向往城市,所謂的主動和合意,表面上看來是有不斷擴大的城鄉差距自然催生的自主性合意,但是,考慮到差距的擴大主要有從革命意識形態到發展主義信仰主導下的制度和政策所引起,它實際上帶有強制性。作為主流話語的生產者和傳播者的知識分子,高度“現代化”了的文化精英們將其信仰和價值標準不斷進行灌輸和滲透,也使得農民青年人受到影響,從而進一步表現出強制性的特征。城市代表的符號對于農民青年來說就是發達、富裕、成功,而農村所代表的符號則是落后、貧窮、失敗。
三、中國城市化的啟示
1.“詩意的生產”。列斐伏爾提出“詩意的生產”——生產出“人的類存在的空間”——將摧殘身體,扭曲身體,打亂身體節奏的所謂理性知識等變為詩歌和音樂,舞蹈和戲劇的詩性知識,因為這些藝術形式是人們內心情感的真實表達,是沒有被抽象空間異化和扭曲的美學體現。“人的類存在的空間”的生產是合乎人生存的狀態和節奏的空間生產,讓身體的生物節奏不再處于混亂和無序;讓身體不再被過度消耗或過度追求瞬間、短暫的快感;或是為了迎合比賽、審美的需要發生改變,導致身體的嚴重摧殘和生理、心理疾病。2010年中國睡眠研究會的調查顯示,從全國各大醫院門診統計,中國內地成年人中失眠患病率高達57%,工作人群中有65%的人存在睡眠障礙,這個比例已遠遠超過歐美等發達國家。2012年世界知名辦公方案提供商雷格斯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壓力最大的國家。這份調查還指出,如今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過勞死”大國,一年過勞死亡的人數達60萬。巨大的工作壓力是導致過勞死的主要原因。壓力背后便是資本控制的欲望和身體。城市化、現代化、商品化、信息化等過程似乎導致同一結果——自然界和人的身體在被“摧殘和掠奪”后的“好處”是可以花錢來修復和治療的,比如水污染了,很快有了工業產品——礦泉水(裝載在塑料瓶里水是否同樣也被瓶子污染,或在水在運輸和裝載過程中也被污染);身體整容失敗了,可以再整形。因此,“詩意的生產”和目前所進行的快速的城市化是不同質的兩種空間生產。從人的身體到精神層面上對空間生產提出社會主義空間要求——應該符合人身體的需要,而不是任由資本空間生產中的肆意妄為。
2.城市化的發展注重社會發展而不是片面追求速度。經濟增長和社會的發展,被人們誤解為是一致,認為總是相互促進的。事實上,貧窮和自然環境的迫害和資源枯竭等問題并沒有阻礙經濟增長,但社會是否發展了?列斐伏爾指出:“人們把它們混為一談,認為增長帶來了發展,認為數量遲早會帶來質量……增長意識形態涉及死亡……人們帶著一種堅定的樂觀主義,相信生產和生產力的無限增長……帶著同樣的樂觀主義,人們還認為,這種經濟的增長遲早會讓所有的欲望都得到滿足:物質的和‘精神的。”[2]這是人們低估了資本的欲望,因此他說:“人們應該做的,是在減少生產的過程中,為其制定方向;人們應該把增長的方向,指向社會的質量的發展……發展和增長并不是同時發生的,增長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發展。因為那些和發展相關的因素……不創造一個合適的空間,就不能夠創造形式和社會關系。”[2]而快速城市化當然推動了經濟快速發展,建筑業顯然成為了領航的產業,但是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與城市化的差距拉大,也是我們不可否認的。由于筆者無法提供確切數據證明,但從城市化帶來的問題(上文已經提到或者還有沒提到的)我們可以確定地提出城市化應該減速,重點不在速度,而在質量,社會發展的質量,至少列斐伏爾很久以前就發現了一點:“最清醒的那些美國人,他們已經放棄了無止境地追求”[2]。
3.改變城市化的發展模式是放慢速度的關鍵。中國的城市化目前必須停下不計代價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此模式只會導致嚴重的工農失衡和城鄉對立。工業化的發展需要原材料和勞動力。土地、勞動力、空間都進入流通領域成為商品,列斐伏爾指出:“在產品的普遍化面前,所有為作為一種作品的城邑帶來活力的東西,都消失了。”[2]過度的城市化,農村社會凋敝,大量移民的擁擠城市,同樣也是城市的危機。因此,城市化高速發展,帶來了的問題,絕不是“現代化”可以解決的,列斐伏爾認為未來的斗爭和反抗就發生在城市中心。“工業已經在事實上表示為非城邑或者反城邑的了。”[2]工業發展通過展開對空間的資源利用,勞動力的剝削而實現。城市越膨脹,城市化速度越快,只能證明空間化過度增長,農民轉變為無產者的速度更快。城市和鄉村同時遭受到了破壞。進一步而言,空間經濟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社會關系越來越來分裂。原有的農村共同體被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分裂過程,分裂的現象對國家原有的制度和空間都是威脅。因此,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生產一種新的空間制度,目前出現空間問題其實也是對原有的空間分裂和破壞的反映。什么制度?與空間生產相適應的制度。城市化的過快過度發展不僅是環境生態、自然資源無法承受和遭受破壞的單純問題,資本對空間的控制所形成的結構化等級社會將威脅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空間生產從來就是帶有經濟性和政治性的。
參考文獻:
[1]? 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 [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與政治[M].李春,譯.北京:世紀出版社,2005:2-110.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5.
[4]? The Production of Space,Heri Lefebvr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 Smith[M].Blackwell Publishing,1991:154-298.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