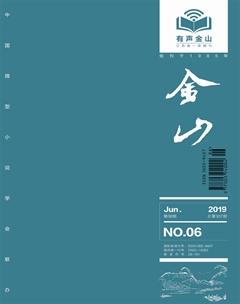跨越半個世紀的書緣故事
嵇鈞生,鎮江人,祖籍揚州,曾就讀于鎮江穆源小學和省鎮中,196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中國航空精密機械研究所研究員,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及國家級、部級科技進步獎一、二等獎多項。出版《光學工具技術》《英漢光學術語釋義詞典》《鎮江淪陷記》及《風雨人生路——嵇直紀實傳奇》等專著。在《瞭望》《中華讀書報》《博覽全書》《炎黃春秋》等多家主流報刊發表各類文章百余篇。
在 風景秀麗的江南,長江和大運河的交匯 處,有一座歷史古城,著名的金、焦、北固三山名勝古跡吸引了眾多的文人墨客,京滬鐵路由此通過,發達的水陸交通又使她成為大江南北、長江中下游的一個商業重地。民國時期,她是江蘇省省會,因此也是一個政治文化中心。這個城市就是鎮江。
八十多年前的抗戰前夕,在鎮江繁華的西門大街上,有一家“鎮江書店”。書店三開間門面,寬敞明亮,書的品種很多,新文藝書更是琳瑯滿目。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書自不必說,其它如現代、良友、新中國、開明及文化等出版單位的新書也是應有盡有。一些成套圖書如生活書店的“創作文庫”“小型文庫”,良友圖書公司的“文學叢書”“良友文庫”,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學叢刊”“文化生活叢刊”,也多有陳列,吸引了許多讀者。
在眾多的讀者當中,有一位小學生是這里的常客。他只有十三四歲,個子雖小,卻聰穎清秀。每天放學路過,他總要到這里來轉轉。小學生沒有多少錢,過年節省下的壓歲錢、開學時節省的文具費以及每天早飯省下的兩個銅板,只夠每周買一期韜奮先生編的《大眾生活》和《生活星期刊》,遠遠不能滿足自己的求知欲了。渴求知識的少年便把這里當成圖書館,每天放學后就站在書店的書架前,看完一本又一本,像張天翼的《蜜蜂》《團圓》,茅盾的《春蠶》,巴金的《砂丁》《電椅》,施蟄存的《上元鐙》《梅雨之夕》,穆時英的《南北極》等書,以及巴金譯的《俄羅斯童話》《門檻》,都是站在這里看完的。豐富的文學乳汁滋養了這位少年,小小年紀就在報刊上發表《春曲》《夢》《旅人之心》等許多篇頗顯文學才華的散文。當時誰也沒有料到,這位名叫范用的少年,當時鎮江穆源小學的小學生,后來會成為三聯書店總經理、海內外知名的出版家。
少年的勤學精神感動了書店的一位名叫賈福康的店員。賈先生長范用六七歲,當時約20歲出頭。他不但不趕走白看書的范用,還常常給范用介紹好書,討論文學藝術,談學校生活以及當時的國難大事,他們成了忘年交。
不久賈先生到國貨公司文具部當店員,那里也兼賣雜志,于是范用也跟了去,如饑似渴地閱讀《光明》、《中流》、《讀書》半月刊、《生活知識》等雜志。
1936年夏,范用小學畢業后考上了江蘇省鎮江中學,但不久日寇對鎮江狂轟濫炸,他的母校穆源小學以及鎮江中學全被炸成了廢墟。學上不成了,他在柴炭巷的家在又一次轟炸中燒毀。1936年10月底,外婆便給他八塊大洋,讓他獨自一人登上西去的江輪。就這樣,他帶著國恨家仇,走上了逃難之路。幸運的是,當他淪落漢口時,結識了后來成為我國出版界著名人物的讀書生活出版社的黃洛峰、趙子誠等一群革命青年。從此,15歲的范用在這些大哥哥們的帶領下走上了革命道路,開始了他一輩子從事的圖書出版發行事業。
不想,在武漢范用又巧遇逃難來的賈先生。范用便將賈先生引薦給黃洛峰經理,于是賈先生也到了讀書生活出版社。只是不久賈先生報考了抗戰工作干部訓練團軍校,離開了漢口。從此兩人天各一方,奔波動蕩,失去了聯系。
時間飛快流逝,一晃半個世紀過去,到了1992年4月,詩人戴天從香港給范用打電話,問是不是認識一位姓賈的鎮江老鄉?原來詩人在臺北《聯合報》副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提到了京城出版家范用“范老板”,賈先生正好看到,便向副刊主編痖玄先生打聽:“文中所指范用是否尚存?是否知其下落?”并說“本人與他過去有很深厚的感情”。從此50多年前一個小學生和一個青年店員因書結成的情緣又因文而續了。賈先生在給范用的信中說:“憶昔約為1934年前后,我們相識于鎮江書店,每周六,你必來買《生活周刊》,那時你在我印象之中,是個好學深思的清秀少年。我也不過二十二三歲。”當他們終于在北京見面時,都已是子孫滿堂的耄耋老人了。他們十分珍視他們青少年時代結下的書緣,他們都有著豐富復雜的人生經歷,真是有說不完的話。
原來,賈先生在受訓后,被分配到軍委會政治部(部長陳誠、周恩來)第三廳(廳長郭沫若)軍報科政治部,以后被派到西北辦報,一直從事新聞事業,1949年去臺灣后教書,早已退休。
1997年4月,范用應邀到有80多年歷史的母校鎮江穆源小學訪問,筆者陪同前往,賈先生也正好回到鎮江。我親見了兩位老友跨越半個多世紀,重新在故鄉相逢再續書緣情的熱情場面。彼時他們都早已退休,但仍在努力為社會作貢獻。范用仍然關注于他一生從事的出版事業,經常發表一些美文,并出版文集。幾十年來,他一直從事為別人做嫁衣裳的出版發行工作,只有在退休后,他才有時間進行筆耕,把他的童年故事、人生心得以及新中國出版界的許多軼事娓娓動聽地告訴讀者。而賈先生作為一位回民,更多地致力于宗教文化的研究,出版多部專著,并發表了多篇關于家鄉鎮江的伊斯蘭宗教歷史的著作。他還團結海外的宗教界人士,關注家鄉的宗教文化事業,多次回故鄉訪問。
范用生前不止一次對我說,他上省鎮中只有兩個月就棄學逃難了,所以他的最高學歷是小學。但是由于他在鎮江穆源小學受到了老師的良好教育,又遇上像賈先生那樣愛書人的幫助和鼓勵,致使他終于成為一位杰出的作家和出版大家。如今兩位老人都已仙逝多年,每當我回憶起他們深有教育意義的圖書情緣故事,都會深受感動,并期盼我們都能從中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