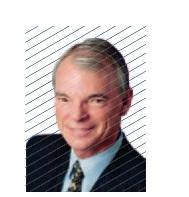超越現有的失業衡量標準
邁克爾·斯賓塞
在二戰后的大部分時段,經濟政策都集中在失業問題上。大蕭條期間的大規模失業,對至少兩代人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但就業只是福利的一個方面,而在當今世界,光實現就業是不夠的。
二戰與1980年之間的增長模式基本上是良性的。其間雖然出現過經濟衰退,但失業率持續維持在低水平。勞動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逐漸提升,尤其是中等收入群體實現了更大程度的繁榮和向上流動。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央行的任務也很簡單:維持充分就業并控制通脹。
這種關注失業率的思維方式如今仍然存在。比如針對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的討論,就反映了人們對技術性失業的憂慮。美國經濟被認為相對健康,因為失業率處于歷史低位,增長溫和,通脹也受到了抑制。
但幾十年前的良性增長模式已不復存在。有些經濟體的主要問題是增長和就業。在一些處于初期階段的發展中經濟體,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就業增長,這樣才能為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以及傳統部門的窮人和未充分就業者提供機會。
然而,就業只是第一步。在現代經濟中,就業的挑戰是多方面的,受雇勞動者在諸多領域都潛藏著一些重大問題,包括就業保障、健康與工作/生活平衡、收入與分配、培訓,流動性和就業機會。因此,政策制定者應該超越簡單的失業衡量標準,考慮影響福利的就業的許多方面。
以就業保障為例。每個快速結構性變革時期都會創造、破壞和轉變就業,就業所需要的技能也會發生變化。即便這些勞動者沒有失去工作,他們的福利也可能因對失業的憂慮而受損。在此背景下,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服務的設計和覆蓋范圍就變得更加重要。但一些政府和公司非但不支持社會安全網的構建,還試圖通過將醫療保健、養老金和失業保險等福利相關職能外包出去以節約資金。
就業挑戰的另一個方面來自于收入。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都出現了就業和收入兩極分化的模式。由于大量低技能工作被轉移到國外或自動化,導致進入非貿易經濟部門中非自動化工作的勞動力數量增大。低技能勞動的邊際產出較低,加上有效集體談判機制的減少,加劇了收入不平等。
就業挑戰的第三個方面是公平。大多數人都明白基于能力和偏好的差異,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并無法產生完全平等的結果。但如果要民眾廣泛接受這種不平等的存在,就要求它是溫和且以績效為基礎的。而那種基于特權或非績效性機會和報酬的極端不平等具有社會腐蝕性。
這就與第四個問題密切相關:向上流動的前景。在某種程度上,機會上的不平等如今可能被夸大了,至少在美國是如此。人們普遍認為,一旦某人能想辦法加入一個特定的網絡,比如就讀常春藤聯盟大學,就能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從而大大改善其社會和經濟發展前景。
這種說法無疑有點道理。市場確實存在著網絡架構,這種網絡不大可能出現在大多數模型中,但卻在幾乎每個領域內都很重要。其中一些架構(例如傳輸可靠信息的機制)是良性的,但其他一些(例如以往根據社會階層或財富來分配)則相當有問題。例如,最近大學招生丑聞所涉及的八所著名美國學府就表明,富裕的父母可以花錢將孩子送入教育精英團體。雖然頂尖大學學位確實是塊很好的敲門磚,但這遠遠不是獲取寶貴機會的唯一途徑,機會之路并沒有那么狹窄。
這并不是說向上流動性的下降不是一個問題。相反,已經有人對這一趨勢的成因開展了有益的研究,而這項研究也可以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參考。這恰恰是重點:事情從來不存在簡單的解決方案。一個數字——就業者的比例——不再足以衡量經濟的健康狀況,更別提勞動力的福祉了。我們需要一種更為細致的做法以應對就業可能對福利構成影響的多個方面。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9;編輯:許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