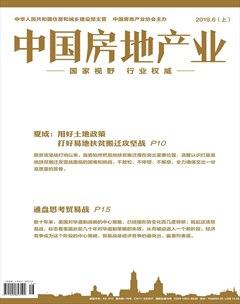保持貨幣政策定力 解決中美貿易矛盾
楊宇霆
中美貿易摩擦升溫,市場隨即預期貨幣政策寬松,期望央行把利率推低,離岸市場更不時流傳中國主動將人民幣大幅貶值,以抵御美國對華的貿易政策。
筆者認為,美國對華連年的貿易逆差是美元零成本,造成過度進口的必然結果;在市場極度波動、缺乏風險胃口的時候,中國更要保持貨幣政策的定力,穩定人民幣匯率的預期,提高外資對人民幣資產的信心,改變全球美元主導的格局,重根本上改變全球貿易失衡的狀態。
過去數周,中美貿易關系突然惡化,成為全球經濟的焦點。經過一年多的貿易談判,兩國官員互訪、溝通,并試圖發布聯合聲明以及初步的貿易協議,中美兩國還是在重大問題上未能達成共識。
事實上,兩國的角力一直停留在貿易和市場準入的層面上,邊講邊打。事實證明,關稅政策對解決貿易失衡毫無用處。按美國海關的口徑,2018的逆差達4192億美元,同比上升11.6%,是歷史新高。美國提高一部分中國貨品的進口關稅,對收窄對華的貿易逆差,毫無幫助。
其實,這場中美貿易戰不只是進出口層面的問題,更多的是兩國在全球貨幣系統中不平衡的表征,因此,單從貿易政策上處理問題并不能解決這個深層次的矛盾。雖然中美之間的爭端似乎出現轉機,但要真正改變兩國的經濟關系,更需要在貨幣系統上解決支持美國長期貿易赤字的根源問題,以及為各國央行(包括中國在內)外匯儲備管理上去美元化提供出路。
美國可以長期支持其貿易赤字,是因為其有能力長期借貸。例如,美國長期對中國出現貿易逆差,同時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卻不斷膨脹。從1981年開始,美國10年國債利率從16%的高位不斷下跌。美國人享受中國工人制造價廉物美的產品,卻沒有想到拖欠中國大量的貸款。對美國消費者來說,中國的店長,又是債主。這就是“特里芬悖論(Triffin Dilemma)”。
中國40年前的改革開放,一次性地為世界經濟提供大量的勞動資源。這種情況有點像在歐洲發現北海油田一樣,相關的國家在短時間內累積大量的財富,需要通過以主權基金的方式為資金尋找出路。美元是儲備貨幣,美元資產市場便成為這些國家資源的投資對象。中國也把外貿盈余轉為美元資產,持有的美國國債年年上升,最新的余額數字為1.12萬億美元。
為什么美元可以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學術圈的解釋是網絡外部效應(Network externalities)。各國越多使用美元,網絡效應越來越大,加大了美元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成本越來越低,已經流行的只會更加流行。既然很多國家已經使用美元作為支付貨幣,其他國家也就同樣使用美元支付貿易,并且購買美國金融機構發行的各種金融產品,以及美國政府發行的主權債務。美元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美國監管機構主導全球金融系統的規則,掌握對其他國家的金融制裁的決定權。
金融市場對美元的霸權地位的解析,以石油美元(Petrodollar)理論最為流行。1971年,當美國放棄金本位之后,美元大幅波動,1974年尼克松政府與沙特阿拉伯達成協議,限制沙特只能以美元作為石油出口的交易貨幣,以此換取美國提供軍事上的保護,沙特央行也從此選擇讓本幣與美元掛鉤這種匯率制度。按照這種解釋,美元不單只是一種石油貨幣,也是一種軍事貨幣(Armadollar),美國的貨幣制度應該是石油本位,這樣也可以解析為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是美國國債,因為美國必須負擔沉重的國防開支。
進口關稅在本質上是政府試圖提高進口成本,在美元零成本的基礎上添加的“偽溢價”,試圖抑制美國人過度消費。但進口關稅只能影響進出口貨品的相對價格,美聯儲還是可以無限量印鈔,但卻不能全面降低美國的購買力。一年級的經濟系本科生也曉得,關稅政策違反市場經濟原則,減少消費者剩余,造成無謂損失。更最重要的是,在操作上,關稅政策是選擇性的,針對中國并不公平,更影響兩國關系。
要真正解決當前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需要根本上改變的美國融資能力,這就涉及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地位的問題。美國需要知道,買東西是需要付款的,借款需要還款,還款是需要努力工作的,不能靠央媽買單,更不能靠槍桿。
人民幣國際化正是解決這個深層次矛盾的良方。更準確的是,世界各國必須改變以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習慣,正本清源,回歸基本面,以真實的資產作為貨幣基礎。既然美元當初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源于大家對于其購買力的信任,也就是其儲備功能,中國也可以更加積極推進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使更多央行、主權基金和金融機構減少持有美元資產。
如果美元失去了基礎貨幣的地位,應該出現長期貶值、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的情況。這種現象,是新興市場面對金融危機的典型表現。美元貶值,會減少美國的進口購買力卻同時增加其出口的競爭力,幫助美國實現進出口平衡。另外,長期利率上升,也會提高美國的總體儲蓄率,減少美國的過度消費,進而減少貿易逆差。同時,隨著中國人均收入的上升,進口消費品的數量必然增加。居民工資增加,也就意味著出口產品的成本上升,如果美元長期貶值,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出口競爭力也將下降。這樣的發展,就是對過去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態做出修復,從根本上解決中美兩國根深蒂固的矛盾。
問題是如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去美元化呢?經過前幾年的推動,人民幣已經成為全球匯率市場上相當活躍的一種投資貨幣。但是,在內地和香港的貿易以外,在國際貿易的層面,人民幣的滲透率仍然相當低。另外,雖然很多國家的央行已經開始持有少量的人民幣資產作為外匯儲備的一部份,而且已經跟中國人民銀行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但是,人民幣資產在全球的份額仍然相當低,美元仍然被市場視為無風險貨幣(risk free),如果要人民幣與美元看齊,這個目標仍然很遠。
中國應該在國際層面上加快推動世界各國發展新型外匯儲備系統,改變美元獨大這個不正常現象。當然,IMF的SDR是一種選擇,但擴大這個籃子更能體現真正國際貿易上的權重。事實上,中國目前利用CFETS一籃子作為人民幣匯率的基礎,這種做法極具參考價值。雖然國內外匯市場超過96%的交易仍然是人民幣兌美元(2018年5月,即期),加強其他貨幣在國內市場的流通,有利于發展一籃子貨幣的相關產品。
近年,國內期貨交易所已經推出一系列的人民幣計價期貨產品,為大宗商品人民幣化注入新動力。4月起將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券納入國際三大主要指數之一的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并將在20個月內分步完成。本月,中國A股將在已被納入的MSCI中國指數和MSCI新興市場指數中分別占到5.25%和1.76%的比重。這些發展具備相當的突破性,可以增加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地位以及流通性。過去一段時間,筆者觀察到境外市場對人民幣資產的胃口越來愈大。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貨幣政策應該要保持定力,維持匯率有序變化,不搞惡性貶值,進一步提高外資對人民幣的信心。“大水漫灌”不僅僅影響外資判斷人民幣匯率的長期價值,更提高國內的宏觀杠桿率,增加金融穩定的風險,是灰犀牛風險的源頭。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不等于固定匯率,而是讓市場更容易把握影響匯率的因素,以有效對沖其風險。如果中國的貨幣政策變得更加現代化,透明度更高,能做到“市場友好”(market friendly),方便投資者通過市場手段對沖匯率風險,這將會提高國際投資者持有中國資產的信心,進而提升人民幣相對美元的國際地位,根本地解決國際貿易不平衡的問題。
(本文作者系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澳新銀行集團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文章來源:財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