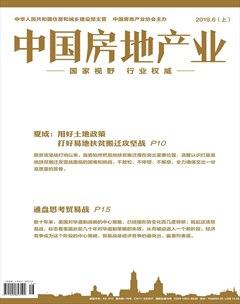大格局下看中美貿易糾紛
陶冬
該來的,總歸會來,躲是躲不掉的。美國宣布將25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品關稅由10%上調至25%,并準備對剩余3000余億美元中國產品課征懲罰性關稅。中國迅速對600億美國產品加征25%關稅,“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這個規模在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
世界兩大經濟強國爆發大規模貿易戰,時機上有其偶然性,做法上凸顯出特朗普強烈的個人色彩,但是此事有其必然性。貿易逆差,既是進口與出口之差,也是消費與儲蓄之差,還是使用與生產之差,三者恒等。只要美國人的消費習慣不改變,美國的貿易逆差是不可能真正縮小的,特朗普所為不過將對華貿易逆差轉化為對其他國家的逆差,根本無法讓美國更偉大。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中美貿易之爭,不過是二十一世界全球影響力之爭的序曲,其本質乃是國力之爭。改革開放四十年,美國一直以開放市場為誘因,試圖將計劃經濟的中國納入全球經濟的軌道,注入市場經濟的DNA,最終希望改變中國的價值體系。但是這個期望變成了失望,于是從奧巴馬第二任起,對華政策的基調由“接觸”轉向“遏制”。這是美國國策上的變化,特朗普不過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加上了濃重的個人色彩,但是“遏制”戰略并非始于特朗普,也不會因為某日特朗普離開白宮而結束。
十五世紀末至今,世界上總共發生了十六次世界老二挑戰老大,其中五次挑戰成功,四次沒有發生戰爭。美國在過去的一百年,擊敗了四位老二。如今中美之爭是世界老大與老二之爭。貿易戰已經大打出手,科技戰初露崢嶸,以后會不會有金融戰、食品戰?不得而知。未來二三十年,筆者看到的是不同形式的較力,時疾時徐,連綿不斷。
短期來看,筆者對六月底雙方達成階段性停戰,并不感到悲觀。這次談判的動態利益平衡并沒有改變,只是籌碼大了,嘴上強硬了。特朗普還是需要階段性成果來邀功,而且最好在美國選民進入夏季假期前發生,以期達到最好的宣傳效果。但是2020年美國選舉年,中國議題肯定是政客的箭靶子。克林頓時代之后的五次大選,初選勝出的共和與民主兩黨總統候選人均對中國持敵視態度。
今天筆者擔心的不是行事乖張的特朗普,而是在對華立場上美國顯現出的空前一致。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無論是左翼精英還是右翼精英,無論是白領還是藍領中間,處處感受到冷戰時候的氣氛。中國精英在計算貿易戰的經濟成本(如美國消費者蒙受怎樣的損失),美國精英用的卻是冷戰思維。這是筆者所看到的認知錯位。
毋庸諱言,中美打貿易戰,擁有巨額順差的中國一定吃虧。在美國在華企業、人民幣匯率上中國是可做文章的,但是投鼠忌器,輕易不會動用。投資信心,可能比出口更受影響。
但是從長遠看,過了這個坎的中國經濟一定以內需主導,十五年后中國國內市場的體量可能超過美國市場,中國應該可以發展出自主的科技體系。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上一次中國被嚴重依賴的大哥所拋棄,是六十年代初的中蘇關系破裂。特朗普也許是下一位赫魯曉夫。(本文作者系瑞信董事總經理、亞太區私人銀行高級顧問,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