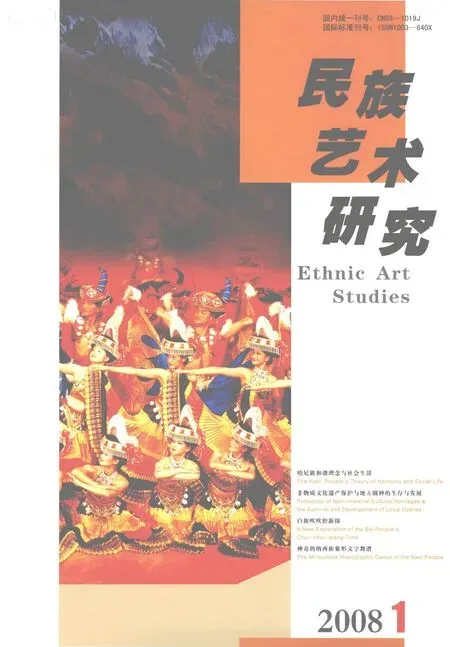有關中國電影通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丁亞平
近年來,中國電影史學的研究形成一股熱潮,出現了若干代表性的學者與成果。我從事電影史研究,也不揣淺陋先后出過一些著述。時光荏苒,我一個人寫的《中國電影通史》(兩卷本,120萬字,中國電影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聯合出版)面世已經兩年多了。此書的完成和出版雖不能說是無憾,但亦是盡心之作。電影史研究,想要“言之有物”,就要去除先驗性的幻象和框范;而進行中國電影通史的研究,面對新的問題,發現新的史料,探求新的答案,呈現于具體實踐,無疑有著相應的路徑、原則和方法論意識。對此進行梳理、反思和總結,是有意義的。
一、傳承、創新和通史路徑
學者之所以稱學者,實在傳承,在找尋學術路徑與發揮個人原力。1963年,中國電影學術界有了第一本《中國電影發展史》,其中的三位作者中的兩位,李少白和邢祖文先生,是我所供職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研究所的前輩老師,也是電影學界最重要的老一輩電影史學家。他們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的研究,作為一種學術風格、一種電影史學派和元素的顯著標簽,為他們,也為影視研究所贏得了無數聲譽。
《中國電影發展史》出版時,被命名為“初稿”。這部上、下兩冊的電影史著作,梳理、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國電影的發展歷史,凸顯了當時要求與特色。它距離寫作的對象比較近,又有官方支持、策劃與組織,所以在史料、觀點主流化、電影史模式、范式的開創性上都占了先機。《中國電影發展史》無疑是淵博的,材料豐富,具有范式建立和拓荒的性質。后來的電影史著作,包括港臺出的幾本,各有所長,各有所失,卻幾乎可以說都是從程季華主編的這本中國電影通史著作里派生出來的。這部電影通史的政治性與電影史結構及觀點選擇,顯然有它其時書寫的理由。這項具有開創性的電影歷史敘事既包含了政治對學術的介入,也包含將電影史視為有意義的方式加以建構的努力。共和國的電影歷史敘事模式,在與時代語境的映射中孕育開啟。 1981年,這部電影史著作未加修訂,繼續以“初稿”形式重印出版。這種出版方式并沒有導致書的傳播受到阻滯。相反,此著作在新時期的作用和影響非同尋常,聲名遠播。但是,毋庸諱言,左翼電影成為中國電影發展史述的主要素材,認定它在電影史上發揮了巨大作用,比其他電影的活動重要得多,具有狹隘性。以新的眼光考察歷史,需要超越。[注]重寫電影史,相對于在實際的電影史研究和寫作中提出的消解、解構和“顛覆”,還是提“重思”與“重述”更好,更有代際意義上的微妙的張力。李少白老師自己比較了不起的在于,他一直想解構《中國電影發展史》。比如,他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想寫一部《中國電影藝術史》。李少白聯手邢祖文申請了院級和國家級的項目,組了課題寫作的班子,積極規劃著之后的研究論域與方向。這個難度不消說是非常大的。因為,完全跳脫發展史的史學范式和治史觀念,去另辟蹊徑,確實是一項重任。但李少白有其高瞻遠矚解構的強烈愿望。也就是,他不想把電影史寫成電影政治史。這背后的潛臺詞,是他希望電影史不能簡單地為政治服務,希望尊重歷史,回歸學術研究。丁亞平,郝蕊:《創新的是電影史學發展的終極源泉》,《電影研究》第4輯,中國電影出版社,2018年版。
一種學術傳統和學術文化是寶貴的,再怎么強調也不為過。而在這種傳承中,也需要學人內心中能夠有我們時代歷史前進的方向,不斷地萌動出嶄新而又與眾不同的素質和構想來。每一個時代的電影史尋求改變,把過去和當前結合起來,站在當下回顧、重審以前的電影歷史,無論是文本、個案研究,還是做更全面的歷史考量,融入作者新的眼光、歷史分寸感和基本的立場是必需的。如果說電影史研究寓蘊范式、學派,那在不同的語境下一種范式或學派有什么樣的活力和創造力,有哪些代表性的成果,這應該是電影史研究者要考察、思考和自覺的。
傳承、創新和守護傳統,是學科發展的靈魂,是電影學術、電影史學觀念方法的核心內容,也是推動學術發展的呈現。在近十幾年來電影史學研究的熱潮中,門類史、微觀史得到拓展和深化,而通史研究,也被前所未有地激活。怎樣將新的電影史寫作作為一種進一步提高理論反思能力的寶貴實踐,是許多學者思考的中心問題。通史寫作,過去一直是電影史學研究中的弱項,在有的人眼中可能這無足輕重,沒有什么價值。如何改變這樣的認知與現狀,需要思想解放、觀念更新,也需要刮風下雨、雷打不動,以足夠的自我堅守與堅持進行漫長的研究和寫作。其中的關鍵是,我們頭腦里有無這種意識。對于電影史著述而言,更崇尚的是行動。中國電影通史,現在已出版的、已完成待出版的,和正在編寫中的,有好幾種。我想,在電影史研究和寫作中,保持“滴水穿石”的韌性和進行長期不懈的努力是一個重要的前提。而在具體工作中,則不必擔心在什么伸腳掛手上面做錯,電影史的意識、撰寫的標準是不是過嚴,更加大膽的電影史書寫體例及新意的捕捉,為多少已成為幾十年“固體”的電影通史這個難題開了一扇能吹進新風的窗子。
電影通史是什么?電影通史將時間向度作為自己的主要維度,試圖解釋電影長時段發展所發生的變革,但又并不限于此。“電影所能獲得的藝術效果部分依賴于電影的技術狀況。技術的發展在許多情況下是受經濟條件制約的。而經濟決定的影響則產生于社會語境之中。”[注][美]羅伯特·C ·艾倫,道格拉斯·戈梅里:《電影史:理論與實踐》,李迅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 年版,第5頁、第21頁。在關聯與制約中探索影響電影史發生與演變的生成機制及其因果鏈條,是其重要任務。李少白在談道中國電影史的研究方法時認為,電影史“兼有電影和歷史的雙重品格。作為電影學的歷史方面,它研究構成整個歷史現象中電影現象的變化過程。作為電影的歷史部分,它研究電影歷史現象的更替、變遷”[注]李少白:《中國電影歷史研究的原則和方法》,《文藝研究》1990年第4期。。不少研究者認為,研究電影歷史必須跳出以往研究影片歷史和作者歷史的范疇,將電影置于歷史之中作更為開放的研究,既融入更具主體性意義的“電影”探析,又同時可為社會發展史、意識形態史、文化史、經濟史、政治史等“起到注腳的作用”[注]酈蘇元:《關于中國電影史寫作走向的思考》,《當代電影》2005年第5期。。
無疑,電影通史是在豐富的影像和文獻之上進行的更全面的對電影的歷史考察和梳理,它是基于電影實踐的過去和現在之間不斷的對話。為獲得一個可以觀照不同電影史的公共視野,它使電影史有了更深入的發展和補充。電影史參考現代中外研究成果,從電影作品入手,通過分析比較的方法,密切聯系與作品和電影人相關的社會背景,敘述電影史上發生的以前的中國電影和電影人的世界及其連續性歷史,目的是從當時的政治、哲學、文學等思潮中尋繹電影藝術風格演變的歷史依據,理解并說明今天中國的電影傳統是如何從過去到當下被逐漸建構起來的。
由電影史學實踐出發,研究者的價值和意義被彰顯。過去以《中國電影通史》為題的較具規模的由個人撰寫的電影史著作一直沒有,2016年這本《中國電影通史》出版,它的研究和寫作無疑具有填補空白的開拓性性質。作為全新的通史著述,所做的研究是積累性的。從搜集資料,寫專題論文,追蹤一百多年來中國電影發展的脈絡,到最后成書,體現了這種特點。該書對1896年以來中國電影不同階段的發展進行屬于自己的梳理、分析和闡釋,其中有電影作品、電影人研究,也有電影歷史風貌、重大事件的回顧與闡述,同時又不缺乏對一個歷史時期電影生態、文化生態橫斷面的分析、把握與深入剖析。中國電影通史這樣的較大體量的著作,努力破解當下中國電影史研究的困局,它比其他專史要求涉獵的內容更廣、更豐富,史料更翔實,在某種意義上,作為全面了解中國電影的工具性的圖書,它于有的讀者而言,輕松就能做到一書在手,隨時備查。
電影通史與過去的電影史著作特別是不無童稚化的電影史講義與教程一類的書有著重要區別。與現實的電影經驗相比,電影通史以宏觀的視野、學術的品格和客觀踏實的精神回歸理性、科學、專業,不摻雜任何功利性,融入了有效的反思;電影通史因為距離的關系,“不受對象、權力和威勢影響,更多關注電影發生發展中的精神邏輯,顯示出其存在的意義”。[注]丁亞平:《中國電影通史》(第一卷),中國電影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頁。適應一時的口味,或者繼續沿襲主流電影史學,或者將冷飯一炒再炒,不符合史學研究者心中的理想和原則,這樣的電影史不值得我們為它浪費時間。
二、中國電影史“縱深線”的復雜性和通史寫作的限度性
我在一種可稱為“縱深線”時間的維度中融入思想與精神,采用新的理論和方法,對電影歷史“縱深線”的原型圖式、多維走向及其交叉重疊與潮汐起落進行探究、梳理和把握,并在自體反思和理論場域中出新。這跟電影史學發展中的跨學科趨向有關,也跟我們的重新思考的創新意識、史學思維和方法論有關。其史學意識和思維,體現了電影通史研究的自覺,較之以前的研究,它可能更為重視歷史主義的理論原則、觀念、研究范式、方法、模型和視角。研究和寫作中國電影通史,力圖重視電影研究“縱深線”的形成和歷史學的實證性,這之中也會面臨許多問題。
一個突出的問題是,作為中國電影通史的“縱深線”,其內容中較為容易產生質疑的可能是如何以及怎樣涉指臺灣電影和香港電影,兩者是構成中國電影史非常重要的部分,不知該作何考量。筆者的意見和處理是:《中國電影通史》這樣的書雖因篇幅所限,未能全面囊括大陸、香港和臺灣三地在內的中國電影,但是在梳理和研究中仍然要注意找尋、捕捉電影史上不同時期中國電影整體發展中的“縱深線”和共同建構的脈絡,在貫通大陸、香港和臺灣一百多年來電影發展歷史及其把握與闡釋上體現獨特的創新性。對于中國電影或中華電影來說,以前三足鼎立,現在是一個融合的市場。在此之前的三足鼎立的電影,筆者在寫作中貫之以大陸電影為主,港臺電影為輔的觀照與研究原則,即:以中國大陸電影梳理、論述為主,港臺部分適當涉及,一些“縱深線”上的部分重要的電影史事、人物被梳理和展現。在大的歷史節點和具體電影發展上,對涉及到的臺灣電影、香港電影進行重點的評析,如:早期電影互動和發展、20世紀40年代上海電影人南下香港、50年代在香港的朱石麟和費穆等人的電影創作及香港的巴金電影改編、香港電影文化流變等都要有論述,著意將中國電影史放在大的“縱深線”時空跨度上進行表述。至于近40年來中國電影的發展,需要盡可能詳細地梳理和總結大陸和港臺電影發展的歷史脈絡、歷史成就和歷史經驗。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的電影市場逐步打破封閉的態勢,內地和香港及國外合拍片成為制片業的重要選擇方向,且從以協拍為主,轉向以大陸為主(以我為主)的拍攝原則。開始,中國內地制片廠協助歐美等國拍攝了《太陽帝國》和《末代皇帝》等影片,此后更多的是與香港合作。自此,電影工作人員逐步走向高度交融。與張鑫炎合作《少林寺》、與李翰祥合作《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內地協拍)等,帶動了港臺與大陸合拍的熱潮。第五代導演的作品陸續走紅國際影壇,在各大國際電影節上斬獲獎項,出現“臺灣的資金,香港的技術,大陸的人才”相組合的新關系。1993年合拍片熱達到高峰,創紀錄拍攝56部。進入21世紀后,也即在形成中國電影的融合市場中的原三足鼎立電影,已經作為中國電影的整體,極大地推動了華語電影繁榮與興盛的走向,產生了廣泛的傳播力。由此,中國電影的“縱深線”越來越交融在一起。
不管是香港電影也好,臺灣電影也好,在中國這個范圍之內出現的電影,我們認為都是中國電影史上的電影;在這些“縱深線”范圍之內活動的電影人和他們的創作,我們都可歸為中國電影史上的電影家和電影現象。電影通史涉及臺灣電影和香港電影的內容,雖可能較簡明與綜合,但卻一定要注意從新的角度提出問題,討論其為何如此發生,而不像傳統的一些電影史或香港電影和臺灣電影專題史學著作那樣,探討單一維度的香港電影、臺灣電影發生什么和怎樣發生。
還有一個問題,是近40年來的中國電影史,所涉內容很多,加以主要指向當代中國電影的評價與判斷,材料龐雜,認識、視角各有不同,電影隨著當代歷史客觀環境的變動承載不同的定義和理解,然而倘若從“縱深線”舉重若輕地進行新的發掘、整理、解讀,并將其放在更宏觀的歷史語境里觀察,以使中國電影通史成為一部總體性的電影史,則自然難度下降,殊非易事之電影史,同樣可以予不可能以可能。
中國電影為40年來的改革開放做出了重要的注解。自從電影的生產制作、發行和放映各個環節連體形成產業經濟形態之后,中國電影在呈顯龐大的產業規模的同時,展現出爆發式增長和跨越式發展的景觀。2010年內地電影年度票房邁入100億元,2018年中國電影市場票房突破600億大關,以609.76億元完美收官,比上年559.11億元增長9.06%。
電影產業持續走在快速發展的軌道上。2012年內地電影市場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2018年一季度一度超過北美市場,成為全球第一大電影市場。銀幕總數已達到60079塊。截至2019年2月22日,中國內地電影市場該月已突破100億元,這是繼2018年2月后,內地總票房第二次突破百億大關,并把時間縮短到22天,比2018年提前了6天。在世界電影史上,單一市場月破百億元的票房的紀錄由中國創造。中國電影觀眾的觀影年齡層廣泛,電影市場體量不斷擴大,在增強中國電影的產業和文化影響力的同時,作為全球電影貿易大國之一的地位得以上升。中國電影市場的發展,依賴于國產電影創新的內生增長動力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升。中國如何邁向全球第一大電影市場?中國電影無疑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基點和轉折關頭,盡管對電影改革的實際運作與走向的看法有很大差異,但不管怎樣,許多重要的經驗值得總結,國產電影有著怎么樣的未來走向,電影創作如何在改革開放演進過程中被進一步喚醒、改變和塑造,成為值得關注的當代電影史的重要問題。[注]參見丁亞平:《中國電影:如何走向全球第一大電影市場?》,《藝術評論》2018年第10期。
通史研究無疑需要盡力集大成而致中和,在這方面做積極的宏觀認知、梳理和歸納,值得認真去考量。當代中國電影的發展, 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中國電影與社會經濟的融合緊密。電影作品的內涵及藝術風格映寓著特定的時代遭逢和美學選擇。
在中國電影史上,社會派、人文派、商業派、浪漫派構成電影史“縱深線”上的多樣性美感與話語形態。社會派直面現實,最受觀眾喜愛和富有參與性,和現實主義的真實美感形態結合,匡正時弊,給人愉快和省思,有益于社會發展,構成電影的主流。人文派重視藝術的風格化建構,影片在真實性、思想的深刻性和結構的完整性諸方面較其他形態的電影尤顯突出。商業派變異多端,歡快喧鬧。浪漫派則熱烈燦燦,是典型性的“逆出之類”。這樣的四種形態有時也會被打散和重組,而且對它們的概括可能有人不完全認同,但他們其實反映了中國電影,以至華語電影發展的基本狀況。社會派和商業派在顯在的層面掌握話語權和文化優勢;而人文派捕攝神韻而又婉曲、多義,成功地表現了“關心人”的主題,于隱在的層面顯示出極強的生命力和范式的意義;浪漫派顯現出某種希望的活力與主體性張力,但屬于少數派,這也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和90年代以來電影商業化興起、發展的結果。
中國的電影歷來和不同時期的政治以至國家意志的發展相勾連。“十七年”時期,20世紀80年代,一些電影,特別是秉持社會和人文選擇取向的影片上映后往往會遭到批評,而且批判相當兇猛,硬被安上“丑化黨的領導”“歪曲現實”等帽子,“上綱”很高,讓人膽寒。與之成為對照的是,香港電影導演的作品,大都是職業化的電影,是在片場和影院工作的結果,通常會回避談論意識形態和政治。作為好的導演,除了扎硬寨、打硬仗,不屑于走捷徑、抄近道,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回避跟老板和觀眾談政治和意識形態。香港以至臺灣影人的電影屬于商業派和人文派的居多,與這種職業生態相聯系。而商業與人文并非總處于互相支持的兼容關系之中,而是有時處于“縱深線”互相抵牾的悖論性的關系中。
人文或藝術電影大都受限觀賞性較差的基本條件,創作并不順利,影響力不大,這是人文電影最大的危機,而且這也是范式電影、藝術電影以至基本電影的危機,這比中國電影獨霸中國內地龐大的市場或者在國際電影節比賽丟幾個大獎都更為嚴重。可見電影的發展,與不同的時代與生態環境,和特定電影人及其各別作品的具體形態相聯系。復雜、多維的電影實踐、活躍態勢與多樣性趨向,包括審查制度以及中國影院電影的宣傳和商業的雙重屬性等,反襯出電影史學具有的限度性。
進行通史的寫作,在對中國電影做了“縱深線”發生史的周翔描述的同時,能否在結構上以及論述內容中加強對中國電影史發展中多維度的重要文本以及重要導演風格形成、特征以及啟承和影像的基本邏輯關系提供明確的分析線索?在通史研究和寫作過程中,人們究竟希望中國電影通史這樣的書,融入怎么樣的最新學術成果和打開怎么樣的全新研究視野呢?我想,前提當然是盡量顯現電影歷史和“縱深線”的復雜性、當代性,呈獻一種新的看待電影史的面貌。中國電影通史著作,記載、分析、研究中國電影發展進程中的階段性特點與客觀規律,重點反映電影“縱深線”的復雜交錯與承續的生態格局及歷史流變。電影因時代的不同,其面目、特點與影響也不同。我格外重視去思考的是:怎樣在追蹤、梳理百余年的中國電影歷史的過程中,找到我們研判中國電影問題所用的藝術的、文化的、學術的范式標準和框架?能否在電影史的總體性探索與“縱深線”描繪過程中超越狹隘的意識形態的話語和道德話語?如何寫出一部有自己特點的電影史,以豐富人們對中國電影的認識?這些是一個電影史研究者不能不去努力的目標和方向。筆者研究中國電影通史,將中國電影歷史發展視為與社會緊密聯系的存在,但相關電影史的綜合梳理,仍然是以代表性的電影人和影片為坐標,圍繞電影史“縱深線”上的電影人、影片,包括中國電影史發展中的重要文本以及重要導演風格形成、特征進行論述。
作為一部電影史著作而非專題理論研究,所處理和使用的術語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約定俗成的為大家共同接受與認同的概念,如“抗戰”電影、“文革”電影、主流電影、商業電影,但在做這樣處理的同時,電影史家關注的重點,應該是用新的分析法而不是舊的敘事法來撰寫歷史,采納什么樣的概念和認識能對電影史的研究工作有更細致、精準及脈絡化的理解。另一類術語和概念則可能更具有電影史的闡釋力,隱藏著一種當代史的視角。好的或比較好的理論視角、概括與術語,應該具有相當高的建構性。電影史是活的學術研究,不用死的框框框住它,把電影當成一個開放的系統來研究,研究視野更為開闊,方法和方向更為清晰,這是重要的。
三、第三重空間:走向歷史和邏輯的統一
電影史作者不是一個自在逍遙的歷時性旅行者,也不是簡單地去獨辟門徑,一味馳馬試劍。電影史的真實與敘事往往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經驗論視域下的電影史料及其運用在日趨開放的數字化語境下改變了它的意義。電影史的重寫與“修正”提供了不同的可能蘊含以偏概全的視野和角度。通史敘事的面相,存在于超乎其上的第三重空間中。電影通史的研究基于作者自己的客觀審視和主觀闡釋所得,將“發生了什么”“怎樣發生”的主體性建構與“為什么發生”結合,在走向歷史和邏輯的綜合中力圖對電影史及其生生不息的發展進程進行較為系統的掃描和深入的闡釋,在主客觀統一的范式中彰顯開放、完整的電影歷史研究方法的效能,以此進一步凸顯電影通史寫作的嚴整性和獨特性。
有關通史的研究,無論是偏重于社會學方法還是倚重風格分析,是編年史抑或國別史,有時都需要融入“跨界”的視角、新的話語體系,突破觀念的藩籬,以深入描繪電影歷史發展的豐富面貌。如海外學者米蓮姆·漢森的白話現代主義、湯姆·甘寧的吸引力電影等,和電影歷史現象和相關電影實踐并非總處于互相支持的兼容關系之中,但他們所采用的仍然是富有啟示的有趣方法,是域外史學開出的花朵。再如“大電影”的概念,是筆者和影視研究所部分學者進行理論研究的個人成果,它并不是官方概念(在這方面絕無有關“大電影”的“官方文件”)。在電影史研究中使用的“大電影”概念和結構分析,不是指“影院電影”“大銀幕電影”,而是指數字化轉型和網絡化新語境下電影形態、電影敘事、電影本體和電影業態及生態的改變,涉及影響日趨重要的技術、影像本體、傳播的多重維度。[注]此可詳見丁亞平《新語境下“大電影”的建構與發展》,《文藝研究》2012年第11期。參見丁亞平主編:《大電影制造:異彩紛呈的熱播影視》,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版;丁亞平主編:《大電影制造:熱門影視的光影世界》,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版;丁亞平等著:《大電影概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版;丁亞平主編:《大電影轉向:熱播影視的發展趨勢》(上、下),文化藝術出版社,2013年版;丁亞平主編:《大電影的拓展: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策略分析》,文化藝術出版社,2014年版;丁亞平主編:《大電影的互動: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策略可行性研究2》,文化藝術出版社,2015年版;丁亞平主編:《全球化與大電影: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策略可行性研究3》,文化藝術出版社,2016年版。這樣的新的術語、視角和場域,包括前面論及的“縱深線”等,如潮水般涌來,一起推著我們往既定的大道上走。不消說,其中當然蘊含對中國電影下一步的創新路徑和發展空間等的前瞻探討。
通史的寫作和探討,和那些先于我們存在的秩序相遇,可以打開觀照方式和視野,擴充心量,卻又不能不帶有“自我”氣質和自傳性質。
但是,通史寫作,史料筑基。一部電影史著作,重返歷史的現場,史料的發掘是基礎,盡力搜集資料,認識并把握其中呈現的確切性、可信性與問題,持比前人有更細密更確切的發掘力分辨力,是研究與寫作的前提。為使研究內容更為生動翔實和可靠,電影通史寫作和論述有時也可以盡可能比較充分、大量地引述電影人的訪談內容,通過多處使用一些重要的中國電影人的訪談或自述等口述史材料,使感性的東西融入理性分析和歷史的探索中。[注]以我的《中國電影通史》為例,電影人口述涉及和包括第四代的謝飛(下冊第83、94、122、160頁)、黃健中(下冊第95頁)、張暖忻(下冊第108、109頁)、楊延晉(下冊第96-97頁)、黃蜀芹(下冊第142頁)、鄭洞天(下冊第83、150頁),以及常彥(下冊第92頁)、馬德波(下冊第89頁);第五代的張藝謀(下冊第139?141、145、146、148、152頁)、陳凱歌(下冊第140、145頁)、田壯壯(下冊第151、152、153頁)、張軍釗(下冊第141頁)、霍建起(下冊第82頁)等。茲不贅述。
電影通史這樣的著作,努力去總結電影歷史經驗,揭示電影發展規律,但所體現出來的選擇與筆墨仍各有不同,對百余年中國電影的梳理取舍仍比較大。筆者對此是怎么考慮的呢?(一)電影史,即使是以“通史”名之,要包羅一切電影現象和作品,既無可能,也沒有必要。(二)還是需要承認中國電影歷史發展中存在著矛盾和復雜性,慎重選擇和處理有關論述對象是必要的。(三)一部內容豐富、生動的電影史(特別是電影通史),對其中出現的“執拗的低音”(日本學者丸山真男語)不能無視而不去做必要的敘述與呈顯。寫中國電影史,要能干凈獨立,貫穿秉筆直書的勇氣和傳統,以學者鮮明的治史立場進行分析。選擇讓電影史的本質更真實的方式去把握,而不是其他。
電影史寫作的個性化,其實也是不同的電影史作者個體/主體不同的選擇和做法的呈現。一部中國電影通史,面對多品種多樣式的電影,往往會聚焦考察和重點梳理影史上有代表性的電影作品,以劇情故事片為主,兼及紀錄電影、動畫電影。但是,電影史作者有其個性訴求,可以選擇追求自己理想的寫作方式與編輯體例。雖然,筆者認為一部電影史不可能把什么都悉數包羅,而且,能把復雜的電影發展歷史化為扼要且穩當的表述,也是格外考驗史識和學力的。
電影史對電影發生發展的歷史需要做全面的審視與掃描。徜徉其中,一方面作者希望在具備知識分子特質的導演身上看到對社會與現實有思考有擔當有深度的電影,并將之突顯地呈現出來,放到比較重要的影史位置上;另一方面,作者也希望中國電影通史這樣的著作能展現當代中國電影的“眾生相”,從全面的角度進行歷史的梳理與分析。如“文革”電影雖然相對于“十七年”時期電影(尤其是故事片)產量很少,但“文革”時期電影表現出高度的集體意識和快速走向極端的革命實踐的熱情,為電影藝術畫了一幅特殊而譫妄的“畫像”,不能視而不見。“文革”時期的中國電影,江青的作用,“樣板戲”的影響,以至那一時期拍攝沒有停止的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新聞簡報》[注]《中國電影通史》限于篇幅原因,對新聞紀錄片、科教片較少論及,但對重要的電影現象,有所論述。如“文革”后的1977年10月18日,文化部(當時電影主管機構)發出《關于停映有“四人幫”反黨集團成員形象的新聞紀錄片和他們指使拍攝的部分科教片、藝術片向國務院的請示報告》,要求相關新聞紀錄片一律停映(下冊第72-73頁)。至于“文革”時期,有關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新聞簡報》,本著作并非“完全沒有涉及”,在第六章第一節第三部分(該部分的標題為“同一種紅色的新聞紀錄電影和洋為中用的《紅色娘子軍》”),標題所標明的“紅色的新聞紀錄電影”即指《新聞簡報》,該段落(下冊第13頁)對《新聞簡報》進行了簡明敘述。此外,下冊“文革”時期的外國導演紀錄片,介紹了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但沒有涉及當時由周恩來總理邀請尤里斯·伊文思及其伴侶馬斯林·羅麗丹女士在中國耗時3年創作完成達12小時12部的系列紀錄電影《愚公移山》,這是重要遺漏。正如有學者所指出,這部紀錄電影是在世界電影史上都很重的一筆,在中國電影歷史中不該被遺漏。,作為當時最及時的“革命現場”,電影通史著作對此不能沒有涉及。再如中國獨立電影,這些影片在特定歷史階段和環境中因為不可能申請到“龍標”——即放映許可證,觀眾面受限,影響力不大,但因此就不該納入通史研究的范圍內了嗎?尤其是數字電影時代以來,中國獨立電影的創作是不可忽視的中國電影史的構成部分。又如關于“獻禮片”“英模片”和《建國大業》等主旋律電影作品的論列和分析,也出于同樣的考慮,這樣的影片,同樣具有明顯的歷史價值。
在中國,“獨立史官”的歷史傳統,對后來影響非常大。不從政治的角度書寫中國電影史,有其史學合理性。作為學術研究,我們不想把電影史寫成電影政治史,希望電影史不去簡單地為政治服務,希望尊重歷史。過去,政治對中國電影歷史書寫的影響和改變,是比較明顯的,這種做法讓人感覺好像電影史就是為某個人寫的,感覺中國電影只是因為出現了左翼電影,因為延安和解放區電影,才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這當然是一種有偏差的歷史認知,是需要解構的電影史。
各個時期中國電影發展都包括電影在這一時期獨立的工業、風格和主題關懷的系統發展的描述,而這些不同時期的特征常常是共存和重疊的,但這不能否定就其主要特點進行概括的意義。
對于一部電影史著作而非電影理論或批評論著說來,重返歷史現場是史論寫作必要的前提,電影史研究需要看到它特定歷史時期的特點,要準確把握,進行宏觀跟微觀結合的研究,這樣結論才可能比較扎實,是歷史主義的。所以盡力了解、搜集資料,努力思考、融合,以扎實材料支持這樣的歷史梳理與分析,做到筆者一直主張的“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注]首先,“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是完整的方法論,歷史主義本身就是方法論,是很重要的史論研究的觀察視角,建立論述的框架,所以這是不能割裂的。在電影史研究中,歷史和邏輯,從來都是既不可或缺、又彼此互動的。也正因為這樣, 這兩者之間其實也并非總是那么界線分明。其次,當你把議題或論述對象放到歷史語境中去,確實有如何稟有主動精神,怎么去論述并給出自己的判斷、評價、觀點的問題,這對你的研究的方向、深度、整體的格局和水平具有重要意義,所以還要有邏輯的建立、自己的闡釋。這里有梳理、接續、拓闊,也可以有扭轉、矯正與塑形。再次,對于一部新的電影史說來,這之中其實還有一個中介層,就是如何把它做一個必要的論述和表達,把你的觀點做一個專業化程度高、又區別于他人的史學和理論論述結合的新的個性表達。每個人的研究個性、風格、觀點跟思想依賴于這樣的表達、論述的個性角度形式,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方法論,其中必然會包含自己的知識、學科背景、歷史思維,等等。(丁亞平,郝蕊:《創新的是電影史學發展的終極源泉》,《電影研究》第4輯,中國電影出版社,2018年版。),是必要的。在我看來,這也是電影史寫作跟電影理論、電影批評的區別之一。我們做電影研究和史著寫作,考慮應盡可能地讓它重回歷史本來的形態中,努力梳理、把握它和特定歷史相應的社會、政治、文化、藝術的復雜關系,而在中國出版一部內容、篇幅較大的電影史著作[注]筆者《中國電影通史》的寫作,最初沒有列入自己個人的學術寫作計劃,而是來自中國電影出版社的約稿。,一方面不會簡單地尋求“發球得分”,另方面恐也難以太過形而上地要求,就像要求拔起自己的頭發讓自己的身體脫離地球一樣。中國電影通史這樣的書著寫作,有其學科建設價值與中國電影的文化傳播意義。在電影史的寫作中,史料或文獻需要集中而又具有覆蓋力,要顧及它的微觀、中觀、全貌、“縱深線”和歷史演進的脈絡,所以寫完、出版后即使發現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也是我們專誠不二、潛移影史的自然結果。
電影通史寫作堅持歷史的維度,形成開放的研究和體驗、激發問題意識,以至對于整個新電影史范式的反思和論述,都包含在我們與我們這個時代之間的情感的、精神的聯系和對社會現實問題的觀察之中。作為電影史學的新的建構,多少年后回過頭來看,近年興起的中國電影通史寫作,也許會是一個新的起點。電影史研究者的主張與其說是嘗試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不如說是追躡電影歷史發生與發展的軌跡。理智清明,心與天游,方法活潑,窮變化以洞徹事理,創新性地去進行歷史敘事、呈現其具有的特色、時代意義,更為重要。潛入歷史和學術的汪洋,“板凳坐得十年冷”,更能幫助我們以更開闊的胸襟走好自己的路,進而更清楚自身與他人的特色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