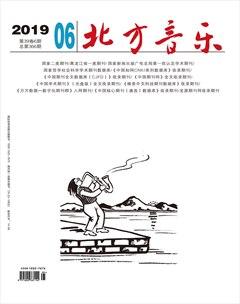山西踢鼓子秧歌的源與流
楊易杰 郭笑晗
【摘要】踢鼓子秧歌是山西民間舞蹈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源于農耕文化,給三晉文明增添了一抹亮色。本文通過追溯踢鼓子秧歌的歷史淵源及變遷過程探尋踢鼓子秧歌的“源”,進而提出現階段踢鼓子秧歌發展之“流向”,以期實現踢鼓子秧歌的新發展,為山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建設貢獻已力
【關鍵詞】山西:踢鼓子秧歌;民間舞蹈
【中圖分類號】J712 【文獻標識碼】A
一、踢鼓子秧歌的歷史淵源
踢鼓子秧歌,是山西民間舞蹈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三晉大地上一個獨特的藝術種類。它發源于山西晉北地區,流行于山西的大同、朔州等地,是山西晉北地區的文化代表,近年來已被評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
踢鼓子秧歌產生于晉冀蒙三省的交界地,由于地處雁門關,緊鄰內蒙古自治區,導致這片地區長期以來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響,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特色。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踢鼓子秧歌兼具粗獷豪放且柔美細膩的風格特征。
踢鼓子秧歌流傳廣泛,歷史形態久遠,據記載,在宋朝舞隊中,就已經形成了秧歌的雛形,但至今還沒有考察到踢鼓子秧歌具體產生于什么時期。在民間采風中從一些老藝人的口述中我們了解到,踢鼓子秧歌早在清朝之前就已經出現了,明末清初開始發展,盛行于解放之后的文藝大發展時期。發展至今,它已是人民喜聞樂見的一種藝術形態。
踢鼓子秧歌的起源主要為一些民間傳說,大多與水滸好漢有關,其中有兩個說法較為普遍。說法一梁山英雄董平在回鄉探望母親時,在內蒙境內被契丹人抓了起來,由于董平也主張反宋,于是就把他放了。他在回家途中,正逢朔州正月十五鬧紅火活動,董平也是性情中人,一時興起便和當地人民編演了一段踢鼓子秧歌。他將他所熟悉的梁山好漢的故事運用到了節目內容中,這些節目深入民心,受到了老百姓的喜愛,便流傳了下去。另有一種說法是宋江在招安之后,沒有得到大部隊的支持,于是轉移根據地到長城內外,對外宣稱為練秧歌,實則是積蓄力量,準備東山再起。這些民間傳說雖說已經得不到具體驗證,但卻為踢鼓子秧歌的舞蹈形式增添了民間色彩,人們崇尚水滸英雄好漢,把這種精神融入民間娛樂形式中,促進了踢鼓子秧歌的流傳發展。
二、踢鼓子秧歌的變遷
由于時代久遠,流傳時間較長,受到的影響較為廣泛,山西踢鼓子秧歌原本的藝術相貌發生了一定的衍變。據了解,最早的踢鼓子秧歌,是在手腕處掛一小鼓,舞動時用腳踢鼓而舞,故稱“踢鼓子秧歌”。經過時代的變遷,踢鼓子秧歌受多種原因影響融入了眾多其他元素,促成了其形態變異,從當今踢鼓子秧歌的表演中我們可以看出它與武術和戲曲的交融最為明顯。
首先在動作方面,傳統踢鼓子秧歌形成于農耕文化的黃土地上,它的動作與勞作息息相關,拔泥步就是其顯著的代表。在發展至清朝之后,受戰亂影響,男角的動作中融入了大洪拳、小洪拳、二踢腳等武術套路。在道具方面,最初的男角“鼓子”的道具有手鼓、腰鼓等。隨著時代發展,明清時期戲曲盛行,踢鼓子秧歌受戲曲影響,在道具上逐漸去掉了之前的手鼓,加入了戲曲中的髯口,鼓子便衍生出了以髯口為主的流派。“拉花”的道具為小镲、手鑼,在歷史發展中,還出現了以扇子和手絹為主的流派,稱作扇舞花。在風格特征方面,由于踢鼓子秧歌產生于蒙漢交接地,容易引發戰爭,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長期交融,導致其風格在流傳中形成了“鼓子”剛勁有力和“拉花”柔美輕盈的對比。在其服飾中,當今踢鼓子秧歌的丑衣、大衫、彩鞋等,也與戲曲服飾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
究其原因,除自然因素以外,人文因素對它的影響更為重要。山西踢鼓子秧歌是民間的舞蹈,民間舞蹈是人民的藝術,它產生于人民,它的發展自然受人民生活習慣,生活喜好所影響。戰爭時代戰爭多,人民為防身練習武術,于是在舞蹈行類中融入了武術。明清時期戲曲繁盛,踢鼓子秧歌潛移默化受戲曲影響,娛樂中藝人們為迎合大眾,便在踢鼓子秧歌中融入了戲曲。
這些改變是它在歷史舞臺上的自然發展,隨著時代的進步,它的動作、音樂、角色、道具以及服飾方面都有所豐富,這也是踢鼓子秧歌流傳至今深受人民喜愛的一大原因。作為民間舞蹈,我們應該尊重它的自然變異。但這些變遷的結果,也會擾亂我們的眼球,在如今的衍生態發展中,使我們忽視了踢鼓子秧歌的根,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代踢鼓子秧歌傳承的完整性。所以要想發掘出完整的踢鼓子秧歌,我們不能只關注現有的種類繁多的踢鼓子秧歌表演,要更加深入民間,多方面采集動作元素,并尋根溯源。
三、被我們忽視掉的源
在多次去往山西懷仁、朔州等地的采風過程中,我們了解到,在民間,當今踢鼓子秧歌的流派眾多,但它的源已經快要消失。據目前已知的情況看只有懷仁市東寺莊村還留存有較為原始的以手鼓為道具的踢鼓子秧歌,大部分踢鼓子秧歌的繁衍地都已經不再留有手鼓,而我們在這一點上缺乏更深入的探究,這就造成 人們對于名為踢鼓子秧歌在表演時卻沒有鼓的疑問。這個疑問是民間踢鼓子秧歌受多種因素影響變遷的自然結果,我們不需要去追究這個結果的好與壞,但如何保護它,發展它,卻是需要我們去重新思考的。
從舞蹈身體的元語言來說,踢鼓子秧歌男性角色“最初的語言”應該是拿著手鼓,用手鼓踢、磕、擊形成動作的舞蹈,這種形態可以說是踢鼓子秧歌的原生形態,也就是踢鼓子秧歌的根。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探究清楚踢鼓子秧歌到底是什么,它后來的變異是從哪里開始,它今后的發展方向應該往哪里去。刨清楚它的根,它的枝葉發展才能昌盛。所以對于踢鼓子秧歌的元語言我們是應該選擇重視,再去探尋的。如此,才能保證踢鼓子秧歌的完整性與準確性。
四、當今在發展踢鼓子秧歌時我們應該如何追源溯流
如今,民間一些文化館以及老藝人已經開始從事整理山西踢鼓子秧歌的工作,對于傳統文化的保護,大家已經開始行動。但從目前了解的情況來看,對于如何保護踢鼓子秧歌的思路還需繼續理清。手鼓作為踢鼓子秧歌的符號,應該在踢鼓子秧歌的發展中留有痕跡,我們應該抱著回真向俗的態度去追尋。民間對于踢鼓子秧歌原生形態這一片的空白,需要我們的提醒以及幫助,從更加真實的民間,從生活形態入手,將踢鼓子秧歌的根發掘出來。
當今的踢鼓子秧歌不僅僅流傳在原生形態,衍生態的踢鼓子秧歌在山西各大高校也越來越被重視。在衍生態踢鼓子秧歌發展的如火如荼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就如原生形態的踢鼓子秧歌一樣,它的發展也缺少了對根的重視。從原生切換到衍生形態中,依然是變遷后的形態保護的較為完善,卻缺失了踢鼓子秧歌的元語言。如果我們能夠將本源手鼓的意義探究透徹,將手鼓作為符號再探究它其他形態的演變,判斷經過變異的踢鼓子秧歌哪些更靠近它的元語言,是否會更加容易將流派眾多、形態眾多的踢鼓子秧歌區分清楚,從而能夠篩選更加有意義的元素保留加以提煉,放入踢鼓子秧歌的規訓形態中,實現它的發展。
踢鼓子秧歌作為山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在探索其價值的路途中必定會遇到種種問題與疑惑,我們一定要本著追根溯源的態度去反復探索與考究。確認其文化符號將有助于我們對踢鼓子秧歌動作、道具、服飾等種種因素的辨認,也有利于我們將踢鼓子秧歌向課堂化、舞臺化的方向發展。在其豐富的流派中找到一條主路,理清踢鼓子秧歌的源與流,也將是我們這一代人探究踢鼓子秧歌的必經之路。
作者簡介:楊易杰(1994—),男,山西晉城,碩士研究生;郭笑晗(1993—),女,山西太原中央民族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