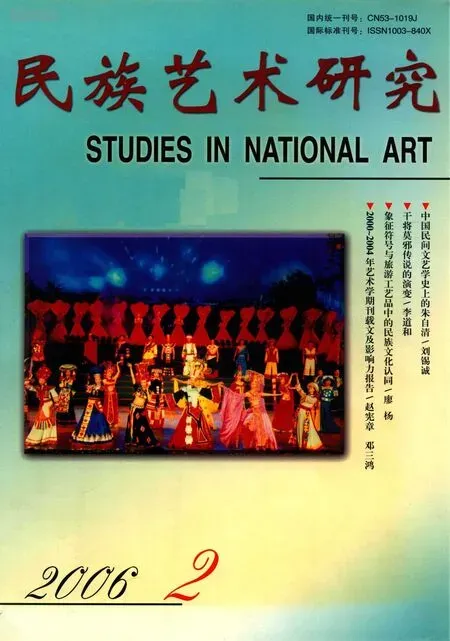時代精神與文藝高峰——哲學對藝術經典的三種建構
李 洋
王一川教授在對藝術高峰的專題研究中,把那些與藝術高峰的形成有關系的各種人,依照他們的職業、身份和發揮的不同作用,簡潔地概括為五要素:立峰者(藝術家)、造峰者(思想家等)、測峰者(藝術研究者)、觀峰者(讀者與觀眾)和護峰者(藝術管理者等)。在這五要素中,“造峰者”指哲學家、美學家和思想家,他們不是直接研究藝術的研究者和批評家,他們與藝術創作沒有那么密切的互動關系,他們也不是一般的觀眾,工作也與藝術管理沒有關系。但在藝術高峰的形成中,這些思想家發揮著無法替代的作用。本文認為,我們可以通過哲學與藝術經典之間的關系,去理解“造峰者”與藝術高峰之間的關系。那么,從哪個角度才能更準確地分析哲學對藝術經典的影響呢?我們不得不提到黑格爾“時代精神”(Zeitgeist)的概念。
一、藝術高峰與“時代精神”
黑格爾認為,哲學與文學藝術的經典作品都源于醞釀和生產這些思想、這些作品的“時代精神”。所謂“時代精神”,就是“貫穿著所有文化部門的特定的本質或性格”[注][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61頁。,哲學、藝術和科學都是“時代精神”的表達。但是黑格爾強調,哲學在時代精神中格外特殊,“哲學是對時代精神的實質的思維,并將此實質作為它的對象”[注][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67頁。。在時代精神中,哲學的形式與藝術、科學上的成就是共存共生的,但哲學不僅是“時代精神”的實質內容,也在外部把“時代精神”作為它思考的對象。因此,哲學通過“時代精神”與藝術經典發生關系,同時,哲學也與藝術經典共同構成了“時代精神”的表達。
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把思想與藝術的關系闡釋為意識與文化的關系,他提出,“文化饋贈給意識的顯然是一種與遺忘力相對的新型能力:記憶。然而,我們在此關注的記憶不是痕跡的記憶。這一嶄新的記憶不再是關于過去,而是有著面向未來的功能;不是感知性的記憶,而是意志的記憶;不是痕跡的記憶,而是言語的記憶。”[注][法]吉爾·德勒茲:《尼采與哲學》,周穎、劉玉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頁。我們可以化用德勒茲這個精妙的分析,把哲學與藝術經典的關系歸納為三種形式。其一,哲學的時代精神體現為“意志”,對藝術家和藝術經典發出召喚,推動經典作品的形成。其二,哲學的時代精神體現為“語言”,即哲學本身可以進入了藝術的語言本體,讓思想與藝術共生,把哲學沉思轉化為藝術作品的形式或風格。其三,哲學的時代精神體現在來自“未來的功能”,即哲學基于精神和思想的訴求,不斷返回歷史、重塑記憶,去發現、確認經典作品的精神價值。我們結合具體事例對這三種關系展開分析。
二、時代意志召喚經典
首先,哲學對藝術經典發出召喚,歷史上的藝術經典總是對特定時代精神的某種回應,藝術杰作之所以會成為“高峰”,是因為它們在思想的召喚中應運而生,應聲而出。哲學家的思想成果為藝術經典的出現提供了“時代意志”。德勒茲在此處所說的“意志”(volonté),一方面包含了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所說的藝術史心理學意義上的“藝術意志”(Kunstwollen),即那些決定了藝術風格發展的“最初契機”與“形式意志”(Formwillen)[注]這是沃林格對“藝術意志”的基本定義,他認為藝術意志決定了所有藝術作品的內在本質,林林總總的藝術形式是藝術意志這種先驗存在的客觀化表現。參見沃林格:《抽象與移情》,王才勇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7頁。;另一方面,還包含了對“時代精神”的整體認知,即海德格爾所說的“作為求意志的意志”[注][德]海德格爾:《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頁。。哲學家把對世界的敏銳觀察,凝匯在時代的問題中,哲學對知識狀況的概括和對社會變遷的預見,為藝術創作開辟了新的領地,為即將發生的藝術創作指出了最有價值的方向,醞釀和召喚藝術杰作的出現。
在這個意義上,哲學就像“先知”,哲人們的思想啟迪著藝術,讓藝術家清晰感到時代變動的感召,靈敏地發現時代的問題,再通過他無與倫比的想象和才華去創作出經典作品。哲學表達的時代意志,對于藝術來說具有超個體性。丹納(Hippolyte A. Taine)相信時代精神高于藝術家的個人才華。他做了個比喻,藝術家的個人才華就像種子,而時代精神就像自然氣候,藝術家能否創作出經典的作品,依靠時代精神的哺育,他把時代精神對藝術的影響稱為“選擇”。“精神氣候仿佛在各種才干中作著‘選擇’,只允許某幾類才干發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別的。由于這個作用,你們才看到某些時代某些國家的藝術宗派,忽而發展理想的精神,忽而發展寫實的精神,有時以素描為主,有時以色彩為主。時代的趨向始終占著統治地位。”[注][法]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選自《傅雷譯丹納名作集》,傅敏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頁。通過這種“環境的選擇”(choix du milieu),根據固有的標準讓那些與時代精神相一致的作品成為經典,而遺忘或淘汰其他類型的作品。
在歐洲啟蒙主義時期思想與藝術的關系中,就非常突出地體現了哲學與藝術經典之間這種關系。盡管啟蒙運動最早發生在17世紀的英國,但卻在法國發展成最有影響的思潮。伏爾泰、狄德羅、讓·達朗貝爾(Jean d’Alembert)等啟蒙思想家們開始對君權神授和“存在巨鏈”等專制思想提出了挑戰,他們推崇理性,質疑上帝的存在,批判腐朽的宮廷文化。啟蒙主義堅信人的力量,人的獨立理性才是人類道德與知識的基礎,他們相信理智的思考可以解釋世上的所有現象。
這個時期的繪畫正是蒙受了啟蒙主義思想的感召。巴黎上流社會流行的沙龍經常邀請伏爾泰等思想家參加,這些思想家在藝術沙龍上的言行徹底改變了巴黎沙龍藝術的風格,開啟了新古典主義風格。當時最著名的藝術沙龍主人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就資助了伏爾泰等人撰寫了啟蒙主義思想代表作《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百科全書》這套啟蒙主義精神的代表作就是哲學家與藝術家合作的結果,伏爾泰等啟蒙主義思想家撰寫了內容,而畫家們繪制了插圖。啟蒙主義崇尚理性,推崇理性秩序和對科學的精確性、系統性的追求,這些觀念都影響了18世紀中葉開始形成的新古典主義。因此,新古典主義就是啟蒙運動的產物,這些藝術看上去是從希臘借鑒了單純而典雅的形式,其實在精神上是受到了啟蒙主義思想的感召。
狄德羅不僅是當時最活躍的思想家,也是劇作家,他對繪畫也格外關注。作為啟蒙思想家,他對當時法國沙龍繪畫不屑一顧,經常撰文批評沙龍繪畫上流行的洛可可風格。比如他對后來成為巴黎沙龍學院院長的弗朗索瓦·布歇(Fran?ois Boucher)嗤之以鼻,但對關注市民生活的夏爾丹(Jean-Baptiste Chardin)、格勒茲(Jean-Baptiste Greuze)卻格外推崇,認為這些繪畫進行了對人性最為逼真的刻畫。所以,法國18世紀的古典主義繪畫與啟蒙主義之間有著某種呼應關系,藝術家在繪畫的風格、使命和美學追求上,與伏爾泰、狄德羅的社會理想和美學趣味不謀而合,成為時代精神的表達。荷蘭藝術史學者曲培醇認為,“格勒茲的計劃做的和狄德羅自己創作的一種新戲劇的嘗試可以相提并論。這種市民劇側重描繪當代中產階級的生活和面臨的問題。格勒茲實現了狄德羅的主張:一種處理當代現實、展現真實情感、樹立美德典范的藝術。”[注][荷]曲培醇(Petra ten-Doesschate Chu):《十九世紀歐洲藝術史》,丁寧、吳瑤、劉鵬、梁舒涵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頁。
然而,狄德羅作為思想家,對應運而生的古典主義風格也有質疑,他發現古典主義繪畫過度依賴理性而脫離生活,學生們過于重視訓練素描的技巧,忽視了對巴黎市井真實生活中具體人物的觀察。狄德羅在《論繪畫》中明確提出,對社會和現實的關注不等于排斥人的情感表達,而生動的歷史畫甚至要好過那些靜物畫,這無疑是對古典主義的反思,進一步召喚藝術家們創作出超越嬌柔的形式主義和寫實理性,通過強烈的個人情感去反映社會現實。正是這樣的主張奠定了隨后發生在法國的浪漫主義繪畫的基礎,尤其是兩部代表作籍理柯(Théodore Géricault)《梅杜薩之筏》(Le Radeau de la Méduse, 1818)和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自由引導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 1930)。經過了啟蒙主義和大革命的洗禮,浪漫主義畫家不再過分強調笛卡爾所謂“我思故我在”的理性,轉向直接表達人的情感所能釋放的能量,“在浪漫主義對理性的反叛中,藝術家頌揚情感,視情感高于理性,激情要擺脫約束,自由沖破規范,個人超越集體,神秘事物是理性無法解釋的,而主觀感悟比客觀更能認識事物的本質。”[注][美]威廉·弗萊明、瑪麗·馬里安:《藝術與觀念》,宋協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27頁。因此,狄德羅先后兩次對藝術創作產生了影響,這完全依賴于對時代精神的體悟和表達。
同樣,在德國狂飆突進運動中,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對歌德也扮演了影響者的角色。赫爾德“是德國啟蒙時代美學的具有革命性的人物,對于新古典主義來說,他們才是真正的掘墓人。”[注]汝信主編:《西方美學史》,第二卷,彭立勛、邱紫華、吳予敏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19頁。赫爾德在青年時代非常博學,不到20歲就在教會學校擔任教職,教授自然、數學、歷史、法語和德語修辭學等課程,非常受學生歡迎,是當地知名的“理想主義教育家”[注][德]卡岑巴赫:《赫爾德傳》,任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17頁。。赫爾德對當時流行的理性主義美學不滿,撰寫了《批評之林》與萊辛和克勞茨展開辯論。1764年,他辭去神職,開始啟蒙主義運動的法國之旅,結交了狄德羅、達朗貝爾等思想家,并全面接受了啟蒙思想。1770年,他在斯特拉斯堡結識了只有21歲的大學生歌德,赫爾德與歌德的相遇被譽為是狂飆突進中最重要的事件,“對德國文學史和思想史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注][德]卡岑巴赫:《赫爾德傳》,任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41頁。其時,赫爾德盡管只有26歲,但他的世界觀和美學觀已經形成,思想更加堅定和成熟,赫爾德已經建立了自己的體系,也非常自信。他對歌德毫無保留,無所不談,把他對啟蒙主義的見解以及對法國藝術的失望都講給了歌德聽。歌德認為,“對我產生了極其重要結果的最重要的事件是和赫爾德的認識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密切關系。”[注][德]卡岑巴赫:《赫爾德傳》,任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41頁。盡管后來歌德與赫爾德不和而分道揚鑣,但在歌德成長過程中,赫爾德的思想、學識和對藝術的判斷,深深影響了他對文學和藝術的理解,進而使他完成了他最早的代表作《少年維特之煩惱》(1774),這也是德國狂飆突進的重要作品。
在歷史上,狄德羅、赫爾德這樣的思想家不在少數,他們的哲學思想準確把握住時代精神的變化,重塑了時代的內在觀念和美學趣味,啟迪著藝術家,與隨后出現的藝術經典之間有著召喚與呼應的關系。
三、時代精神轉化為藝術語言
歷史上的許多經典作品都會以某種方式彰顯時代精神,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把經典作品對藝術家的影響稱為“影響的焦慮”。他不像丹納那樣過分強調時代精神是哺育杰作的精神條件,他認為“個體的自我是理解審美價值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標準”[注][美] 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頁。,我們強調時代精神,但不能忽視藝術家作為個體的獨特性和創造力,不能否認藝術作品存在于自在的文本世界之中。“一部杰作是一個人心靈表達的精華。世上不存在非個人化的杰作。”[注][法]夏爾·丹齊格:《什么是杰作》,揭小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頁。然而,時代精神不僅能從外部對經典的出現推波助瀾,在藝術文本內部,哲學也可以產生影響。哲學家與藝術家在相同的“時代精神”中共同思考(我們可以想到“philosophy”這個詞的原意就是“友誼”),他們的思想和文本完全可能彼此糾纏,相互生成,共同創作。杰出的哲學離不開完美而精確的語言,而藝術作品也可以表達哲學般嚴謹的推理和對生活的沉思。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與比利時畫家勒內·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就表達了哲學與藝術經典之間的第二種關系。米歇爾·福柯在1966年出版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中,集中思考了與古典知識型密切相關的再現問題,而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勒內·馬格利特對這個話題也非常感興趣。當福柯與馬格利特思考相同的主題時,哲學就成為他繪畫的語言。馬格利特本人對哲學很感興趣,他對黑格爾、海德格爾以及薩特思想都特別了解,而且他希望別人把他稱為“哲學家”,只不過他是借助于繪畫去思考哲學。1966年,馬格利特被福柯在《詞與物》中的思想深深地吸引,尤其在第一章還細致地分析了委拉斯凱茲的《宮娥》。馬格利特始終關注圖與文的關系,所以,在讀過《詞與物》之后,專門給福柯寫了兩封信,表達他對這本書的閱讀感受。馬格利特在1926年創作“煙斗系列”的第一個作品,名字就叫《影像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images, 1929),但這個系列的作品在后來就很少再繼續創作。但是,時隔40年之后,當馬格利特讀過福柯的《詞與物》后,又重新創作了“煙斗系列”的新作《雙重神秘》(Les Deux Mystères, 1966),這幅畫直接針對他自己在1929年創作的《影像的背叛》,他把《影像的背叛》重新畫了一遍,但是把這幅畫放在一個畫架上,在畫架外的空間左上角,他又畫了一個漂浮著的巨大煙斗。這幅畫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它直接來自于福柯哲學思想的啟發。
1968年,馬格利特逝世。福柯為了紀念這位畫家,出版了《這不是一只煙斗》,他專門用兩篇文章分析馬格利特的這幾幅畫,同時也公開了馬格利特給他的兩封信。福柯在這本書中對《影像的背叛》展開了分析,這兩篇文章雖然是對馬格利特的紀念,福柯同時也在延續他與馬格利特在共同問題上的繼續對話,即對相似—再現體制的批判。
在傳統繪畫中,我們習慣性地認為,畫中的事物就是實在事物的表象,而畫上的文字或者標題,指向這幅畫的意義。因此,圖與詞的關系就是一種再現和確認的關系。在福柯看來,這種關系來自于主宰了15世紀到20世紀的西方繪畫的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就是確認造型再現與語言說明的分離(它強調相似性),人們通過相似性來觀看,通過差異性來言說,結果兩個體系既不能交叉也不能融合。”[注][法]米歇爾·福柯:《這不是一只煙斗》,邢克超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頁。在畫中,要么是圖支配詞,要么就是詞支配著圖,二者處在一種不平等的、有主次分別的秩序空間。第二個原則就是通過“確認”,建立相似與再現的關系。只要一個圖與某物相似,人們就會習慣性地依照相似原則去尋找詞語進行確認,圖與物是相似的,我們通過詞完成這種確認。人們總是把圖中的相似形象確認為物本身。在福柯看來,這正是圍繞著相似和再現建立起來的古典知識型最形象的表達。而馬格利特的繪畫恰恰也把詞與物、相似與確認的問題放置在一個矛盾的情境中,把福柯的思想變成了他繪畫的語言本身。這真是一場哲學與繪畫的精彩對話,哲學對藝術的作用并不是一種召喚,而是與繪畫共同思考。而馬格利特的繪畫并不想表現什么,它的語言與內容就是哲學本身。
思想家與藝術家的對話或許不一定像福柯與馬格利特那樣契合,尼采與瓦格納就經歷了從親密的知己到美學上的仇敵的變化。這個思想史上著名的“瓦格納事件”提供了理解哲學與藝術經典的另一種共生關系:哲學與藝術在強烈的張力中發展。哲學史和美學史已有太多關于這段往事的討論,我們想強調的是,尼采與瓦格納之所以成為摯友,因為他們都在叔本華的思想中獲得了靈感。尼采在瓦格納的音樂中感到了強烈的共鳴,這促使他寫成了《悲劇的誕生》,而瓦格納則創作了《尼伯龍根的指環》中的《齊格弗里德》(Siegfried)。然而,他們圍繞德意志精神的復興而燃起的友誼之火,因他們對音樂的不同理解而熄滅,尼采公開寫書批判瓦格納音樂沉溺于蠱惑大眾,瓦格納的音樂“意味著同一件事:在文明的沒落中,在大眾具有決定權的所有地方,本真變得多余,不利,受冷落。”[注][德]尼采:《瓦格納事件/尼采反對瓦格納》,衛茂平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頁。從精神上的知己到世俗中的敵人,瓦格納的音樂都成為尼采哲學中最為生動的內容,而瓦格納也在與尼采的決裂中創作了他晚期的杰作。
四、時代理性點燃歷史記憶
哲學還能以回溯的方式,參與藝術作品的經典化和再經典化。哲學家對藝術作品的分析與專業的藝術史學家的區別在于:哲學的歷史追溯伴隨著更加堅定而充分的理性判斷,以及更為深邃的超越性的思想價值。哲學用思想的光芒重新照亮歷史,讓那些靜置在角落中的杰作重新煥發生命的光芒,在這個方面最為典型的就是海德格爾對荷爾德林的發現。
當海德格爾思考現代性的問題時,用“上帝的消失”描繪所謂的“世界黑暗的時代”,他認為在那個技術發達的時代里,精神反而是赤貧的,這個時代甚至“無法察覺上帝的缺席”“甚至連自身的貧困也體會不到。這種無能為力便是時代最徹底的貧困。”[注][德]海德格爾:《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頁。但是,這種悲觀與哀嘆讓海德格爾的沉思照亮了一百多年前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當然還有里爾克),他在他的詩中找到了精神歸宿。“在貧困時代里作為詩人意味著:吟唱著去摸索遠逝諸神之蹤跡,因此詩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時代里道說神圣。因此,用荷爾德林的話來說,世界黑夜就是神圣之夜。”[注][德]海德格爾:《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頁。海德格爾在詩中刺探到語言與存在的關系,認為語言才是存在永恒的棲居之所,詩人證明了“只要語言在,他們就存在”,海德格爾在詩人身上發現了哲學無法找到的勇氣與希望。荷爾德林的詩歌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基于存在,它既沒有“沉淪”,也不是“沒落”,它就在存在之中。正是在這個視角下,海德格爾重新定義荷爾德林的非凡價值:
荷爾德林是貧困時代的詩人的先行者。因此之故,這個時代的任何詩人都超不過荷爾德林。但先行者并沒有消失于未來,倒不如說,他處于未來而到達,而且,唯有在他的詞語之到達中,未來才現身在場。[注][德]海德格爾:《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頁。
海德格爾之所以給荷爾德林如此高的評價,是來自于他對技術統治的世界的沉思煥發出一種力量。荷爾德林生活的時代與海德格爾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時代精神中。但是,對時代精神的洞察使得海德格爾在歷史中重新發現了荷爾德林的價值,讓哲學重新點燃了文學史沉寂的記憶,在20世紀讓人們又重新聚焦于這位德國詩人。阿甘本承接海德格爾的討論,在荷爾德林的詩歌中,進一步發現了“節奏”和“起源”是重新理解藝術本源結構的關鍵,“荷爾德林的這段話將藝術作品的根源性結構定義為‘休止’和節奏,這樣一來,作品的根源性結構就進入了一個跟人類在世界中的存在及其與真理和歷史之間的關系息息相關的維度。”[注]Giorgio Agamben: The Man without Cont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01.
哲人們發起的藝術的再經典化,或許在思想史上的意義要大于藝術史,但是越來越多的哲學家選擇回到歷史中的某些藝術家那里,回到曾經被忽視和遺忘的作品中,讓他們的時代理性釋放出更大的光輝:莫里斯·梅洛·龐蒂對塞尚繪畫中身體、目光和感覺的分析,德勒茲對卡夫卡小說中“少數語言”的抵抗策略的發現,阿多諾對勛伯格現代音樂中蘊含的辯證理性的闡述,德里達對梵高名畫《農婦的鞋》的再闡釋……這些思想家孜孜不倦地回到過去,在歷史塵埃中回望和凝視那些經典作品,德勒茲所說的“未來的功能”,就是說時代精神始終對重塑記憶和再造經典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