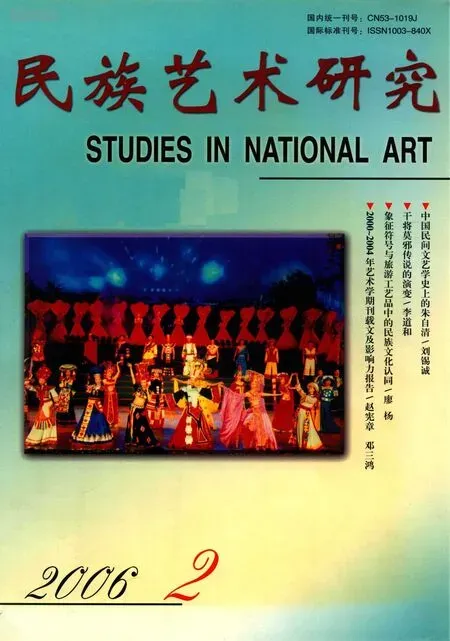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改本”之路與中國戲劇的現代性審美重建
張福海
中國戲劇自1979年底起始即在社會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同政治、經濟等領域的改革相呼應,在審美——戲劇領域提出時代的命題:實現戲劇的審美現代性。所謂戲劇的審美現代性,就是從戲劇的獨立存在出發,立足于人本主義立場,在終極意義上回到戲劇本身,回到人本身,革新戲劇形態,重建與再造戲劇的審美范式。這是中國戲劇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必須面對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時歷40年,當年戲劇界發出的“戲劇危機”的呼聲已無聲消弭;現實的狀況是,創作觀念陳舊落后,舞臺面貌僵化保守,演出劇目平庸低下。因此,觀眾以拒斥進入劇場的態度表達對高水準戲劇的期盼。歷史上曾經連綿不斷有過數度輝煌的中國戲劇,如今卻被人們棄之如敝屣,甚至成了人們望而生厭、幾近唯恐避之不及的怪物。戲劇由于無力回應現實人們的期待而退到審美的邊緣地帶,在遮天蔽日的物質世界的天底下成了一個凄涼孤獨的幽靈——時代拋棄了戲劇,同時戲劇也拋棄了時代。
如果說,1980年之前的中國戲劇是以近代性質為其特征的話,那么,1980年開始的中國戲劇由近代轉向現代的性質就決定了這個轉向的內涵是十分豐富的,因其豐富性而必然帶來走出困局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加之中國戲劇史上還未曾提供過這樣深刻動變的經驗,由是中國戲劇在實現審美的現代性道路上舉步維艱、充滿了困惑和茫然。中國戲劇應該怎么樣才能走出自身的困境,實現自身的現代性?鑒于40年的經驗和教訓,本文提出戲劇的“改本”問題,并認為以往所進行的每一次戲劇變革,每一種戲劇探索都忽略了、遺忘了或繞開了中國戲劇進程中這個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環;所以,走改本之路是中國當代戲劇進行現代性建設、實現現代性審美應該找回來、補上去并予以展開的一個歷史性的環節。
一、“改本”作為戲劇的現代性審美重建之路的內涵闡釋
在以往的40年里,中國戲劇為實現其審美的現代性,戲劇界曾有過多種改革嘗試,甚至還有人提出創造新的劇種問題。事實上,改革之路每向前移動哪怕是微小的一個步子都是艱難的,更遑論新劇種的創造!可是,生存還是毀滅?現實對戲劇的生死相迫,已經到了變亦變、不變亦變的地步。這個變,首先是集中在作為戲劇舞臺藝術基礎的文本的問題上;也就是說,戲劇的現代性是憑借怎么樣的戲劇文本形式顯現出來的問題。不過,這里說的文本,已不是以往我們所理解的那種僅僅為舞臺提供一個演出用的劇本,而是和整個舞臺藝術的創造結合在一起的一種間性文本。進一步說,通常意義上的劇本是在劇本創作之前它就已經先期被既成的舞臺樣式所決定了的,而這里所說的文本,其本身就是和舞臺藝術的現代性審美創造結合在一起的文本。所以,這樣的文本我把它稱之為“間性文本”;進一步說,間性文本的本質就是劇場性。在這個意義上來認識超越以往作為舞臺藝術基礎的劇本的文本,從地位上看,它無疑是舞臺將是何種形式、何種精神、何種面貌的基礎。中國戲劇現代性的審美實現先要解決的就是這樣的文本問題。
間性文本的創造并非一空依傍;那么,它的文本取向是怎樣的呢?我認為,它應該是建立在以古典(即傳統)劇本或劇目作為始祖本的基礎上的文本創造。這樣的文本,可名之為“改本”。
“改本”是以古典劇本或劇目為本事、為依托,并作為改本的原始素材或題材,對其進行根本性的改變和創造,即“改”其所“本”的“本”;這個本,就是原劇本(目)的根本,也就是它的精神性部位或精神基礎,予以改而造之。這里除了致力于植入一個新的靈魂、賦予一種全新的精神外,也包含了對原劇的發現、提取或發展、升華的某種趨向或某種質素——無論是哪種,其指向和定位是以現代人的審美觀念給予現代性審美的審視,從而使古典劇本或劇目經過現代性審美觀念的洗禮而獲得新生。這是所說的改本的第一個層次上的理念;第二個層次的理念是對改本“本”的“改”的問題。這里說的“改”,就是對待改本所改的“本”的情節、結構和人物的態度問題。古典劇本或劇目的人物的設計、情節結構的構成,都是基于作為其精神基礎的“本”上的,因此,根本之處既然已經發生了改變或重造,那么,對原有的情節和結構以及對人物形象塑造的考慮,當然也就不可能是原封不動的襲用(何況我們的態度是把古典劇本或劇目當作素材或題材來看待的),而是根據需要給予不同程度的改造和取舍,或創造其情節,或改變其人物的命運。對古典劇本或劇目所依托的劇種或所屬的劇種形態,從人物形象塑造、情節構造到舞臺上的表演形式、語言使用、音樂設計、舞美設計等方面,進行整體的創造性改造所完成的一種全新的屬于劇場意義的文本。這就是視古典劇本或劇目為題材或是素材的眼光所改的“本”。劇場意義上所改的“本”與所“改”的精神指向的“本”呼應,即改本的第一個層次和第二個層次兩個層次的共契,此即 “改本”的基本理念。換言之,“改本”就是用舊磚石瓦礫來建造新戲劇的大廈。2016年由上海昆劇團演出的明代湯顯祖的《南柯記》,便是本人的改本思想實踐的產物。作為改本,在此列舉四點:1.原劇中的大槐安國(螞蟻國),是作為客觀的存在表現的,改本則改造為淳于棼主觀變現出來的,是主觀意識的產物;2.淳于棼的夢,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夢,改本解讀為是表現淳于棼的意識流動的心理過程;3.淳于棼因醉酒而遭革職,是該劇的重大關目。改本對此關目詮釋為它的寓意性,即軍隊的整體化、規范化、等級化、理性化是對自由感性的個體生命的壓抑和泯滅。因此,淳于棼醉酒的非理性行為,是感性個體生命對理性、規范的體制的打破和掙脫。而淳于棼被所屬的群體驅逐出去拋棄掉的同時,也便獲得了作為一個獨立個體人的自由,那么其自我發展、自我創造、自我完成也就具有了可能性,如此而對淳于棼何以不回故鄉東平卻要客居揚州的追問也就得到了解答;4.淳于棼看破紅塵、實現精神的升華,他所達到的終極之境是與佛覺說相通的,契玄禪師就是這樣來理解的;但淳于棼自我完成的道路是不一樣的,這里很容易發生混淆的是,歷史上對淳于棼實現的精神超越多被解讀為佛教徒的開悟,如果是這樣,《南柯記》很容易等同于佛教教義的宣傳。改本的處理是,淳于棼的精神超越不是佛教徒為開悟而進行自我修為求證的結果,他是通過一夢而悟,因夢而覺。雖然達到的境界如同劇中人物契玄禪師所理解的那樣,但契玄禪師作為佛家人只能是站在佛教的立場上來解釋,這是從人物的身份出發所做的理解。這就決定了《南柯記》的性質是戲劇的而非宗教的,它不是宗教教義的宣傳,而是審美的創造。簡言之,改本的《南柯記》是從人物的意識流動著眼的一部心理劇——意識的活動;淳于棼在被群體拋棄后,因情致夢,在螞蟻國里經歷人生苦樂悲歡、榮辱興衰,夢醒后驚異于生命無常、逝者如斯,遂產生人與螻蟻何異的人生頓悟;劇中以淳于棼純粹的個體悲劇意識,創造性地描寫了他對世俗凡情的執著和掙脫與自我超越、自我實現的精神升華的情感痛苦蛻變的過程,從而把觀眾帶入新異的審美體驗之中。如此改本,力求創造出一個現代性的戲劇審美世界。
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改編不同于改本。改編是在近代的即社會學意義的指向上,對原劇人物或人物關系、情節等方面給予某種強弱程度不同的變化或調整而實現的。改編具有這樣幾個特征:1.是以各種不同的藝術樣式(如小說、電影、曲藝等,也包括戲劇不同樣式的轉換,如話劇轉成戲曲或戲曲轉換成話劇等)作為改編的對象,這種改編首先是在體裁即形式或形態上發生的轉換;2.強調對原作精神的忠實,亦即在忠實原作精神前提下的改編;3.保留原作的基本情節結構,如有變動也是進行有限的調整;4.保持原作的人物以及人物關系,不能有大的變動,但人物可以有增減。這四點是戲劇改編的基本原則。
還要指出的是,這里說的改本并不同于改編的原因是,以往的改編是造成中國戲劇走向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改編是對原劇本做近代意義上的改造,其宗旨是推陳出新,服務現實。如改編于清代傳奇《雙熊夢》的昆曲《十五貫》、改編于明代傳奇《紅梅記》的京劇《李慧娘》等,即是此類具有代表性的改編劇目。前者改編的主題是敢于“為民請命”,提倡調查研究,反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后者表現和歌頌的是反抗壓迫者的斗爭精神。這即是它們推陳出新的“新”之所在。可見,改編是從社會學意義的指向上使用、強調和在某種程度上變化原劇的情節、或者人物之間的關系;改編本的舞臺面貌一如舊觀。此種改編,重在思想教育和宣傳,使其發揮“武器”的作用,這便是服務于現實。
二、中國戲劇現代性建設的改本表達
改本是立足于對古典劇作或劇目賴以存在的“本”的“改”,改的目的是重建與再造一個現代性的新本,亦即把所改的古典劇本或劇目重建為具有現代審美精神的文本。如前所論,這樣的重建與再造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改編,而是在現代審美精神統領下“改其所本”,變革舊胎,脫離舊質;這樣的改本,也可以表述為翻舊成新、舊戲新作,呈現清代戲劇家李漁所說的那種“如閱新篇”的新的審美效果。翻舊成新,舊戲新作即是改本所奉行的基本宗旨。由于改本是基于古典戲劇、是對古典戲劇的重建與再造,故改本亦可稱之為“新古典主義”。
提出當代戲劇建設走改本之路即新古典主義之路,是對40年戲劇經驗及教訓的梳理和總結的結果,也是與中國戲劇的歷史所給予的歸向性的暗示的契合。多年來,屢有舊戲重作的劇目出現在戲劇舞臺上的現象,如上海京劇院的《貍貓換太子》、浙江昆劇團的《公孫子都》、浙江小百花越劇團的《梁山伯與祝英臺》、河南豫劇院的《程嬰救孤》等等。這就是說,這些劇院(團)雖然不是主觀上明確地意識到這條路向對于當代中國戲劇建設的至深意義,但在客觀上已經無意識地有了某種察覺,只是還不能有意識地停頓下來去認識它思考它。這些劇院(團)的舉措看似偶一得之,其實,并非這樣簡單,而是來自于歷史經驗的暗示:在戲劇史上,明代傳奇出現之前近兩百年時間里(1368-1567)走的就是一條改本之路。明代立國后為恢復被元蒙統治時期破壞了的漢文明進行了一場文化重建運動,戲劇領域取“宋元舊篇” 即宋元南戲予以儒家精神的改造與重建。我們今天看到的“荊、劉、拜、殺”(即《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四大南戲”,還有《琵琶記》等劇目,便都是宋元南戲經過明人之手加以改造過了的改本。明代的改本是一次成功的戲劇重建運動,它直接培育了之后誕生的傳奇。明改本的發生也不是孤立現象。在明改本之前,元雜劇的形成就是以宋雜劇、金院本的劇目為改本對象,其基本的思想理念就是對被傾覆了的漢人文精神的緬懷與光復的企盼,是充滿了悲金悼宋的情緒的,從而成就了元雜劇自身。本文提出的改本當然不同于元明兩代的改本,但至少歷史曾經給過我們這方面的啟示。
改本的現象不是中國戲劇所獨有,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現象。在東方,日本的芝居(しばい)、能樂(のう)和歌舞伎(かふぎ)也表現得很充分。如室町時代(1336-1573)之后能樂創作出現繁榮的景象,其中很大一部分劇目就是對室町之前的作品的改制。著名的猩猩劇目就有七個之多,后來還有了猩猩劇目群的出現,而這些猩猩劇目都是改自于15世紀室町時代的《猩猩》劇目。在西方,改本也體現在莎士比亞的戲劇創作上。他的37部劇作幾乎都屬于改本。而此前也有劇作家就他選擇的劇作進行過改造,但都沒有獲得像莎士比亞那樣巨大的影響。根本原因就是莎士比亞注入的是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精神而進行的改本的創造,而另外的那種改造不過是改編而已。莎士比亞的改本因體現近代的人文主義精神而取勝,使原劇獲得新生、重放光華,同時也創造出英國乃至歐洲戲劇史上一個新的歷史時代。有趣的是,進入20世紀后,莎士比亞的戲劇卻又不斷被現代主義的戲劇家們作為改本的對象,用現代主義的眼光加以重新改造;莎士比亞之外的西方古典的和近代的戲劇,也被后來戲劇家們作為題材進行改本創造。著名的法國古典主義劇作家拉辛的名劇《菲德拉》,就是改自古希臘戲劇家歐里庇德斯的《希波呂克斯》,而英國當代劇作家薩拉·凱恩的《菲德拉的愛》,則是改自拉辛的《菲德拉》。薩特的名劇《蒼蠅》,是根據埃斯庫羅斯的《俄瑞斯忒斯》這個悲劇進行存在主義的改本式創造的。類似這種古已有之的例子舉不勝舉,而在當今,則彰顯了改本的現象已有全球化的趨向——戲劇悄然進入題材上的歷史輪回,就其中的意義而言,表現的則是歷史和現實反思式的精神接力。
選擇舊戲重作的方法,是戲劇面對現實的一種自救而不是改本性質上的創新。雖然說改本本身也是一種自救行為,但是,改本是以創造的精神來進行戲劇自救的行動,而舊戲重作卻是不改舊觀、沿襲舊輒的重作。因此,我們現今看到的一些重作的劇目,最嚴重的缺陷就是沒有應有的現代性的精神因素為內蘊,所以注重的只能是戲的外部形式的“包裝”,風格、氣質和表演形式并未突破原劇的局限,因循的還都是老戲既定的、原有的旨趣。因此,除了舞臺上演員多、場面大、景象豪華壯觀、色彩華麗炫目之外,在戲劇應有的品格上,多數劇目反而還抵不上原劇的魅力;那種浮華、淺薄的靠外殼取悅視聽的嘩眾取寵做法,無疑是受到了多年來商業化的影響所致,觀眾并不看好。本文無意否定一些為旅游娛樂性而打造的大型實景節目的演出形式,但戲劇不能這樣搞,戲劇藝術不同于舞臺上其他任何一種類別的表演樣式,它不應該是像古代社會中被當成侍奉宴享以為助興的侍品,也不應該像今天還有人那樣把它看作是消遣和娛樂的物什;戲劇不是國內那些流行的小品,也不是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大片。戲劇是對關于人的最高問題即心靈問題的過問,如同宗教家或哲學家所說的是終極關懷。如此看來,時下某些重在場面、重在好看的樣子的老戲重作,無非是以往戲劇界所奉行的“舊瓶裝新酒”的做法在當代以相反的方式的應用——“新瓶裝舊酒”。這種名副其實的“新瓶裝舊酒”的方法,在表演、唱詞、唱腔、服裝、化妝等方面沒有什么進取,還是老樣子,不僅無補于戲劇困境的擺脫,反而會進一步傷害戲劇,把本來就處于絕境中的戲劇更快地向死里推,哪里談得上是戲劇的自救呢!正所謂未能自渡,焉能渡人?這就是說,舊戲重作,并不是頭腦一熱將其當成新點子就可以操刀來行事的。我認為,當今戲劇,每一部戲的創造都應該和戲劇的命運聯系在一起,這與戲劇的盛世時代不同,戲劇的盛世時代可以有各個等次的劇作出現,如我們今日看到的元雜劇作品或明清傳奇的作品,就有很多平庸之作。這在那個時代很正常,可以用“不可能部部都是精品”來看待。但在我們今天用這個尺度衡量就不行,因為我們今天的戲劇處在衰敗的時節,因此,任何一部劇作的生產都承擔著戲劇在存亡危急之秋如何拯救的一份使命,這就決定了任何一部戲劇的創造和生產應該是有品位、有檔次,可以影響全局的力作。這是當下即現實的要求。話要說回來,真正意義上的老戲重作——改本意義上的舊戲新作,已然不是我們從前的經驗所能完全勝任的,而且從前的經驗因之還要受到挑戰和質疑。這是因為,我們現在置身的人文環境與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同,是一個開新創造的時代,一個真正走向世界的時代。
然而,改本的“改”,不是某個方面或某個部位的改,而是整體的、全方位的改。如:與改本相應的人物的語言使用,應該采用現代白話;唱詞的撰寫,宜相應、適當地打破屬于古典昆劇的曲牌聯套體和京劇上下句的板腔體的體式,接受中國新詩的成就,從戲劇表現人的特點(即代言體)出發而加以改造(當然,并不排除對古典戲劇的借鑒),創造一種新型的現代白話體式的劇的語言模式,以表達人物的思想情感,但在舞臺表現上又能吸收古典戲劇語言中的裝飾性或具有符合改本人物需要的音韻特色,使其與現代白話的寫實性口語化有著一定程度的區別;人物的表演遵循虛擬性和程式化表演體系確立的原則,借鑒中外的舞臺表演藝術成果,創造超越物像的新的表演形式;音樂唱腔打破套曲的規范,更多地融入現代元素,提高速度和加快節奏;服裝、化妝符合人物塑造的需要和現代人的審美視覺理想。總的說,改本的“改”,即是對其原本所立之“本”的“改”,同時又是建立新“本”之“本”的“改”;也就是說,不但從本體上改其本來的主題思想,還要在文本形式上將其改成新的面容,這才是真正的改!在實際操作上,準確地講,改本,它是一種人為的構造,是制作或構造意義上的改本!正是由于它是以古典的劇本或劇目為材料的改本,因此,改本的制作是在不完全脫離或隔斷原劇提供的人物和情節的前提下,立足于人物,立足于戲劇精神,立足于創新,立足于視覺化感受進行的改本創作。簡言之,就是立足于現代審美的改本。這樣的改本,是在充分尊重中國戲劇的“劇統”(如建立在空舞臺上的時空觀念、虛擬性、程式化、歌舞化等中國戲劇建立起來的體系化的法則和軌范,本文對此稱之為“劇統”)前提下的戲劇創造。
三、中國戲劇由近代轉向現代審美的總體評價
戲劇是審美領域的一項創造性的精神活動,它與政治、哲學、道德等不同領域的不同性質的活動一樣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獨立價值,并和政治、經濟、道德等其他領域的建設與創造一樣,共同塑造每一個時代的精神面容。由于戲劇的本性是創造,因此,戲劇審美必將因其不斷地發現與創新而演變,從而導引著不同時代的審美取向。以1980年為標志的中國戲劇由近代向現代的審美轉向即如此:最初,就是“文革”結束后,戲劇界原本以為與人們久違了十年的古典戲劇(亦即我們通常說的傳統戲)開禁后會重現“文革”前舞臺的繁榮景象;可是,它的演出在短暫地紅火了一陣子之后即遭到觀眾的冷落。不久,戲劇界人士才恍然明白,觀眾更多的是圖看個傳統戲被封殺了十年后重又演出的新鮮感而來的,卻并不買賬。于是,為了把觀眾拉回劇場,戲曲演出團體通過推出改編、新編和表演手段創新的新劇目以吸引觀眾,但終難奏效。說到底,人們對這個時期的戲劇演出所表現出的冷落態度,實際上是對戲劇舞臺新精神、新面貌的企盼。所謂企盼新精神、新面貌,就是企盼符合人們現代審美要求的戲劇的表現;換句話說,就是對戲劇審美的現代性的要求。這是因為改革開放后,審美領域表現出的一個突出特征是人們已不再局限于從前那種孤立封閉狀態下的審美視域,而是把包括戲劇在內的本土藝術置于世界戲劇的環境里和背景下來進行考量的。這是必然的、不可限止的全球性的眼光。這樣,以回到人本身為內核的現代性審美要求隨之到來,中國戲劇由近代轉向現代審美亦隨之發生。可是,此時的舞臺演出尚未能超越近代性的戲劇觀念,于是,戲劇危機論和戲劇改革論的呼聲由此風起于戲劇界。這就是中國戲劇在20世紀下半葉面對的第二次重大變革。
中國戲劇由近代轉向現代審美,此前的第一次變革是發生在20世紀之初的1902年,即以梁啟超、陳去病、柳亞子等人為代表的一批銳意社會改革的知識分子所發動的戲劇改良運動。這次戲劇改良運動,其目的在于沖破古典戲劇的匡范,把中國戲劇推向近代,實現中國戲劇的近代性。因此,他們的戲劇主張和實踐,是立足于近代性質的戲劇變革,中國戲劇也以此為分野,從古典走向了近代。在迄今117年近代戲劇的路途上,如果以京劇為標志的話,中國戲劇歷經了“改良新戲”(如時裝新戲、時事新戲、古裝新戲、洋裝新戲等)、“海派京劇”、“舊瓶裝新酒”式的新編歷史劇和現代戲、“文革”時期的“樣板戲”等幾種不同式樣或形態的戲劇階段。
近代戲劇作為向現代戲劇的過渡階段,與古典戲劇相比較而言,其在精神指向上,是以實用功利(戲劇作為意識形態的載體)為特征的,積極參與社會的變革,同時強調人的價值,關注人的現實生存狀況;在美學追求上,重客觀再現,重寫實方法,也重視情緒熱烈的浪漫想象。但是,由于中國社會特殊的歷史情境所致,戲劇藝術因為長期的以社會學、政治化為主導形成的局面,致使其總體審美品格不高,關于人的塑造問題,總的評價還是匱乏的。后來,在“文革”中戲劇終于被推向極端政治化而走向末路。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戲劇的審美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就是實現戲劇由近代轉向現代的第二次審美變革。
然而,中國戲劇的現代性審美轉向斷然不同于從古典轉換為近代的情形,因為那種轉換還沒有使近代戲劇從根本上和古典戲劇拉開距離,形成差別;而現代性審美由于它的精神是立足于對獨立個體的人的生命存在狀態及其精神歸向的關注,同時,基于這種指向,其戲劇的思維方式、感覺方式和表達方式轉向重主觀表現、重藝術想象和重形式創新等等——這種轉向,無疑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全方位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哪個部位如形式上或技術(程式)上的改造或創新等此類外部的吉光片羽所能致用于全局、所能改變全局的。戲劇現代性的實現是一個整體,就如格式塔心理學所揭示的那樣,是整體大于部分相加之和;把它轉換為戲劇的表述就是,戲劇的現代性質決定每一個部分必須依據現代性質而改變。可是,由于我們以往所持的立場在本質上還是近代性的戲劇立場,講戲劇改革都是停留在外部形式上,即技術層面上(如創造新的程式,改造原有的表現手法等等)的,以為形式上的革新再加上題材好就是改革,殊不知觀念未變,“本”未改,題材再好,形式再新,花樣再多,也不過是外在的部分的相加,這樣的部分相加并不會使戲劇整體的性質改變。戲劇界直到今天,還在一直用這種元素主義理論的認識來理解和對待戲劇改革。所以,這么多年戲劇改革沒有能夠見到往前邁出具有實質性的一步。然而,戲劇的審美現代性由于它是屬于當代的,但對我們來說卻是陌生的,是需要我們通過創造來建立的一種當代戲劇文化,因而它毋庸置疑的屬于中國當代的現代性戲劇。由于是陌生的、是需要通過創造實現的,因此,戲劇的任何一種變革都會遭到傳統戲劇觀念的抵制乃至圍剿,況且改革要沖破的不僅是近代的戲劇觀念,還有古典的束縛。中國戲劇改革之艱難可以想見,事實也證明了它的艱巨性。
回顧中國戲劇的現代性進程,如果把這40年約略以每十年分作一個時段的話,中國戲劇表現出的主要傾向可以這樣來認識:20世紀80年代作為頭一個十年,戲劇問鼎現代性,走向改革創新的探索之路,這是在戲劇界人士高呼“戲劇危機”的憂患聲中進行戲劇自救的努力。第二個十年是20世紀90年代,戲劇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走向谷底,戲劇界期望通過適應市場的需要獲得戲劇的生命力,因而轉向對市場化或商業化效應的運作與追求。進入21世紀到現今,是第三個十年和第四個十年,中國戲劇在商業化的追求中全面失利。此間,中國昆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口述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接著是京劇(2010年11月也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遺”代表作)代表的一大批劇種成為國家級的口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對象。顯然,這四個階段不是戲劇現代性審美縱向的深入發展過程,反而是逆向的步步倒退,在倒退中也就把問題直拖到了淵底。“現代性”對中國戲劇幾乎成了一個被等待的戈多。但客觀地說,這個過程未嘗不是“反者道之動”,它是中國戲劇在實現審美現代性問題上的焦慮的體現與反證!在遙遙無期的焦慮中,人們似乎已經變得麻木了 。事實不然,《安魂曲》《背叛》《黑鳥》《哥本哈根》《阿波隆尼亞》在京、津、滬三地猶如節日一樣的演出,卻是座無虛席。可是,我們不能不正視四十年中國戲劇在追求審美現代性的道路上存在的問題。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來認識問題的具體表現:首先一個問題是,就是總是從事功的立場上看待戲劇,因此,總是把戲劇當作具有現實實用功能的武器來使用,而不是表現人的生命世界、揭示人的心靈,這就降低了也限制了戲劇自身所能夠發揮的審美功用;另一個問題是,不能從戲劇的歷史來考察戲劇演變的邏輯融通過程,因而未能提出實現戲劇審美現代性應有的具體的理論主張,以及具體工作的布局與實施方案;再一個問題就是,所持的戲劇觀念陳舊落后。從前戲劇觀念的變革和戲劇的創新無不是憑借某種思潮、某種運動而發生的。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戲劇的變革不否定確需外力的推動。但我認為,戲劇作為獨立存在的一門藝術,它對人的心靈狀態的敏感和自身運行的能力,本可以有力量像當年“海派”戲劇那樣,改變形態,革新創造。可是,這么多年里,戲劇的審美現代性問題更多的還只是一個流于空泛不實的口號;更令人憂慮的是,現在連這個空洞的口號都稀薄了。所以,戲劇作為一個民族或國家精神上達的標志,其應有的非凡的想象力和卓越的靈感,從天而降的才情和智慧等等凝聚在一起的神秘莫測般的創造力,難于降臨舞臺,故在實踐方面仍還處于近代戲劇的水準上。鑒于以上的實際問題,戲劇的改革創新即在實現其審美現代性的道路上才會徘徊難進,甚至是走一步退兩步。回顧20世紀80年代發生的那場戲劇觀大討論,雖然是建立在戲劇本體論上的立意,可是,涉及到戲劇審美現代性的具體問題卻很少觸及,尤其對戲曲說來,“現代性”幾乎還是一個空漠的概念。這樣,戲劇在無力提供具有現代性審美劇目、觀眾對劇場嚴重疏離和舞臺日益荒蕪的景況下,此時適逢古典戲劇作為遺產的出臺,就如同救命的稻草一般,使戲劇在瞻望前程無從擇路的境遇下,像“逃禪”似的退回到遺產守護的復古立場上。于是,戲劇界便借此形成了以復古主義為主導的演劇趨向。僅舉一例可證:單是以昆劇《牡丹亭》一劇進行演出的,就有美國版的、上海版的、江蘇省版的、蘇州市版的等各種不同版本的昆劇上演,另外,還有江西贛劇、京劇、雷劇等不同劇種的《牡丹亭》版本也跟著上演。這些《牡丹亭》都是在保護遺產的背景下超出了應有的常態性的演出,其演出也便因此具有了某種悲壯的神圣性。“保護非遺”成了復古主義思潮的庇護傘,不言而喻,創新是不受歡迎的,實則是被排斥的。可是,戲劇畢竟不是古戰場,觀眾也不人人都是古玩家,戲劇是為現代人的現代審美而存在的。那么,戲劇經過商業化和復古主義道路的嘗試后,就愈加清晰地彰顯出只有重建與再造、實現審美的現代性,才是中國戲劇通向未來的道路和慧命長存的根本所在。
四、“改本”是當代戲劇建設不可缺失的環節
本文認為,改本即新古典主義之路,是當代中國戲劇實現現代性建設不可失卻的一個環節。以往,我們曾熱衷于期盼現代題材的戲劇創造能給中國戲劇帶來一片新的天地,事實上卻事與愿違。原因在于我們習慣于把戲劇創造看成是某種社會運動的一翼或某種時代思潮的派生物,還不能把它作為一項獨立的審美活動來認識和對待。回溯中國戲劇近代史的每一個階段,包括中國戲劇從古典向近代的轉向之發生,可以說都是為特定歷史時期某種社會思潮或某種政治運動的需要而被作為使用的工具來發揮作用的。如1904年創刊的《二十世紀大舞臺》的創刊宗旨中即明確表示,戲劇改良,就是要使戲劇成為革命的助力,“以改革舊俗,開通民智,提倡民族主義,喚醒國家思想為唯一之目的”[注]《二十世紀大舞臺·二十世紀大舞臺叢報招股啟并簡章》,《二十世紀大舞臺》1904年第1期。。戲劇藝術一旦成為某種社會思潮或某種意識形態的載體,就必然會隨著特定時期的政治變化而起伏升降。然而,以過問心靈為元問題的戲劇藝術,要想在激烈的社會運動中完成自身的藝術蛻變,實現自身的審美創造,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證明,戲劇是藝術之“思”的產物,而非社會運動中的弄潮兒;一朝它被推到激烈的社會變革的前沿,它就必然會依從非審美的實用功利為取向的需要,不是變成武器,就是變成傳聲筒。一百多年里,中國戲劇幾乎都是在一個接一個緊張、急切而又激烈的社會浪濤中或發生改良,或進行革新,或實行變革。所以,在特定時期的社會運動的背景下,戲劇的改革要么太過急功近利,要么太過急于求成。在壯懷激烈中期望戲劇的建設或戲劇的創造朝發夕至,難免不令人驚異!在政治思想宣傳和戲劇藝術創造兩者之間,如果政治思想宣傳替代了戲劇藝術的創造,或者戲劇藝術的創造承擔了政治思想宣傳的功用,這種現象的發生,無論是對戲劇藝術本身,還是對政治思想本身,都是莫大的傷害。例如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之初的新劇種創造運動和數十年里大量的新劇目生產,最終的結局是怎么樣的呢!這是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依附于如此動蕩、激烈的社會環境來進行戲劇改革和戲劇創造,其結果不過是朝生夕死,最后都化作了云煙而消散。
我們一直缺少一種真正平和的、審美的社會環境和心態來對待屬于關注心靈問題而非社會問題的戲劇藝術。然而到了今天,經過40年的積累,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適于戲劇變革的土壤和戲劇生長的新的人文環境。這個環境是豐富復雜的,也是多彩多姿的,但表現得最為顯著的特征是既平庸又深刻,既膚淺又深沉,既世俗又神圣。這樣的環境把人們的心態磨礪得只能愈加趨向平和與深摯;只要我們回顧一下國內這些年來引起國民關注的一系列著名事件所表現出的理性態度,就會感受到清末民初梁啟超、嚴復等思想家們倡導的“開民智”的新民主張在今日已體現出“民智漸開”的新生面。人們開始回到個體回到自身,開始真正意義上對自我命運和心靈感受的關注;人們也因此開始需要關注訴諸靈魂的戲劇,戲劇也就必然需要通過自身的變革,以期進入時代的人們的心靈世界,人們的生命過程。
選擇走改本之路,有一個顯見的事實是,戲劇界對實現戲劇現代性審美曾致力于現代題材的創作,可是多年的實踐證明:現代題材的創作所帶來的諸多問題致使它不易成活;即便演出了,也很難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進入21世紀以來,戲劇界客觀上對現代題材的創作表現出的是一種回避態度。今天我們可以較為清醒地對現代題材的現代性審美創造難以成功給出兩個方面評價:一個是理論上準備不足,另一個是實踐上還沒有積累下應有的屬于新形態戲劇創造的經驗。因此,以現代題材進行現代性審美創作在今天還不能成為我們的主攻方向;而中國古典戲劇作為歷史上的完成態,如昆劇、京劇等早已走進了歷史并成為歷史。如果利用這種形式,像以往“舊瓶裝新酒”的方式進行改編或新編,那是近代性戲劇的做法(即便是近代性的做法,也存在諸多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卻不適用于現代性戲劇審美創造的理念和追求。這是因為作為現代性戲劇審美的這個“新酒”,其精神氣質已經不是“舊瓶子”能裝得了的,而且它還必將打破“舊瓶子”,重造一個不同于古典戲劇樣式、也區別于近代戲劇精神的新的戲劇審美范式。這樣的一種新的審美范式便是“改本”,亦即新古典主義。
選擇“改本”,是因為中國戲劇在建設現代性的審美問題上不同于西方的戲劇;中國戲劇有自己的“血脈”承傳,有自己的“劇統”體系。所謂自己的血脈、自己的劇統,指的就是它有完全屬于自己確立的一整套的舞臺法則。這些法則如自由的時空觀念、表演的虛擬化和程式性、演員的角色行當化,以及歌化舞化音樂化的樂本位觀念等等;同時,構成這些法則的具體形式的本身,是通過十分復雜的高難度的技術性表演呈現出來的。中國戲劇自近代以來經歷的歷次變革,無論是進(突破它)是退(保守它)還是守(利用它),無不是困于斯惑于斯無可奈何于斯所致。有兩個典型的例證:1918年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傅斯年、周作人等人在《新青年》開辟的關于舊戲改良問題的專欄里發表文章,提出創造新劇,主張廢唱用白,并把臺步、鑼鼓等等視為“遺形物”統統廢去[注]余上沅編:《國劇運動》,上海:新月書店出版,1927年版,第5頁。。可是,新劇到底應該是個什么樣子,“新青年”派的理論到此為止,并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可行性的描述。1926年,余上沅、趙太侔、張嘉鑄等人發起“國劇運動”,主張“要用中國材料寫出中國戲來”[注]1918年10月《新青年》第5卷第4號分別發表了胡適的《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傅斯年的《戲劇改良各面觀》等有關戲劇改良的文章。胡適在文章中把舊戲中的“臉譜、嗓子、臺步、武把子”等表現方法統稱之為“遺形物”,并提出“廢白用唱”的主張;傅斯年在文章中認為“創造新社會的戲劇不當保持舊社會創造的戲劇”“舊戲不能不推翻”。。那怎么樣才叫作“中國的材料”寫出“中國戲來”呢?他們認為:“這些中國戲,又須和舊戲一樣,包含著相當的純粹藝術成分”[注]余上沅編:《國劇運動》,上海:新月書店出版,1927年版,第6頁。。“國劇運動”派雖然在理論上對舊劇進行了深刻的理論研究,對未來的、理想的“國劇”也有一個初步的、不完備的設想,但是,恰如他們自己所說的那樣,“這個目的,祗能說是假定的”[注]余上沅編:《國劇運動》,上海:新月書店出版,1927年版,第6頁。在實踐上,“國劇運動”派和“新青年”派一樣,也沒有創造出實績。
希冀創造新劇以取代舊劇的“新青年”派和建設一種新型國劇以區別于舊劇的“國劇運動”派,之所以都沒有獲得成功,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對待中國戲劇的“劇統”問題上,前者想甩掉它,后者則想利用它。這樣的想法,無非都是從對中國戲劇進行新的建設出發的多種思考。因為我們對古典戲劇的既成法則和軌范既躲不開也繞不過去,可新的創造又沒有先例和經驗借鑒,因此,就只有自己來設計、來構想。他們堅持自己的戲劇主張,但卻對與同時期一些戲劇改革實踐取得的成效如時裝新劇、古裝新劇等新的戲劇樣式,似乎并不在意,或許并不是他們所追求的,故未提及。雖然如此,后來中國發生的每一次戲劇改革進入到實質性階段的時候,也就是在實際操作上應對具體問題的時候,都無外乎是就 “虛擬性”“程式化”“樂本位”“唱、做、念、打”“手、眼、身、法、步”等等技術性的問題如何解決而展開的。但我認為,盡管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可是,在實際的處理上,并不能僅僅解釋為單純的技術性問題,實際上是超越了技術性的層面的。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對中國戲劇的改革說來,已經成為問題的核心所在——它的背后隱藏的是一個關于現代性的重大命題。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中國戲劇在現代建設上,自從話劇被引進來之后,它擁有的表現現實生活的強大能力曾強烈地影響了人們的審美取向;因為這個緣故,許多戲劇改革者的戲劇實踐都情不自禁地向話劇舞臺靠近,甚至拿話劇舞臺的寫實性模式來規范戲曲舞臺的創造,1918年胡適等“新青年”派的戲劇改良觀就受到話劇的影響。出現這種現象當然也不難理解,原因就是為了尋求突破古典戲劇舞臺的路徑,迫切需要建立一種新型的戲劇舞臺樣式時,話劇的強大審美誘惑力致使戲劇改良派們希望能擁有像話劇那樣的藝術精神而愿意學習它、效仿它的一種努力。20世紀50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方法全面進入中國后,斯氏的演劇觀念引入戲曲,并以此對戲曲給予一定程度的寫實性改造,從現代題材的戲到古代題材的戲都接受過這種改造,后來則愈演愈烈。顯然,這是近代戲曲在自身改造中對話劇懷有的景慕心情的一種追求。后來人們把這樣的做法叫做是“話劇加唱”。這種方法由于存在的問題太多,戲劇界人士普遍認為不契合中國戲劇應有的精神,故頗多非議。
可見,在現代戲劇的建設上,面對中國戲劇的劇統,“舊瓶裝新酒”或“新瓶裝舊酒”的方式、“話劇加唱”的方式,以及關于舊劇的改良、守護、再造、否定等各種理論主張、理論設計[注]關于戲劇改良問題,在拙著《中國近代戲劇改良運動研究1902-1919》中,根據戲劇改良家們所持的不同態度和提出的理論主張,區分為舊劇改良派、舊劇否定派、舊劇守護派和舊劇再造派等四個理論派別。,總的說來,要么是鉆進去出不來,要么是跳出來跑得很遠,潛在的基本心態是既丟不起,又難得用。這里明顯存在著兩個關鍵性的問題:1.若進行現代戲劇建設,那么,現代戲劇的精神是什么?是古典的還是近代性的,抑或是現代性的?這是必須回答的。這就是說,什么樣的戲劇性質,便會決定用何種表現方法及何種表現手段。戲劇將因其性質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態,不同的形態便會有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來實現其不同形態所追求的戲劇美學目的。2.任何一種戲劇樣式都不可能憑空產生。歐洲的音樂劇是綜合了歐洲的音樂、舞蹈、戲劇等多種舞臺藝術創造出來的音樂劇樣式。中國戲劇進行現代戲劇建設,決定了它必定要以古典戲劇為創造的資源,并且遵循中國戲劇建立起來的法式規程,即中國戲劇獨有的劇統進行自己的創造。在確定了所要進行的戲劇創造屬于何種性質之后,那么,剩下的就是怎樣發揮和應用中國戲劇的劇統,以實現自己的戲劇創造,而不是背離中國戲劇的統系。這兩個問題顯露出進行現代戲劇建設所呈現出的一個被模糊了的地帶;這個地帶必須要明確、清晰起來,否則現代戲劇建設就無從談起。先就第二點講,現代戲劇建設本身所肩負的使命、發揮的作用是既能銜接過去,又能創造自身、承續未來的;回過頭來再說第一點,現代戲劇的建設,在性質上只能確立現代性的戲劇性質,這是現代戲劇建設不可動搖的總路線,此外別無選擇。這樣來看,戲劇的現代性質和具有肩負承續能力的戲劇樣式共為一體,這個模糊的地帶也便就此清晰起來了。這個地帶是什么呢?是“改本”,是“現代性”的“改本”。
如前所論,鑒于中國戲劇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本文提出確立實現戲劇的現代性為中國當代戲劇所追尋的創造理念,并選擇走改本之路,以為改本是區別于古典戲劇樣式的一種戲劇形態,這種戲劇樣式并不是完全的新,它的新應該是介于全新的形態和古典的形態之間的一種樣式。也就是說,這種新的戲劇形態并不是建立一個迥異于古典戲劇或與古典戲劇完全不可識別的新,而是相對于古典戲劇的那種古典樣式的新;這個新,是從古典戲劇中脫胎出來的,雖然有別于古典戲劇,但卻是可以識別、辨認的新。因此,改本就成為適合于中國戲劇開辟現代性審美之路的選擇,同時也彌補了中國戲劇建設中丟失了的戲劇本身邏輯演進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這個環節可以叫作戲劇史上的一個“歷史階段”。
結語:中國戲劇的理想國
中國是一個舉世無雙的戲劇大國;足以表征其戲劇大國者,是它有著久遠的歷史,擁有數百個劇種,有被稱為“曲如山海”的數萬個劇目。這是一筆偉大的遺產。所以,選擇走改本之路,可以會通古今,博采中外,緩解多方面的壓力,優先于全新創造的困惑,同時也能夠充分顧及民族審美的趣味。這樣,改本便成為我們戲劇現代性建設情之所由的選擇路向。
改本之舉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把當今中國戲劇變革的邏輯演進中一個缺失的環節彌補上來,成為現代性戲劇審美的創造,因而它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戲劇形態,也是中國戲劇的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此階段將成為橋梁通向中國戲劇的理想國。
改本面對的是汪洋一般了無涯際的古典劇本或劇目之海,其資源之豐富足讓人興嘆先輩創造了何等的精神偉業!可是,改本不是隨便哪個古典劇本或劇目都可拿來改的;改本是用現代性的審美眼光把古典劇本或劇目當作素材或題材來看待的,因此,這樣的眼光是極具選擇性的。如昆曲《牡丹亭》《長生殿》《南柯記》,如京劇《文昭關》《四郎探母》《斬經堂》等等此種古典劇本和劇目,就提供了可以賦予現代性的精神重建或再造的好題材、好材料,或者能夠開鑿出具有現代性審美品格的潛在質素。在戲劇世界里,我們會常常在一些古典劇作或劇目里發現足可啟示我們現代世界的因素,改本追求的現代性就是發現那個猶如阿基米德點的點,然后予以張揚和擴大,使之成為屬于現代審美的新文本——間性文本。
本文認為,改本的實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并應有一套精心設計的實施方案。如以一年的時間為規劃期,用兩年的時間進行改本創作,再用兩年的時間進入劇場排練和學術性演出,如此等等(當然這是一個預想,實際操作起來會更靈活)。就是說制定的方案里將顯示出改本從確定劇目到排練演出等具體實施的整個計劃和時間步驟。在操作上能夠通過一個劇團來具體運作。由于改本是中國當代戲劇建設的工程,這個工程本來就應該是志同道合的戲劇同仁共同具體實施的一個創造過程。還要指出一點的是,改本的實行,雖然在戲劇史上還找不出可以參照的經驗,但在組織形式上卻是可以從近現代戲劇史上找出一些可資借鑒的經驗的。如1911年7月在陜西西安成立的易俗社,它的組織形式和在劇目生產方面所制定的規章,都可以作為一定的經驗看待。此外,還有四川的戲劇改良公會以及話劇的春柳社等很多組織,都曾在實行戲劇改造和戲劇建設方面樹立旗幟、提出綱領、明確任務,并制定出周密的規劃,在實踐中也都取得了各自的顯著成績。這些歷史上的經驗很值得作為今天組織改本創造的參政。
在對待戲劇的基本認識上,戲劇仍是諸門藝術之王;在諸門類藝術中,戲劇無疑具有終極之美。人類的審美經驗表明,戲劇有著人類審美不可逾越的終極尺度,因此也是一個民族審美創造的最高體現。今天的中國戲劇,不應該憑借作為“世遺”或“國遺”的古典戲劇來支撐戲劇局面,也不應該靠欣賞國外的戲劇來補償國人對現代審美的需要。當代中國戲劇應當通過我們現代性的審美創造,使戲劇回到人們的審美生活之中,在現代世界戲劇的發展中貢獻我們的戲劇創造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