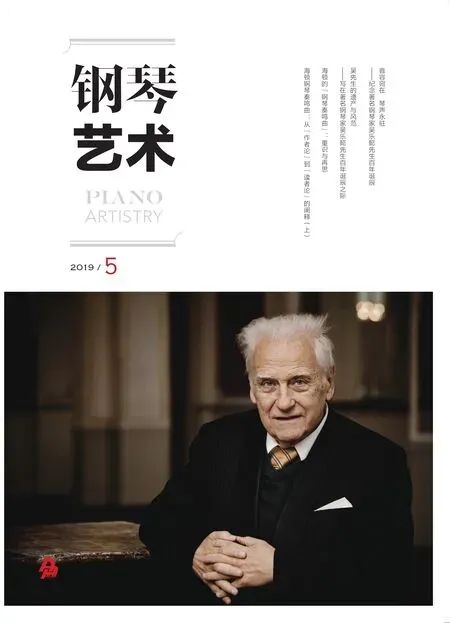圣誕禮物
文/趙穗康
圣誕節,到處都是堵塞的交通,所有人都沖著家人或聚會趕路,我也湊熱鬧,驅車去Brewster鄉下躲避。我怕節日,只想遠離人群。一小時之后,我踏進冰冷的屋子,立刻點上火爐。窗外遠在一片冬季疲憊的灰色朦朧之中。節日的喧鬧似乎已被趕過,留在看不透的薄霧背后。我身心懶散,爬進樓上臥室和衣就被,半睡半醒半夢,居然拖到半夜過后才漸漸醒來。我在床上眼睜睜地看著窗外一縷不太明亮的夜色,覺得自己是個剛從其他星球回來的小蟲。
我從床上起來,順著歡蹦亂跳的火光下樓。我呆呆坐在火爐前面,看著火苗靜靜跳舞,感覺周圍裹著一身空曠的寂寞,壁爐背后的煙囪,噓唏遙遠的古歌,一直通到屋頂之外的夜空。看來圣誕之夜已過,人們大概都已回到正常的生活節奏,此刻和著被窩香褥,夢想明天的瑣碎和成功。然而我這一邊,剛從昏睡之中爬出,沒事沒人,沒時沒空。環顧周圍,這小屋了然獨處山坡邊緣,圍在層層疊疊的樹木之中。我在方圓沒有人煙的屋里旁觀人世,聽上去很是浪漫,實際真的不然。隆冬寒氣夜霧風朔,盡管我有一點兒暖氣,還是冷得癟癟縮縮。我煮杯熱水,另加一件外套。我起身走到琴房,打開不太明亮的燈火,緩緩拉開厚重的窗簾,屋外一片漆黑。我無目的地坐在鋼琴前面,譜架上是橘紅封面的Haydn(海頓)Urtext鋼琴奏鳴曲第四本——多年前燕迪送我的禮物。我翻開第一頁,《e小調鋼琴奏鳴曲》。遲鈍的目光掃過上下跳躍的音符,手指順著鍵盤一路摸索。
Haydn,不可思議的Haydn。我總覺得Haydn是個謎, 一個不斷開拓新意的迷。Haydn奇巧風趣的樂思大概只有Mozart(莫扎特)可比,Mozart從Haydn那里學到很多,尤其是Haydn的機智風趣和出其不意的音樂游戲,只是Mozart能把棱骨分明清晰的Haydn裹上一層自己獨特的典雅風韻。
通常,Haydn被人看成一個承上啟下的中間人物,好像沒有前后左右,他的存在就沒意義。Haydn就是Haydn,是他自己完善的自己。Haydn晚年到達的境界,Mozart的優雅沒有沾邊, Beethoven(貝多芬)的精神沒有關系。Haydn不是Mozart的自然流露,也不是Beethoven的精神意志①。Haydn是自己音樂的旁觀,也是萬花筒的創意奇特。Haydn的音樂沒有迷人甜蜜的氣息和龐大連篇的情緒,Haydn的音樂是好奇的游戲——因為局限的自己不在,所以創意的空間反而無限。Haydn很少重復自己,他從微末具體開始,在靈感的閃爍之間,抓住瞬息即變的鍥機。他的主題簡潔明了,但是他的和聲翻轉魔變出其不意。Haydn沒有自戀,很少流連忘返,剛剛出現一個轉機,隨后又是搖身一變。他在音樂語言上的不斷探索好奇,非常接近批判自審的現代藝術。Haydn的音樂讓我們看到無數的窗口,給我們提供了可以不斷試探不可能的可能。
Haydn一生創造生涯的演變過程跨越了不可思議的幅度。羅森(Charles Rosen) 在他的The Classical Style里面,描述Haydn用了兩個章節,一個是Mozart之前,一個是Mozart之后。另人驚奇的是,Haydn的創意從純粹音樂語言游戲的角度,最后達到一個如此靈魂出竅的神奇世界。
一次Mozart被問誰是維也納最好的作曲家,Mozart不加思索,回答是他自己,但是Mozart隨即馬上改口:不,不是,是Haydn——不是因為Haydn曾經是他老師,而是Mozart非常清楚Haydn音樂里面每個細節轉折的奇特樂思。這不是“靈感”, 也不是意志,這是藝術創作最最根本的基因。盡管Mozart的音樂表面 “優美甜俗”,但是很少音樂家會對Mozart提出批評②,盡管Haydn的音樂沒有Beethoven的氣勢宏偉,幾乎沒有音樂家會對Haydn提出異議,關鍵的原因在于,只要你能真正進入他們音樂語言,你會非常驚奇音樂魔變的無限可能。兩位音樂大師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浮華喧囂的噪音,沒有不破不立的革新立場鮮明。Mozart把激進的樂思裹在優美的外衣里面,Haydn把不可能的可能編織在清晰精煉的骨架之中,
Gould(古爾德)很早就和“CBS”簽署錄制Beethoven全集的合同,可他遲遲拖延,結果未曾完工。但在最后重新錄制Bach《哥德堡變奏曲》(Goldberg Variation)的同時,卻又加錄了Haydn六個晚年奏鳴曲。至少我沒看到Gould特別提及Haydn晚年奏鳴曲。可我第一次聽到錄音,不禁一愣,Haydn居然還有這樣的作品,隱隱之中覺得,又是Gould慧眼出奇,重新挖掘作品新意。這種誤解一直要到自己琴上聆聽Haydn的時候,方才恍然大悟:Gould一點兒沒有夸張,神奇的Haydn,晚年真是達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境地!相比之下,所謂 “古典風格奠基人”“交響樂之父”“弦樂四重奏的范本” ,桂冠種種,都不足以掛齒。連同他的晚期弦樂四重奏,Haydn最后達到的不是音樂學和音樂史上的 “里程碑” ,而是創造一個純凈的、充滿精靈的天上人間。
我這琴房不大,占據屋子中間的鋼琴有點兒像個巨獸怪物。為了視譜,我打開房間一端的吊燈,不太明亮的燈光投在譜架和鍵盤上面,譜面明凈的背后,鋼琴躲在一片昏暗之中。可正是通過前面這片虛無的空幻,透過背后的落地窗戶,我能感覺野外四周森林寒木的寂寞。鋼琴清晰空靈的聲音,像是神光天漏,也像一束救命的篝火,然而,讓我身心通透的不是那簇暖意融融,而是從這昏暗虛空里面滲透出來的聲音。因為我一直喜愛Haydn晚期奏鳴曲,所以平時常常禁不住去摸,但是這些聲音從來沒像今夜這般靈竅魂出。
這本Haydn奏鳴曲集包括從No.53的e小調到最后No.62的降E大調。我一頁一頁翻閱過去,除了這“篝火”的一簇和周圍漆黑的一片,身邊只有天上的聲音,一清一明,一遠一近,一閃一爍,一透一靈,一待一期,一起一落,一點一片,一絲一縷,隨手隨攏,隨意隨心。
我喜歡《e小調鋼琴奏鳴曲》的每個樂章,Haydn晚期奏鳴曲的因素這里幾乎都有。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奏鳴曲,末樂章淡漠遙遠的神奇,用委婉的細言密語反復說出——知道這里我是自相矛盾,就是不知Haydn怎么鼓搗出來這樣的聲音。
樂譜上面涂有以前淡淡的鉛筆字跡,第三樂章譜頁角上寫道:
不是裝腔作勢的高貴,而是自滿自足的不俗和發自內心的喜悅——不動,保持絕對的拍子,千萬別動!
我對這個樂章特別鐘情,那是因為我一開始就曲解誤讀,而且不得不固執自己的錯誤。樂章開頭清楚注明Vivace molto (很活潑的)、 innocentemente(天真的),音樂是個活潑的快板,可我就是彈不到那個速度。這里不是技術問題,因為技術并不困難。可這音樂速度一快,我所聽到的東西全都逃之夭夭。這是天然純真的舞步,不是地上矯揉造作的天真。我踏著不緊不慢的步伐,保持節拍穩定不動,連裝飾音都不敢隨便出軌。我逐節向前,不敢出氣,更不敢斷氣,持續不動和控制有方的節奏氣場,使得和聲變化清晰可辨,音樂內在的語態一晃一閃,透出一種特殊的張力和波動。
樂章的末尾不斷地給你就此結束的錯覺,但是隨即引出一個又一個的驚奇。第101小節回到主題,但是感覺不再一樣。第109小節的裝飾音一個轉向,重新打開一個語境,第113小節在高八度上重復,似乎趨向結束,但是沒有,第114小節邊上又有鉛筆字跡:“話又說回來了。”這還不算,僅僅117一個小節,音樂就在天上,鉛筆字是“空音”,但馬上又是一個轉折,第120小節的左手把整個和聲扭轉回來。音樂進行到第126小節,看上去音樂真要結束,可這小節最后吊在高音b上——每次轉出新意都有它的影子,真的,第127小節是從已經關閉的門洞里面,徒然轉出一個新鮮清麗的亮光,隨即音樂把前面樂句一并席卷,簡練不膩干凈利落地結束了這個樂章。第127小節邊上的鉛筆字是:
What a surprise! Keep coming.Keep the pace,straight to the end.
頁末:Such a tenderness and joy,又 What a great sonata.Art only, nothing else.
《F大調鋼琴奏鳴曲》里的Larghetto ,譜子上有以前的鉛筆字“一上來就是高遠”,好像我真是中了Gould的毒,但是,即使沒有聽過他人的錄音,沒人對你說過應該如何,我想如果能夠直接琴上聆聽下面句子,不信聽不到這個信息:
我隨音樂飄忽周游一個個奇異的世界。《降E大調鋼琴奏鳴曲》第二樂章,每個小節都讓我屏息聆聽。出其不意的音響到處都是,一個更比一個神奇。在繾馳不動但又寂靜空幻的暮色里面,我的手指在琴鍵上下左右溜達逗留,感覺是在紙上推拿點撥筆觸。我發現自己不是彈琴弄樂,而是敷色潤筆,揮毫點墨,奇怪這手好像不是我的,它們徑自跳舞,怎么就在鍵盤上面突然如此靈活,何時我的手指功能,強到可以自說自話的地步?真真不可思議。
最后一首奏鳴曲,更是一時天上,一時人間。這里第27小節的音樂絕對不是現世的聲音:
以前鉛筆的涂抹和音符攪在一處,神奇的聲音從夾層里面飄逸出來。和聲暗中的手腳,把我軀殼肢解,席我心神他去。我一身輕盈,不覺自己存在,傻乎乎地被它牽引,在不斷變幻的風景里面被動。這有點兒像寶玉夢游仙境,可他至少還有一點兒模糊的世間關系,我所面對的景象卻是完全莫名,似乎多了一點兒不拘的單純,多了一份不期的無知,有點拉洋片的感覺。可這洋片不是拉給我看,因為我就是洋片。我的身心透徹明清(靜),我沒自己,景是我,我是境,同時隨著時辰泛溢一起去瘋魔。我都不好意思把譜子抄在這里,因為那得整段整句整篇整頁,每個細小的轉折都有前呼后應,每個平淡的步履全都埋下不是微妙就是奇妙的新天地。我更不想分析,這不但無聊,還把超然他去的軀體踩入塵土。我在飄,我在飛,我沒呼,我沒吸,我不是人,也不是物,不是鬼,更不是魅。那時的我,靈魂一定出竅,心神一定落谷。我身輕無骨,心平如鏡。我的感觸沒有,唯獨聲音穿梭,過網越界,走海入空。這是無中的有,太有了,連自己的在都沒了知覺。
一百多頁的一本樂譜翻到盡頭,最后一個音,最后一道門。當一口氣喘過來時,屋里奇靜,空氣凝聚在角落。突然覺得身子有點兒分量,窗外晨光微啟,地面似乎冉冉昇曦,軀體猶如晨霧一般緩緩下沉。另一個世界的光亮破漏進來。我還在琴上,沒動。左手撐著白紙黑線的樂譜,似乎想要抓住什么,又像企圖擋住妖魔鬼怪左右:“唉,Haydn。”此刻,我甚至都說不出這個樂迷爛熟的名字,更不敢想象Haydn那些古怪滑稽的肖像面孔。
屋子里面依然生息全無,我的手還在琴上,通過琴鍵,十指流通過來,依然還是暮色里的聲韻。
我終于如夢初醒,對這鋼琴和樂譜拜了一拜。我從琴凳起來,走出琴房,拉上門環,去到圣誕之后現世的一天。
2012年12月Brewster, 紐約
注 釋:
①這種說法有點兒“詩意”的偏激,事實上,Mozart并非自然流露,Beethoven也不是只有精神意志。Mozart的音樂是人生戲劇的所有面目:無傷大雅的惡作劇和無賴的殘忍得意,柔情蜜意的溫馨(tender)和天上超越的神性,Mozart的厲害,就是能把所有的技術奇巧和戲劇風波藏在優美典雅的音響里面。Beethoven承傳Haydn和 Mozart 的痕跡到處都是,他在音樂語言所下的苦功,盡管沒有Haydn 和Mozart的輕巧靈敏,但是他的音樂語言從完全不同的角度,超越了純粹的音樂語言,從而魔變出來一個現代精神的巨人, 以至于之后西方音樂,長期都在這個巨人陰影下面。Haydn 、Mozart、 Beethoven,三個人同在一個相近的時代,同出一個類似的音樂風格,但是,他們給于人類的音樂文化三個完全不同的音響世界——可見我的文字自相矛盾,這里沒有半點評判的意思。
②大概只有Gould曾經說過,Mozart不是死得太早而是太晚——這話聽來有點兒殘忍,但是Gould有他特別的角度,和Mozart具體的壽命長短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