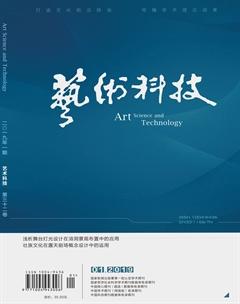中國“喪文化”現象的亞文化研究
摘 要:“喪文化”是被青年群體在社交媒體上廣泛使用和傳播的一種亞文化現象,反映的是一種集體焦慮感。中國的“喪文化”有著和美、日等國不同的特質。亞文化特有的抵抗性在“喪文化”使用和傳播過程中被逐步消解。“喪文化”不等同負能量,在中國呈現喪表達不喪行動的特征。本文闡釋了“喪文化”的由來和現狀,并進行了亞文化分析,對其背后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思考。
關鍵詞:“喪文化”;亞文化;青年群體
2016年,“葛優癱”爆紅于網絡,其生無可戀的表情與癱倒的姿勢戳中了年輕人的內心,在社交媒體中紛紛進行自我表達,帶動了中國“喪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面對“喪文化”,不必視為洪水猛獸,應分析其在中國呈現的獨特亞文化特征。它不只是一種流行文化,還是一種態度集成,表達的是焦慮需要被關注和重視。
1 “喪文化”概述
“亞文化常被認為是與主導文化有區別且共享于某些社群中,具備一定反叛色彩的文化。”[1]中國的“喪文化”雖使用了部分外國符號,但由于國情、思想等差異,在傳播形式和程度上與美國、日本等國有著很大不同。
中國“喪文化”爆發于2016年7月,微博博主@青紅造了個白,發布了一張“葛優躺”圖片,配文“全體頹廢中”,被瘋轉并爆紅,青年群體不約而同地響應。隨之,明星、微博大V等意見領袖加速了傳播,企業也使用這些“喪符號”進行營銷推廣,這種本土的、帶著自嘲外衣的“喪文化”,在青年群體中火了起來。
中國的“喪文化”除了圖文表達,還有音樂形式。2016年7月28日,《感覺身體被掏空》這首歌火極一時,歌中不斷重復的“不要加班”表達了上班族的無奈。2017年初,歌曲《我已差不多是個廢人》又被青年群體廣泛傳播。除此,因企業的營銷推廣,“喪文化”進一步走入日常生活。2017年4月網易新聞與餓了么在上海推出快閃“喪茶”,此外還有“沒希望酸奶”、江小白喪文案、520分手花店等品牌營銷。但中國的“喪文化”有著不同于美、日等國的特質,可以形容為“道路雖坎坷,但歇過之后還要繼續”。雖然它對成功學進行了解構,但并非想徹底放棄,最終向往的仍是成功,只是娛樂化被放大,抵抗性減弱,直至消解。
2 “喪文化”現象的亞文化分析
“喪文化”傳遞的是青年群體看似自嘲,卻十分深刻的訴求。通過心理學、語言學等視角,了解和分析“喪文化”,有助促成背后問題的解決。
2.1 從習得性無助到產生主體意識
美國心理學家賽利格曼提出“習得性無助”概念,認為人對自我能力和環境控制的知覺是從經驗中習得的。在無意識地學習后,感受到了無助,從而形成在心理和行為上的消極狀態。“當努力遭受多次失敗后,他將停止嘗試,并把這種失敗的感覺泛化到所有情景中”。[2]這種在觀察和體驗后習得的無助感,能產生如親歷般的認同感。當意見領袖如大V、名人用“喪文化”自嘲,青年群體觀察后加上親身感悟,很容易產生這種習得性無助感。無助感也促使主體意識在使用“喪文化”中產生。這種主體意識的喪表達是在理想與真實自我產生差距時進行宣泄的出口。
2.2 自我反諷實為自我保護
“喪文化”的嘲諷對象一般是自身,這種“自嘲”行為,實則是自我保護。反諷修辭傳遞兩種含義,一是字面意,二是引申義。“強調的看似是外層的價值觀,而真正的用心卻在隱含意上”。[3]否定與認同通過“自我反諷”融為一體,保護著青年群體的內心。自我反諷的原因有三:首先,媒體環境對于青年群體的干預、影響和滲透超越以往。第二,由于媒體良莠不齊,主體進行信息接收時沒有了“子彈論”般的信服,有很大的懷疑和反抗空間,使原本自我批評的想法化為了自嘲,但背后想要表達的是對自我否認之否認。第三,通過嘲諷自身,來降低社會、家庭等對于自己的預期,自己先行否定,避免給他人帶來更大傷害。
2.3 “喪文化”在社交媒體中的表演行為
社會學家戈夫曼提出過“在人際交往中的‘劇本 ‘表演等概念”。[4]“喪文化”的傳播和使用多在社交媒體中,社交媒體也是當今青年群體進行人際交往的主要方式。喪表達其實是一種情緒表演,并非真想要無所事事,與頹廢還是不同的。形成這一表演行為也出于上文提到的自我保護,“喪文化”的使用者率先開展自身攻擊,這種自我評價很大程度上是對事實的一種放大,往往是不客觀、帶有表演色彩的。這種表演通過對“喪”符號的使用,建構出“喪氣十足”的自我形象,達成夸張自嘲、自我保護、抒發焦慮、甚至單純娛樂等目的。
2.4 “喪文化”的模因
1976年,英國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提出了“模因論(memetics)”,它同樣可以解釋文化進化規律,即通過“模仿”可產生相似的“復制”,可稱為模因。不論是喪段子還是喪圖文,讓“喪文化”得以火熱傳播都與其具有可模仿的特質有關。而“喪文化”得以廣泛傳播不是因為對于“葛優躺”的完全復制,模因傳播的強弱還取決于是否得到受眾的廣泛認同、社會的情境及使用者的心理境況。“喪文化”中的因子正符合這些特征,所以借助互聯網環境不斷被模仿、復制。
2.5 “喪文化”——抵抗的消解
“喪文化”和“屌絲文化”是有一定聯系的。二者的相同之處在于自嘲和自我污名化,不同之處在于“屌絲”群體有著更強的內在反抗精神和強烈的抵抗及不滿情緒。“喪文化”除了表面的無力感,還帶有很大的娛樂特質,抵抗性不再那么強烈,自嘲是用來與自我的內心沮喪達達成和解的,雖然無奈,但還要繼續前行。由此可見,并不是所有的亞文化都呈現反抗特性。與“屌絲”現象相比,“喪文化”的娛樂、和解特質更強,抵抗性卻在過程中逐漸消解了。
3 “喪文化”背后的問題反思
面對“喪文化”,不能單純將其視為一種流行文化,也不能粗暴地歸結為“負能量”,它反映了社會和青年群體存在的切實問題,需要被關注和解決。
第一,“喪文化”并非真“喪”。在面對失敗時,青年群體在“喪文化”的話語共享中得知他人面臨的境遇是相似的,失敗不完全是個人問題。雖然呈現的外部表征類似于自我放棄,但經大部分青年群體后續的行動來看其文化內核仍表現為“不放棄自我”,只是和倡導的正能量有所不同。
第二,“喪文化”側面反映了社會進步。在提倡弘揚正能量的同時,青年群體“言喪”行為雖不被看好,但也被默許存在,反映了社會對自我表達越來越寬容。不極力打壓,而是寬容對待,使得“喪文化”沒有呈現強烈的反抗特征,讓青年群體在釋放焦慮后,能夠清醒地認識自己的責任。
第三,青年群體需被關懷。雖然嘴上喊“喪”,但手上的工作根本不敢停,這種現象側面反映了節奏加快、階級固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讓已入、初入和將要步入社會的青年壓力倍增。雖心有不甘,但個體無法改變社會,確實影響了青年群體的情緒,需要關注和關懷。
第四,“喪”要適當。面對壓力,青年群體可以選擇用“喪文化”釋放,但不適合長期在社交過程中使用,很容易養成使用消極用語的習慣,不但會為自身營造低迷的生活情境,還會造成人際關系的不和諧,在與同事、家人等不同性質群體交流時,很容易造成溝通的失序。
第五,新媒體需正確引導。具有公共性的空間被哈貝馬斯稱為“公共領域”。“新媒體作為公眾傳播信息、發表意見的平臺,有利于公共領域的建構”。[5]應該發揮其優勢,對“喪文化”進行正確引導,不能隨波逐流,肆意生產相關熱點。
4 結語
中國的“喪文化”呈現出與他國、其他類似文化不同的亞文化特征。特定的社會、群體以及特定時期都會對群體文化產生影響,正如弗洛姆的“社會性格”概念闡釋的那樣:“一個社會想要維持正常運轉的狀態,就會培養人去適應這個社會需要的特定的性格結構。”所以,對待“喪文化”應該更加理性、審慎和客觀。
參考文獻:
[1] 陳一.新媒體、媒介鏡像與“后亞文化”——美國學界近年來媒介與青年亞文化研究的述評與思考
[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04):114-124+128.
[2] 胡泳.新詞探討:回聲室效應[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6):109-115.
[3] 張少文.舊瓶新論——論浪漫主義反諷的敘事體式[J].外國文學,2003(5):64-69.
[4] 張長磊.戈夫曼“戲劇理論”視角下的社交媒體表演研究[J].西部廣播電視,2017(15):15.
[5] 于風.喪文化傳播中新媒體的角色分析[J].新聞研究導刊,2016,7(23):81.
作者簡介:李瑤(1995—),女,內蒙古通遼人,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7級研究生,研究方向:新聞傳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