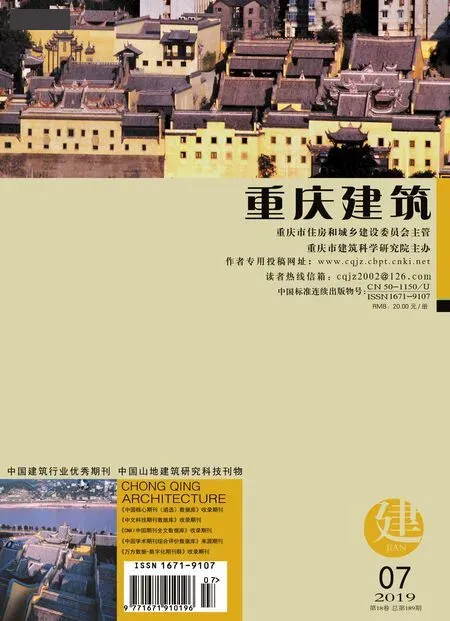吊腳樓:特殊的分類與生命的啟示
——漫談重慶吊腳樓之五
周毅

重慶是除湘鄂西、黔北地區以外吊腳樓分布最為集中的區域。由于地域寬廣、民族眾多、歷史背景、社會經濟、生活習俗、自然環境等因素影響,區內吊腳樓在文化屬性、使用功能、建筑材料、建筑結構、建筑形態等等方面,都存在著巨大差異,如土家族、苗族吊腳樓,其底層為畜圈、廁所或存放雜物之處,與川東沿江臨河的高筑臺、長吊腳、深出檐、無拘束的吊腳樓相去甚遠。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僅以某一種方式對重慶吊腳樓分類,并不能完全表達它的諸多文化屬性和內涵,我們可以根據它的不同屬性和需求,按不同方式進行劃分。
可分為:主城核心區吊腳樓、城區吊腳樓、場鎮吊腳樓、鄉村吊腳樓和民族地區吊腳樓五大類型。
重慶主城核心區吊腳樓:指位于長江、嘉陵江兩江四岸的“重慶城”、“江北城”和“南岸老街”這一核心區域的吊腳樓;
重慶城區吊腳樓:指除主城核心區外,其他城區的吊腳樓;
重慶場鎮吊腳樓:分布在重慶各地場鎮的吊腳樓,涵蓋磁器口古鎮、偏巖古鎮、路孔古鎮、中山古鎮、安居古鎮、龍興古鎮、豐盛古鎮、松溉古鎮、淶灘古鎮、龔灘古鎮、塘河古鎮、龍潭古鎮、雙江古鎮、西沱古鎮、寧廠古鎮、東溪古鎮、濯水古鎮、洪安古鎮、長壽古鎮等等;
重慶鄉村吊腳樓:分布在重慶廣大農村地區的吊腳樓;
重慶民族地區吊腳樓:分布在土家族、苗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吊腳樓。
重慶民族區、縣、鄉,都處在武陵山脈的腹心地帶,蘊藏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獨特的民族文化資源。位于渝東南的重慶市黔江區、石柱土家族自治縣、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是重慶少數民族主要聚居區。一區四縣總人口約289.48萬,其中少數民族人口158.6萬;面積1.69萬平方公里,約占重慶總面積的五分之一。
還可以按使用功能劃分為:住居型吊腳樓、店居型吊腳樓、店鋪型吊腳樓、公共型吊腳樓。
按生成年代劃分為:傳統吊腳樓、近現代吊腳樓、當代吊腳樓。
重慶吊腳樓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殊地域環境下,從干欄式建筑基礎上演變出的一種獨特建筑類型,受移民文化、川江航運影響較大,環境適應性強,平面緊湊、布局靈活,功能單一,不拘一格,可充分滿足生活、生產所需。經濟適用,空間劃分靈活,利用率極高,多以聚居形式存在于坡地及江岸。
重慶城區吊腳樓大多采用捆綁結構,工藝簡單,易于掌握,建造容易,施工速度快、造價低廉;穿斗結構吊腳樓,多應用于場鎮及民族地區,有其獨自的文化屬性和特點,平面規整,精雕細刻,受力傳遞清晰,構架間既相互聯系又相對獨立,構件組合簡潔明快,加減隨宜,無論是水平擴展或是豎向伸延均具靈活彈性,所以適宜于在重慶山地地形建造。

圖1 重慶吊腳樓建筑材料的選擇以竹、木等自重輕、受彎、抗剪性能良好的材料為主

圖2 重慶吊腳樓建筑形式內在的適應性與生命力,造就了這種地域建筑現象的產生、發展與運用
重慶吊腳樓建筑材料的選擇以竹、木等自重輕、受彎、抗剪性能良好的材料為主。外墻多由竹編夾泥墻或木板墻做成,屋頂多為小青瓦雙坡懸山式,樓面采用簡單木地板,建筑自重輕,也較為安全。除了運用吊腳,還常結合分臺、懸挑、附崖等手法,取得懸虛構屋的效果;其規模尺度較小、平面進退有致,使得大部分重慶吊腳樓靈活的適應山形變化;在地勢狹窄地段,重慶吊腳樓僅用簡單的支撐,使人感覺危險,但其實牢固耐用,也使其具有空靈、輕巧的形態特點;而在建造時,重慶吊腳樓采用本土材料,裝修簡單,古樸自然。
重慶吊腳樓建筑形式內在的適應性與生命力,造就了這種地域建筑現象的產生、發展與運用。昔日破爛的吊腳樓已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這固然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然而這種蘊涵了山城上百年風化史的民居,有其合理性及可取之處,它的理念、精神內核應該繼承和發揚,它具有強大的適應力,它是可以創新發展的,并不會因為生活方式和時代改變而被拋棄。在生態文明時代降臨的今天,人們須重新思考與自然、與社會的關系,而重慶吊腳樓脫離大地的形式將有助于滿足生態趨勢的需要,使人們從與自然的對峙,從忽略社會性的人,到謀求與自然對話,模糊人與自然的鴻溝,建立更加健康的人居環境。對重慶吊腳樓歷史、空間、品質、建構等初步的剖析與歸納,可以明確地肯定吊腳這一方式得以生存、發展的必要。重慶吊腳樓雖然有其缺陷,需要一個完善的過程,但從其核心價值的歸納中,已經可以感受到這一古老圖式的現代生命力。它作為山地民居的一種重要類型,借鑒其有指導意義的地方,改善其不妥的地方,賦予這種古老建筑以新的形式和內容,促使其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人居環境建設等邁上新臺階,使之與現代文明相結合,創造出更宜人的居住環境,使其煥發出強烈的生機和活力,實現其時代傳承非常有意義。以往的吊腳為生存所迫而生,今后的吊腳可以因精神寄托、可持續發展等需要而生。
近現代中國,由于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入侵和東洋鐵蹄的蹂躪,曾使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遭遇了漫漫黑夜。東西方兩種迥然不同的哲學觀,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走向了各自的極端。“天人合一”演變出的消極保守和“以人為本”生發出的貪欲狹隘,激化了東西方文化的矛盾沖突,工業革命更加劇了地域經濟發展的“馬太效應”。強權殖民,一度扭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進程和脈絡,使眾多炎黃子孫迷茫在現代與傳統的十字路口,失去了文化自信與自尊。
當今世界,全球經濟一體化,給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了良好契機;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城鄉建設一體化的同步,為地域建筑的復興帶來了難得機遇。隨著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特別是在基礎經濟建設取得驕人成就的歷史背景下,過去的山水重慶早已成為殘存的記憶。如今的重慶僅都市區就由中部、北部、南部、西部、東部五大片區,共21個城市組團構成,并以片區為格局組織城市人口和功能,各片區城市功能完善,均具有相當的人口規模。重慶城鄉規劃多中心、組團式構想的實現,帶來新型城鎮空間在形態、結構和規模上的巨變,在重慶城鄉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們的出現必然引發其內部經濟結構和社會文化結構的變革,必然會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科學技術義無反顧的猛進,經濟社會不可逆轉的飛躍,向我們提出了更加嚴峻的挑戰,問題是:面對這滄桑巨變,我們如何才能重拾文化自信,找回曾經失去的自我,走出那暗夜的迷途?
“20世紀既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偉大而進步的時代,又是史無前例的患難與迷惘的時代……人類對自然以及對文化遺產的破壞已經危及其自身的生存;始未料及的‘建設性破壞’屢見不鮮……工業革命后,人類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同時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吳良鏞《北京憲章》)。
當代耗散結構理論創始人普里高津指出:“西方的科學家和藝術家習慣于從分析的角度和個體的關系角度來研究現實,而當代的一個難題恰恰是如何從整體的角度來理解世界多樣性的發展。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是著重研究整體性和自發性,研究協調與協同,現代科學的發展更符合中國的哲學思想。”他預言:西方科學和中國文化對整體性、協調性的結合,將導致新的自然哲學和自然觀,當然,也必將包括我們的建筑觀。
當我們自豪于輝煌的長江流域古文化時,更需要的是學習巴人尊崇山水自然、追求和諧完美的精神,循著歷史的足跡去努力探尋動態的文脈更新,在弘揚燦爛的山水文化中理順曾被扭曲的文脈,讓重慶未來的城鎮、鄉村、建筑能更多地融入我們的傳統文化,在廣袤的山水中,輝煌于民族文化復興的歷史邏輯點。(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