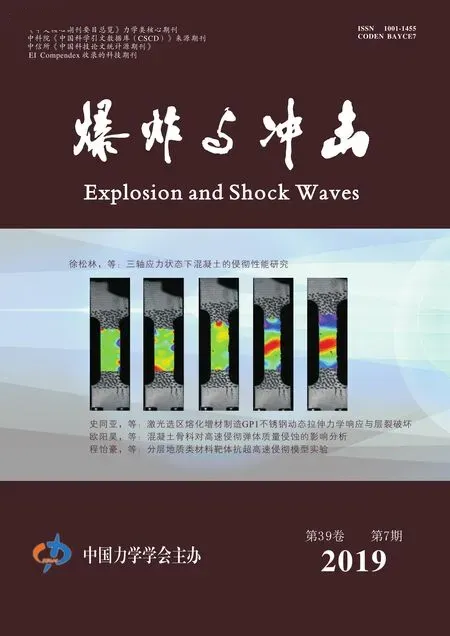分層地質類材料靶體抗超高速侵徹模型實驗*
程怡豪,鄧國強,李 干,3,宋春明,邱艷宇,3,張中威,王德榮,王明洋,3
(1. 陸軍工程大學爆炸沖擊防災減災國家重點實驗室,江蘇 南京 210007;2. 軍事科學院國防工程研究院,北京 100850;3. 南京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4)
近年來,在超高速動能彈體對混凝土和巖石類介質的打擊毀傷效應方面開展了廣泛的研究[1]。其中Antoun等[2]、Wünnemann等[3]和鄧國強等[4-6]開展了超高速打擊巖石和砂的數值計算分析,得到了地沖擊效應的傳播衰減規律和等效荷載計算方法,Dawson等[7]、牛雯霞等[8]、王鵬等[9]、錢秉文等[10]開展了動能彈對混凝土靶和花崗巖靶的超高速撞擊效應實驗研究,Cheng等[11]、Shi等[12]、李臥東等[13]、王明洋等[14]、宋春明等[15]、李干等[16]開展了對巖土類介質超高速撞擊侵徹與成坑效應的理論分析。實際條件下防護工程往往是以分層結構的形式出現的,因此開展分層靶體的超高速侵徹效應研究具有更加現實的意義。這一類問題在裝甲防護和航天裝備防護領域得到了較系統的研究[17-18],但與工程防護相結合的研究還比較缺乏,其中劉崢等[19]基于數值計算方法研究了形式為“花崗巖-砂-混凝土”的成層式防護結構對超高速動能武器打擊的防護性能,并發現在花崗巖層和砂層間增加空氣隔層可以顯著減小混凝土層的侵徹深度,但上述研究結論缺乏實驗的直接驗證。
在文獻[19] 的基礎上,本文中開展約10馬赫速度條件下高強鋼質桿形彈對4種分層組合形式的地質類材料靶體的超高速侵徹效應實驗,來驗證相關數值計算的結果,并進一步探索實際工程條件下抵抗超高速動能武器打擊的優化組合結構形式。
1 實驗設計
劉崢等[19]采用了一種“硬-軟-硬”復合結構初步實現了“侵蝕破壞彈體-吸收地沖擊-抵抗殘余侵徹”的抗超高速打擊效果,其中最上層(第1層)為花崗巖組成的遮彈層,第2層為干砂組成的分配層,第3層為混凝土組成的結構層;當增加空氣隔層時,將隔層設置于遮彈層和分配層之間。
本實驗設計大體參照劉崢等[19]的方案,但除了考慮空氣隔層對結果的影響,還設計了將砂層從分配層轉移到結構最上層的情形以考慮砂層位置對結果的影響;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水平入射條件的限制,采用一種密度和強度均較低的砂漿代替砂。在所有實驗方案中,混凝土層均作為背板結構,且為了便于評價最終侵徹效應,混凝土層厚度為彈體長度22倍以上,此時背板可視為半無限介質。
1.1 彈體參數與撞擊條件
彈體材料選用高強度合金鋼30CrMnSi2A,基本材料參數如表1所示。彈體采用尖卵形頭部實心彈體(圖1),彈頭曲徑比(calibre-radius-head,CRH)為3,彈體直徑為7.2 mm,彈長為36 mm,發射時與外徑18 mm的可分離式聚碳酸酯彈托配合。設計彈體發射速度為10倍音速(10馬赫),入射方向與靶體迎彈面垂直。

圖1 彈體與彈托Fig. 1 Projectile and sabot

表1 彈靶材料的基本材料參數Table 1 Basic parameters of materials of projectile and target
1.2 靶體材料與幾何尺寸
靶體材料主要包括花崗巖、砂漿和混凝土,主要材料參數如表1所示。

圖2 靶體的分層設計Fig. 2 Sets of layered targets
靶體分層設計方案如圖2所示,其中圖2(a)~(d)為方案A、B、C和D的側視圖(此時彈體從左向右水平入射,“1”表示花崗巖層,“2”表示空氣隔層,“3”表示砂漿層,“4”表示混凝土層)。所有方案下砂漿層和花崗巖層的厚度均相等,不同方案之間的區別為是否設置空氣隔層以及砂漿層的位置。整個靶體在內直徑120 cm的鋼制圓筒模具中澆筑完成,其中花崗巖預先切割成600 mm×600 mm×50 mm的長方形并用混凝土澆筑在模具中,花崗巖平面形心與圓筒軸線重合;為了滿足空氣隔層的設置要求,模具被預先設計成直徑相等、高度不同的若干薄壁圓柱形鋼桶,相鄰鋼桶之間采用螺栓連接,這樣一來靶體不同部分即可分別澆筑并根據要求進行任意組合。
1.3 發射與量測技術
發射裝置采用陸軍工程大學爆炸沖擊防災減災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氣體驅動二級輕氣炮,彈托采用氣動分離技術,彈體速度通過激光遮斷測速裝置確定,靶體幾何中心與彈體入射點間的誤差不超過1 cm。撞擊成坑采用光學三維掃描裝置捕捉并利用Geomagic Control 14對成像數據進行重構和特征提取,測量誤差小于0.1 mm。成坑參數主要包括各層的成坑區表面直徑、成孔直徑和背板侵徹深度等。
2 實驗結果
2.1 破壞現象
實驗A、B、C和D的彈體撞擊速度分別為3 486.5、3 447.9、3 432.7和3 440.3 m/s,最大速度與最小速度相差僅1.57 %,因此可以忽略撞擊速度差異的影響。從破壞現象看(圖3~6),所有實驗中彈體均貫穿花崗巖和砂漿層,直至侵徹至混凝土層;混凝土層的彈坑的中心位置與靶體中心的偏離距離不超過1倍彈徑,這說明彈道偏轉效應很小,可以視作垂直侵徹。

圖3 方案A的破壞現象Fig. 3 Damage phenomena in experimental set A

表2 成坑幾何特征參數的量測結果Table 2 Measurements of geometrical character of craters
當含有空氣隔層時(圖3(a)~(b)、圖4(a)~(b)),首層形成一個直徑約10倍于彈體直徑的貫穿孔洞,還會在正面和反面分別形成范圍更大的剝離區和震塌區,且剝離區和震塌區的平面尺寸相當,厚度也較接近(詳見表2)。從底層破壞現象看,方案A(圖3(c)~(d))的砂漿層與混凝土層的孔洞直徑存在明顯的不連續變化,且混凝土層表面孔洞直徑遠小于砂漿層孔洞直徑,這與兩種材料的強度特征與聲阻抗差異有關。砂漿層在孔洞區域外還存在一個直徑約20 cm的損傷區域(圖3(c)),從形態上看這一區域明顯有別于圖3(a)的剝離現象,可以推斷其形成機理主要是首層花崗巖在背板形成的震塌碎片云作用;方案B中混凝土形成的孔洞直徑(圖4(c)~(d))遠小于圖3(c)~(d)的結果,孔洞周圍不存在剝離區,僅在其周圍形成直徑10 cm左右的蜂窩狀損傷區,其影響深度較淺,從形態上看同樣可以歸結為首層震塌碎片云的作用。這種碎片云引起對背板的破壞效應類似于Whipple防護屏的效果[18],這與數值計算結果[19]完全一致。
當不含空氣隔層時(圖5~6),靶體整體上形成漏斗形的彈坑;但從三維掃描的結果看,不同介質界面附近的彈坑輪廓具有顯著的非光滑過渡的拐角,這種現象可以歸結為材料聲阻抗與強度的非連續梯度變化。總體來看,花崗巖層彈坑直徑隨深度變化最劇烈,而砂漿層彈坑的直徑變化則較緩和,這在圖5(b)的砂漿層彈坑輪廓和圖6(b)的花崗巖彈坑輪廓的對比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圖4 方案B的破壞現象Fig. 4 Damage phenomena in experimental set B

圖5 方案C的破壞現象Fig. 5 Damage phenomena in experimental set C

圖6 方案D的破壞現象Fig. 6 Damage phenomena in experimental set D
通過開挖,在實驗A、C、D的彈坑底部可以找到少量殘余彈體,剩余彈體長度均約4 mm(圖7),從彈體一端扁平、一端微微凸起的形態可以判斷,殘余部分全部為侵蝕后剩余的彈體尾部部分,且利用磁鐵可以在彈坑內壁吸引到少量鐵屑,這說明侵徹過程滿足從頭部至尾部的逐漸侵蝕過程[4,14-15,20]。由于方案B沒有收集到可以辨別的殘余彈體,可以認為彈體被完全侵蝕。

圖7 實驗前和實驗后的彈體形態與長度Fig. 7 Profiles and length of projectiles before and after experiment
2.2 彈坑尺寸
分層復合靶體的成坑特征參數較復雜,為了便于分析,這里選取以下參數:對于含空氣隔層的實驗A和B,選取首層正面彈坑表面直徑D1f、首層背面彈坑表面直徑D1b、首層貫穿孔直徑D1p、首層震塌區厚度h1s、混凝土層表面彈孔直徑Dc和混凝土層侵徹深度hc(需加上剩余彈體長度);對于不含空氣隔層的實驗C和D,選取彈坑表面直徑Df、混凝土層表面彈孔直徑Dc和混凝土層侵徹深度hc。以上符號的具體含義可參考圖3~6。最終量測結果如表2所示。
根據表2作以下分析。
(1)將實驗方案A和實驗方案C作對比,或將實驗方案B和實驗方案D作對比時,可發現增加空氣隔層可以減小hc,特別是實驗方案B的hc僅為實驗方案D的49.7 %,但此時實驗方案A和實驗方案B的D1f也要分別大于實驗方案C和實驗方案D的Df,因此在一定條件下增加空氣隔層可以減小結構層的侵徹深度,但這會引起結構成坑直徑的顯著加劇,這和數值計算結果[19]是定性吻合的。
(2)對比實驗方案A和實驗方案B可以發現,當增加空氣隔層時,若將砂漿層從混凝土頂部轉移至花崗巖頂部,則hc可減小50%以上,此時D1p無顯著變化,但D1f和D1b稍有增大。
(3)對比實驗方案C和實驗方案D可以發現,若不設空氣隔層,將砂漿層從混凝土頂部轉移至花崗巖頂部可使hc可減小16.5%,但Df稍有增大。
(4)從減小hc的角度看,實驗方案B(增加空氣隔層并將砂漿層置于整個結構最上方)是最有利的。從減小橫向破壞區域(D1f、D1b和Df)來看,實驗方案B卻是最不利的。
3 分析與討論
3.1 空氣隔層的影響
從本文實驗結果和劉崢等[19]的計算結果看,一定條件下增加空氣隔層對于減小底部結構在超高速打擊下的侵徹深度是有利的。這里進一步給出兩方面可能的解釋:
(1)超高速撞擊動能在撞擊發生后的極短時間內大量轉移到靶體近區的內能中并以應力波形式向靶體遠處擴散。當加入空氣隔層后,由于上下層阻抗嚴重失配,應力波能量向下部結構直接傳遞的途徑被阻滯,因而被迫向花崗巖層發生橫向轉移;伴隨著更大范圍的花崗巖參與破壞過程,彈體在貫穿花崗巖層時的平均阻力有所增加,其最終結果是減小了貫穿后彈體的長度和速度,使得混凝土靶體的侵徹深度減小。
(2)若認為背板侵徹深度是彈體侵徹和花崗巖背面運動介質的沖擊局部作用共同決定時,還可以作如下推斷:當存在空氣隔層時,花崗巖背面的震塌碎片被擴散到較大的空間范圍內(擴散角效應),在這種效應下,碎片對底層靶體的局部破壞作用相對于無空氣隔層的情形而言被大大削弱了,因此侵徹深度有所減小。
值得注意的是,空氣隔層對侵徹深度的影響似乎存在正負兩種效應。例如:Wu等[21]的混凝土靶板貫穿實驗結果顯示,彈體在貫穿多層間隔靶體后的剩余速度要大于相同厚度的單層靶體(初始撞擊速度640 m/s)。從相關文獻[17-18] 看,空氣隔層的正負效應不僅取決于隔層厚度與彈體長度之比,也和初始撞擊速度、首層裝甲的厚度和強度等因素相關,因此對上述因素需要作進一步分析以得出更加全面的結論。
3.2 砂漿層位置的影響
如前所述,超高速撞擊能量在撞擊瞬時大量轉移到靶體近區的應力波中,因此頂層的砂漿(或砂)豐富的孔隙會大量耗散應力波能量,這就大大減小了傳遞到花崗巖上的能量總和。另一方面,從桿形彈的超高速侵徹過程[20]來看,瞬時激波階段(即超高速侵徹的第1階段)壓力最高,侵徹速度也最大,此時靶體材料的強度對抵抗侵徹意義不大。將強度較低的砂漿(或砂)置于頂層,可以減少花崗巖在瞬時激波階段的消耗并在接下來的準穩態侵徹階段(即超高速侵徹的第2階段)更充分地發揮高強度的特點。這一過程的最終結果是減小了剩余彈體的長度和動能。
3.3 對成層式防護結構設計的啟示
本文實驗結果和劉崢等[19]的數值計算成果說明,當滿足一定條件時,合理的分層設計確實可以顯著提高防護效能。當以減小超高速動能彈打擊下結構層的侵徹深度為目標時,可以歸結為“軟-硬-軟-硬”的分層設計思路。第1軟層(疏松層)應具有較低的聲阻抗和較高的孔隙率(可采用干砂、疏松土或級配不良的碎石等),主要作用是承受瞬時激波階段的侵徹效應并耗散初始撞擊引起的部分波動能;第1硬層(遮彈層)應具較高的強度和密度(可采用天然巖體、漿砌塊石、高性能混凝土、剛玉、陶瓷等),其作用是抵抗彈體侵徹、破壞彈體結構、分散彈體動能的時空分布密度;第2軟層(分配層)應具有極低的聲阻抗(可采用空氣或干砂等),通過與遮彈層和結構層間形成顯著的阻抗失配,進一步促進遮彈層防護效能的發揮;第2硬層(結構層)一般采用鋼筋混凝土結構,除了抵抗剩余彈體的沖擊局部作用外,尚應考慮震塌碎片打擊下的防護設計。當然,最終的抗侵徹效應尚取決于彈體的材料性能和結構設計、彈體的撞擊速度和角度,以及各層靶體的厚度,這些因素的影響尚有待進行系統分析。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上述分層設計思路與常規鉆地彈侵爆條件下成層式防護結構的設計思路并行不悖[22-23],此時遮彈層的作用基本不變,而分配層還兼具削弱爆炸波能量向結構層耦合的作用,這說明抗常規武器的防護設計可以與抗超高速動能彈的防護設計相統一。
4 結 論
開展了近10馬赫速度條件下桿形鋼彈對4種配布形式的分層地質類材料靶體的侵徹效應實驗,實驗結果表明:增加遮彈層與下部結構間的空氣隔層、在整個結構頂部設置疏松砂漿層,均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加劇彈體破壞、減小結構層的侵徹深度,但同時會增大遮彈層的表面成坑直徑。從減小結構層的侵徹深度出發,“軟-硬-軟-硬”的分層設計思路對抵抗超高速彈體侵徹是可行的,但其具體效能的發揮尚有待對相關影響因素作更加系統全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