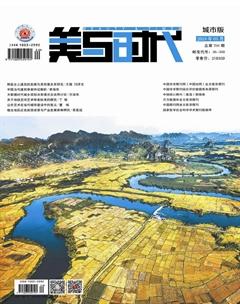上海自然博物館標本布展設計的價值性探討
李錦
摘 要:上海自然博物館新館現已落成,其與老館相比有許多不同。文章認為博物館對于標本的布展方式具有科學性與人文性兩方面的特點,而這兩個方面各自又有兩個層面的含義。文章對這兩個方面進行論述,并引出上海自然博物館所倡導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而這正是上海自然博物館布展方式的價值性所在。
關鍵詞:上海自然博物館;標本;布展;博物館陳列;生態美學;價值性
上海自然博物館新館2015年正式對公眾開放,其展品的陳列設計十分新穎。本文主要關注的是上海自然博物館對于標本的陳列與展示。標本是自然博物館主要的收藏品,對于標本的布展方式集中體現了博物館的理念和價值取向。上海自然博物館新館對標本的展示不僅體現出博物館作為一個研究機構的科學性和嚴謹性,更體現出了藝術審美特征。本文試通過對展區布展方式的科學性與人文性分析,來闡述上海自然博物館所倡導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而這也是博物館如此布展設計的價值性所在。
一、標本布展的科學性
自然博物館的首要任務是展示自然生態,提供準確的科學信息并教育觀眾。上海自然博物館新館布展的科學性,有兩個層面的體現。第一個層面是博物館展品陳列方式的科學性,以“生命長河”展區的展品為例。
“生命長河”展區中的展品是動物標本以及一比一等大的模型。收藏展示標本是自然博物館的主要功能之一。“在自然博物館中實物標本作為參觀行為的客體,就其單件標本而言,可以提供全方位的形態和個體生物學信息;就標本群體而言,它們代表了一個群落或族群,展示了更為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群落關系,無論在科學研究,還是科學教育方面,其作用都是無可替代的。”[1]但是,標本再逼真也僅僅是視覺上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樣貌,并不能展現一個活生生的動物的狀態。上海自然博物館充分考慮到了這一點,部分標本配備了還原動物聲音狀態的音響,步道兩旁的多媒體提供展品的全面信息和影像。如此,展館即做到了生物標本的多維度展示。
“生命長河”的展品分區和展品擺放也具有科學性的一面。首先,在生物學分類中相近的動物標本被陳列在一起。其次,每一個標本個體不是孤立的,標本之間有著強烈的互動關系。例如陳列于展區最后的鹿。這些鹿的品種不完全相同,但是它們的陳列方式依據自然中鹿群的行進姿態,或昂首跳躍,或低頭前進,還原了一個相對接近真實的鹿群生存圖景。并且,依據動物在生態圈中的位置和生存環境,在標本和模型的周圍也陳列了巖石、草甸等景觀。
對于標本的呈現從一樓的“生命長河”延續到負一樓和負二樓的“演化之道”“繽紛生命”“生態萬象”。這些展區依據不同的主題展出不同的內容,包括生物的化石和解剖研究、生物的生物學分類的講解、生態圈的整體呈現以及生物生存習性的演示。生物標本的展出形態由單個整體到骨骼化石、內臟解剖,由單純的生物學到多元學科體系的綜合。從一樓至負二樓,生物標本的展出方式更加多樣和細致。
“生命長河”至“生存智慧”這些展區的排列順序體現了自然博物館對于生物標本展示科學性的第二個層面,即展示內容由宏觀至微觀,由直觀認識至科學分析,由淺入深。在現代科學發展以前,人類對動物的認知是以其外形和習性為主,依據的主要是動物的實用性、是否可食用、是否可以為人類工作等等。而隨著解剖學、生物學、考古學等科學的發展,人對動物的認知也越來越深入,越來越細化。從“生命長河”到“繽紛生命”正是由感性認知到理性認知的過程,展廳布置的風格也從“生命長河”一個野性的大自然到“繽紛生命”的動物研究所。
展區的展品陳列遵照了自然的秩序與科學研究的準則,在展區的陳列狀態和展區順序安排兩方面都體現了科學性的一面。當然,自然博物館的布展不僅在科學性上值得注意,在展廳的人文性方面也同樣值得關注。
二、標本布展的人文性
本文認為上海自然博物館的人文性體現也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展覽方式的審美性體現。
仍以“生命長河”展區為例。“生命長河”展區的入口位于二樓,觀眾在二樓展區入口處幾乎可以看到整個展區的全貌,分布世界各地、遍布高空海洋、穿越幾千萬年的生物同時出現在一個展廳,觀眾站在一個高空俯瞰全景,相比較平時,這是一種陌生化的視角。同時,展品等比例出現在展廳,巨大的動物模型產生震撼的效果,觀眾穿梭在真實的標本和逼真的模型中間,更能產生對自然的敬畏之心,由此帶來崇高的審美體驗。此外,自然博物館充分利用多層設計的展示空間,讓觀眾的視點多樣化,達到一種去中心化的效果。在“生命長河”展區,位于二樓入口處的觀眾看下方的動物標本是俯視的,當走入布道,展品與觀眾處于同一水平線上。觀眾在參觀過程中由最初的高空視角慢慢變成人的視角,參觀的過程更加立體和全面。對于懸掛的海洋動物模型,由平視慢慢變成仰視,如同逐漸走入海底世界,每一個角度看到的景象都十分不同。而曾經的自然博物館老館,標本被封在展柜里,觀眾只能隔著玻璃從展柜的正面或者側面參觀。去中心視點的展覽體現了新的視覺觀看方式,這也與當代藝術的整體觀念相吻合。“生命長河”展區帶來的審美感受是多樣和新潮的。
在“演化之道”展區,化石被加上了傳統的油畫畫框,一片片海百合化石以藝術作品的形式被陳列。“繽紛生命”展區排滿整面墻壁的動物犄角、螺旋懸掛的松果、與書法并列展示的蝴蝶標本等等,用作科普教育的展品與體現藝術審美的展覽方式結合,使標本更具審美性與可看性,這種展覽方式更加有利于教育的進行。科學與藝術的結合使得自然博物館具有了人文氣質。
第二個層面的人文性則是體現在動物標本的展示空間安排中。動物都有其自己的家園,作為一個完整獨立的生命它們應該是與環境結合在一起的。上海自然博物館在這方面做出了努力,“生態萬象”展區就是如此。在這里,各個不同的生態圈以整體的形式展出,動物被還原至原本的生存空間。動物作為研究個體的性質在這些展廳不再是強調的重點,而是被當作生命本身回歸到整個生態圈中,呈現給觀眾的是不同于人類城市生態的其他生態奇景。
其中,“走進非洲”展區集中體現了這一點。這是一處沉浸式的展覽空間,展區內用標本、模型和背景板模擬非洲的自然環境。在這些動植物的標本和模型中間,最值得關注的是當地的土著人和房屋也在展示之列。在以往的大多數展覽中,人與展品隔著玻璃柜,人與自然是割裂的。人以研究者的身份介入自然,人與自然是處在不同世界的二元狀態。例如在“繽紛生命”展區,對動物的科學研究就是把動物當作一個與人不同的“他者”,將動物從生存環境中隔離出來放到實驗室的顯微鏡下。相反,此處人與動物植物同屬非洲大草原,不再用二元的方式看待自然,而是將人與自然看作一體。同時,這種“原生態”的展出方式在設計上也更具視覺吸引力。
展區布置的人文性是通過審美性與人與自然關系的兩個方面來呈現的。審美性是展廳布置的外在方面,人與自然的平等關系則是展廳的布展理念,屬于內在范疇。
三、標本布展的價值性
上海自然博物館布展設計的價值性就在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也是自然博物館的建館主題,即“自然·人·和諧”。無論是標本布展科學性還是人文性的特點,都顯示出了這個主題。
從“生命長河”到“演化之道”再到“繽紛生命”與“生態萬象”,上海自然博物館在盡量地平衡人與自然的不平等關系,從直觀地認識動物的外形到細究動物的分類與解剖知識,最后又將動物放回到自然中,潛在的邏輯是產生好奇到客觀認識再到和諧相處,生物從一個標本最終回歸到生命本身。這是一種積極的人與自然的關系。
在上海自然博物館新館的規劃過程中,這種人和自然的關系顯然已經被考慮在內了。“當代世界正經歷著一場價值觀、道德觀和文明范式朝著深化發展的變革,而這種深化變革的實質就是要我們對自然的態度應從主宰和控制而改變為合作和非暴力的態度。”[2]博物館以中國的“天人合一”觀為展示理念和框架重點,在建設過程中就強調要將人放在自然之中而不是抽身事外。
在當代,與中國的天人合一觀點有相似之處的生態美學觀點也應運而生。西方原本的人類中心主義逐漸讓位于一種生態美學。“生態美學實際上是一種在新時代經濟與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有關人類的嶄新的存在觀,是一種人與自然、社會達到動態平衡、和諧一致的處于生態審美狀態的存在觀,是一種新時代的理想的審美的人生,一種綠色的人生。”[3]這種生態美學是對工業化之后人類生存狀況的再思考,是對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擔憂。
天人合一與生態美學并不完全相同,此處只是表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自然與人的關系已經是一種主流。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展示空間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哲學觀,也是一種生態美學的哲學觀,這是博物館標本展示方式的價值性所在。
上海自然博物館新館對于生物標本的布展方式具有科學性和藝術性,體現了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積極觀點。當然,這種展示方式的優點還在于更加利于博物館功能的發揮。“自然博物館的核心功能是學術研究、標本收藏、展示教育。”[4]上海自然博物館對于生命的展覽空間設計在對公眾的展示教育方面是非常有益的。自然博物館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生物學、地質學等科學范疇,這些領域對大多數沒有接受過專業教育的觀眾來說是比較陌生和有隔膜的。學術化的介紹和呆板的展示都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但是在上海自然博物館,科學性與人文性兼具的展館設計會充分調動觀眾的視覺聽覺觸覺等,讓人全身心投入其中,更加主動和自覺地接受自然知識,讓普通人和兒童愛上自然。
參考文獻:
[1]宋嫻,顧潔燕.上海自然博物館:促進公眾與藏品互動[J].國際博物館(中文版),2015(2):65-69.
[2]潘政,梁兆正.繼承與發展:上海自然博物館建館理念的思考[J] 中國博物館,2007(4):33-38.
[3]曾繁仁.試論生態美學[J].文藝研究,2002(5):11-16.
[4]王平.自然博物館陳列設計概要[J].博物館研究,2015(4):26-30.
作者單位:
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